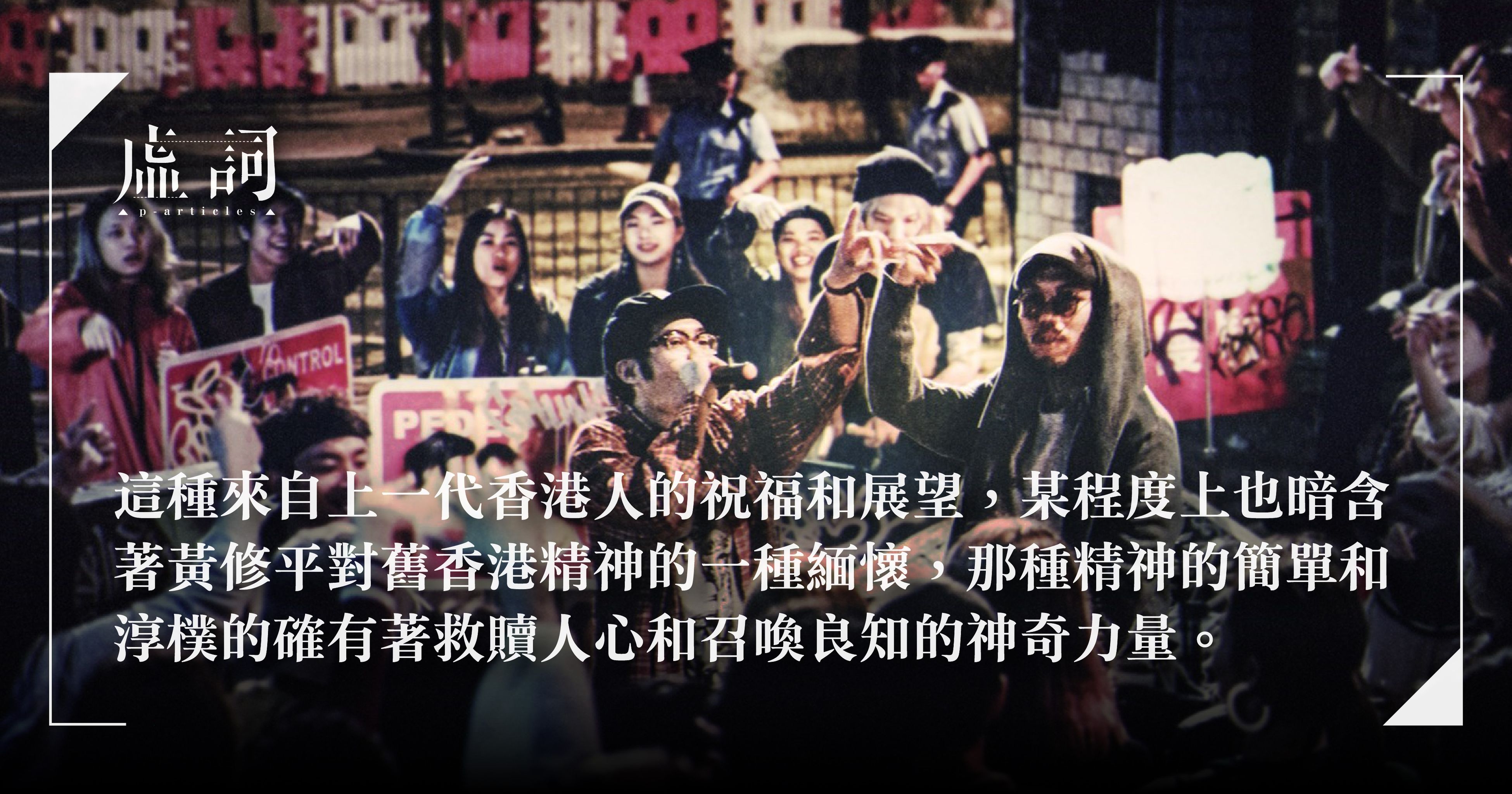隱形操控下的迷失、救贖與反抗——評《狂舞派3》
1. 引言
時隔八年,由黃修平執導的電影《狂舞派3》(下稱《狂3》)於今年2月上映,迴響非凡,其中最引熱議的莫過於該電影與《狂舞派1》(下稱《狂1》)的不同側重。
主演之一Heyo在3月14日旺角百老匯下午16:40場現身謝票,場上有一名女觀眾十分準確地指出,從《狂1》到《狂3》,即從夢想回到現實。這正如黃修平在接受訪問的時候所說:「《狂舞派3》說的不再是一個青春熱血的勵志故事,而是一個更發人深省的故事。」(註1)。影評人鄭政恆更是一語中的:「還記得2013年看《狂舞派》的熾熱心情......到如今卻見中年人的凝重心態,眼見千帆過,『How far are you willing to go for dance?』已改換為現實和理想之間魚與熊掌的掙扎。(註2)」社會元素的增添當然與這些年來的政治局勢有關,不只是黃修平,不只是電影人,如今生存於我城的許多創作者都很難不去思考藝術與社會事件之間的關係,很難不察覺到堅持藝術創作的重重困苦。因此,從《狂1》到《狂3》的轉變,亦可視為我城近幾年來許多創作者的貼切寫照。
關於現實和夢想之間的衝突,黃修平有他獨特的反思,在被問及電影的構思時他如是說道:「義利之爭就係電影的主題,由原來單純勵志的一群人,佢地跳返出嚟,要面對生活的壓力和殘酷,他們的前路要面前(對)一個義利之爭的問題。(註3)」這不禁讓筆者想起「娜拉走後怎樣」的典故,魯迅曾在給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文藝會講上以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劇作《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的主角娜拉為例,說明在經濟未能獨立的情況下,女性出走不外乎兩種結局,「不是墮落,就是回來」(註4),該場演講中魯迅還以籠中小鳥為喻,「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裡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註5)。在這樣的困境之下,魯迅認為倘若無法找到可走的路,最好則不要去驚醒困於籠中的人。
電影《狂3》中龍城工業區年青人的處境和娜拉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共同之處在於二者的經濟都未能獨立,且眼前都似乎只有兩條路:要麼墮落,要麼回來。龍城工業區的的年青人最後作了與娜拉不同的選擇,這讓筆者想到《狂3》開首阿弗的另一個比喻:「從前有一隻老虎,為咗證明自己係老虎而入咗動物園,咁佢仲係咪一隻老虎。」倘若說在溫飽和自由之間娜拉選擇了前者,那麼龍城工業區的年青人們則選擇了後者。這像極了《狂3》主題曲《歡迎嚟到呢座城市》裡的一句歌詞:「拒絕困在籠中」(和魯迅一樣,都是用籠子作為比喻)。即使餓死在籠子外,也不願在籠中遺忘了如何飛翔。對於龍城工業區的年青人而言,籠子中進行的表面上是推動藝術的工作,但實際上卻是一個粉飾工程。
2. 血腥的手即看不見的手
地產霸權源自資本霸權,而資本霸權又源自首次分配的不公,這個看似由價格決定資源分配的自由市場實則是個極為不公的制度,以自由為美名,遮掩各式各樣的剝削。早在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便已在《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中如此寫道:「它(資產階級)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註6)」將資本主義對個體自由的剝削完全揭露。
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資本主義的壓榨和剝削早已不再是「公開的」、「直接的」和「赤裸的」,其手段變得更為掩人耳目,更像是一顆讓人沉醉其中的糖衣大炮彈。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和史蒂夫.托皮克(Steven Topik)合著的《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1400年到現在》(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400 To The Present)便在揚棄了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這一觀點的基础上,認為「(歷史上那隻)血腥的手和那隻不可見的手往往狼狽為奸;甚至,這兩種手往往為同一軀體所有。(註7)」簡而言之,這個制度以穩定的經濟利益為誘餌,讓人們不知不覺地,甚至心甘情願地割讓自由。
《狂3》主要就是對著種粉飾工程的揭露。地產商人不但以名利作為誘餌,還以「文化推廣」為之添花,借打造狂舞街為幌子,讓身處體制外的人更加心甘情願地進入體制,從而為地產商人賺取地產暴利。而租金卻因此高漲,創作者的空間不斷被打壓,許多街頭表演者甚至在街頭表演時也會被警察留難驅趕。這隻血腥的手已不再只是簡單的「無形」,還經過了種種美化,讓人難以察覺。
3. 義利之下個人的迷失
為了突出「看不見的手」對個體自由的摧滅,導演為五位主演設置了五條故事線,每一條故事線都有著差不多的起承轉合,並在狂舞街爆紅之後為他們安排了十分相似的「義利之『爭』」(「爭」在此可以是與親友之爭執、亦可以是角色自我內心的掙扎)。
Heyo(霍嘉豪飾)因狂舞街發展一事和饒舌組合Rooftop的兄弟發生了意見分歧,被視為叛徒,某夜當街被曾經的兄弟集體diss(不尊敬地批評),並被當成導致龍城工業區消失的罪魁禍首;Dave(楊樂文飾)也因為同樣的情況,在舞蹈比賽中被其他選手嘲笑;Hana(顏卓靈飾)因媒體胡亂報導的新聞,被隊友誤會她是想和他們割席。此外,男友Dave因無法忍受她對舞蹈不夠嚴謹的態度而向她提出分手,友情和愛情均出現危機;Youtuber阿良(蔡瀚億飾)為了更有效地宣傳與地產商合作的「狂舞街」,利用撿紙皮婆婆的經歷作為宣傳廣告的故事原型,陷入了良知的自我譴責之中;而仍是小孩的佳仔(劉皓嵐飾)則因為自己的往事被阿良曝光,公共領域入侵私人領域,自尊心受到嚴重創傷。
劇情至此,導演想要帶出的意思已經十分明顯,選擇進入體制的五位主角在進入體制之後雖然獲得了名和利,但同時也失去了更重要的東西。進入公眾視野之後,許多事情都會越來越不由自主,甚至變質。最可怕之處在於,黃修平有意無意之中展現了資本主義這種操控的無形——地產商人唐先生除了商談和剪綵兩幕之外,其他時間都沒有出現,也就是說,在將幾位主角勸入體制內之後,各種衝突和矛盾都是在主角和主角之間,以及主角和親友之間釀造而成,背後操控著一切的那隻手,自始至终都是無情且隱形的。
4. 救贖及反抗:對操控的消解
電影的最後,各位主角選擇退出體制,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不像其他大眾電影,《狂3》沒有刻意以雙贏的劇情收結,也沒有正義最終戰勝邪惡的好萊塢式橋段,但筆者看到最後卻有一種圓滿的感覺。有人說這就是導演想要傳達的藝術精神,正是這種精神讓整部電影廣受好評。而這也正是黃修平認為面對「看不見的手」的對抗方法,即保持清醒,與體制保持距離。
另外,導演還將希望寄望於對個人良知的召喚和對原初生命力的感動,電影中分別由撿紙皮婆婆和美國的孩子們擔任這樣的角色。筆者先討論對個人良知的召喚。劇中,一位婆婆每天都默默地揀紙皮,每每有人幫助她,就會以「好人一生平安」來答謝。這句「好人一生平安」鼓舞著阿良的創業,最後在他迷失了自我的時候,同樣是這句「好人一生平安」重新喚起他的良知,讓他認清自己的初衷。撿紙皮婆婆的形象其實其來有自,黃修平在訪問中講起2012年拍攝《花椒八角咖啡豆》時曾向一位婆婆借用店鋪,婆婆卻說「你哋借啦,唔使比唔使講錢㗎,我阿婆80幾歲,你哋啲後生仔大把前途,拎去拍啦。(註8)」婆婆這一善舉讓黃修平很受感動,於是想到用「好人一生平安」作為電影角色的口頭禪。這種來自上一代香港人的祝福和展望,某程度上也暗含著黃修平對舊香港精神的一種緬懷,那種精神的簡單和淳樸的確有著救贖人心和召喚良知的神奇力量。
至於對原初生命力的感動,則由Dave去美國見到的一群舞蹈小孩所體現。Dave是一個十分勇敢且十分故我的人,為了追尋自己真正的夢想,他專程去美國紐約幫朋友的舞蹈班教學(朋友已經失去一條腿,卻仍堅持教學舞蹈)。在舞蹈班裡,Dave見到了許多小朋友,這時朋友說了一句:「你聽說過B-man和B-woman嗎?從來都只有B-boy和B-girl」。小孩對某種事物的喜歡是最淳樸的、不考慮任何利益的喜歡,黃修平認為藝術的浪漫,正正體現為這種原初的生命力,正如他在受訪時所說:「有時走過工廈的後巷,會聽到夾band的聲音、在街角又會遇到在拍攝的人、在轉角士多店又會碰見朋友。我覺得這種生命力,好強。(註9)」黃修平藉美國朋友的這句台詞,傳達了他對原初生命力的崇拜,正是這種充沛的原初生命力感動了Dave,也感動了黃修平和觀眾;另外,電影中另一個角色佳仔某程度上也發揮著這樣的角色功能,他成長環境惡劣,家境貧窮、父親反對,最後還因付不起高漲的房租而被逼搬遷,但仍舊堅持他的舞蹈夢想,就像電影最後一幕,佳仔在正在動工的地盤前跳舞,畫面令人十分感觸;還有,主題曲《歡迎嚟到呢座城市》的開首是一群小孩子的合唱,那些天真無邪的歌聲為整首歌作了極好的鋪墊。因此,黃修平在懷念上一代的香港精神的同時,亦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
除此之外,筆者亦感覺到黃修平渴望以一種狂歡式的反抗消解資本的無形操控。在電影的高潮部分,筆者看到了一齣狂歡式的表演。「狂歡理論」在巴赫金(Mikhal Bahktine)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中已有集中討論。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的《沃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評》(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裡更是如是詮釋:「通過肉體的騷亂,狂歡擾亂了一切超驗能指,使它屈服於荒謬和相對主義;權力機構被『幽默激進主義』(讓.保羅語)的怪異荒誕的戲仿所間離,『必要性』被置於諷刺的質疑之下,客體被替換,或被否定成為其反面。無休止的模仿和倒置(鼻子/陰物、臉蛋/屁股、神聖/褻瀆)橫衝直撞,貫穿社會生活的始終,解構意象,誤讀文體,崩裂二元對立,將其分解成越來越深的模棱兩可的陷阱,一切明確話語最終變得結結巴巴,落入這個陷阱之中。生與死,高貴與低卑,破壞和再生被打發走了。(註10)」在上場表演之前(甚至表演一開始時),狂舞派一班人還心事重重,似乎被籠罩在權力的操控之下而不得不進行違心的表演。直到Heyo拿著大聲公走上舞台唱rap控訴的那一幕,眾人的情緒紛紛被挑動,台上亂成一團,甚至動起了手,一直都左右為難的Hana和阿良此時也露出了笑容,即使他們明白此舉會讓整個投資工程付之一炬。有趣的是,整個高潮部分都發生在舞台上,此時,以Heyo為代表的KIDA似乎在向世界宣示,只要給他們一個舞台,他們就能重新定義整個秩序。該場戲的最後一個空鏡頭停留在舞台的背面,舞台前的人群在騷亂,而這個不知由誰搭建起來的舞台搖搖欲墜,行將崩坼,像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隱喻,給觀眾留下無限的想象空間。
5. 結語
當然,這部戲雖然廣受好評,但它也一定有其缺點,例如對地產霸權問題的簡化,又例如為了突出所要表達的概念而過於刻意地將角色放置於二元對立的位置,這些問題在何兆彬的評論文章〈《狂舞派3》:從夢想拉到現實〉(註11)已詳細闡明。但不可否認的是,跟近幾年同樣反映社會議題的本土電影相比(如《十年》、《麥路人》、《一念無明》),《狂3》不但生動地反映了地產霸權的社會現象,還嘗試揭示其中的運作模式,更重要的是,它還為我城的救贖和反抗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建議。後兩點正是之前的電影所欠缺之處,筆者私以為,這便是《狂3》迴響極佳的原因。
註:
1. 姚嘉敏:〈由夢想到生存,《狂舞派3》中的本土深情——訪導演黃修平〉,《虛詞》,2021年3月9日。
2. 鄭政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焦點短評」,2021年3月5日。
3. 同註1。
4. 魯迅著、閻晶明編:〈娜拉走後怎樣——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講〉,《魯迅演講集》(桂林:灕江出版社,2001)。
5. 同註4。
6. [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台北:左岸文化,2004)。
7. [美]彭慕蘭, 史蒂夫.托皮克:《貿易打造的世界:社會、文化、世界經濟,從1400年到現在》,(台北:如果出版社,2019)。
8. 同註1。
9. 同註1。
10. [英]特里·伊格爾頓:《沃爾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評》,(南京:譯林出版社,2005)。
11. 何兆彬:〈《狂舞派3》:從夢想拉到現實〉,《虛詞》,2021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