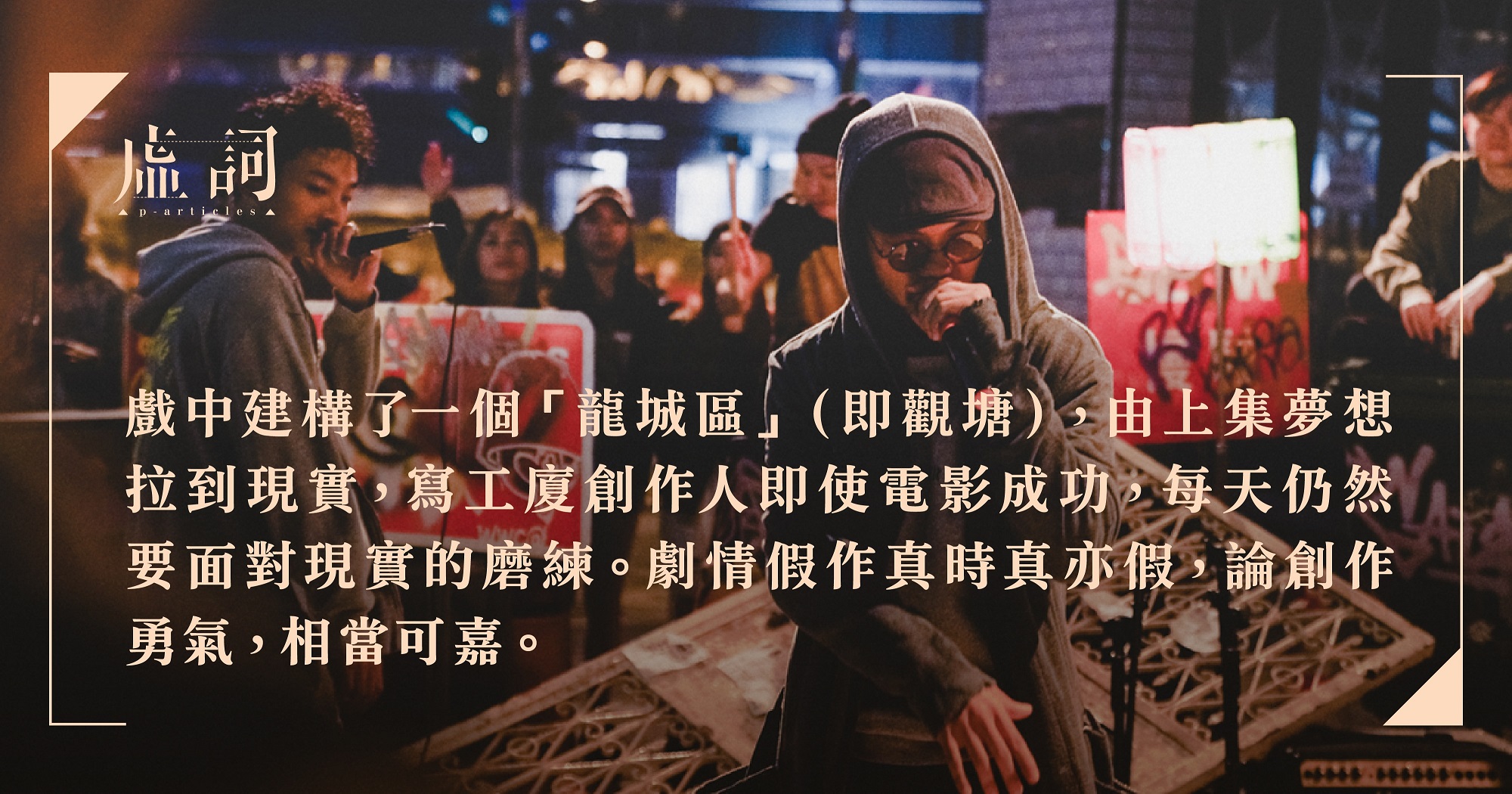《狂舞派3》:從夢想拉到現實
疫情第四波暫緩,戲院終於重開,作為今年第一齣上畫的香港本土電影,兼高先電影院開幕電影,《狂舞派3》挾七年前餘威,令人期待。
港片衰亡,但同時越來越受到年輕人重視,究其原因,是因為港人正感到失去身份。對有點年紀的人來說,是因為往日港片曾有太輝煌的年代。
香港電影工業是否已死?前兩晚有兩代電影人就此主題先在Clubhouse交手,繼而各自在拍片自述,惹起網民一殼花生。這個題目即使講三五天也說不清,但兩位主角根本牛頭不對馬咀。老的是在說港產片要回到過去風光日子機會等於零,嫩的說電影/遊戲/YouTube界線已經模糊。其實辯論的主題根本沒有定義清楚──今日遊戲界的確能吸金,連吳宇森都監製遊戲啦──他會認為自己在從事電影工業?定係只是搵搵外快?
「香港電影工業」這個主題我們先定義清楚。上網看Vocabulary.com對工業(Industry)的定義,解釋是「製作某特定商品、服務的製造商或生意。成衣工人設計、生產及出售成衣,旅遊業則概括所有旅遊業的商業部份。」簡而言之,你專注在某行業,製作產品,這是商業活動,沒寫在字面的意思是它養活了一個行業,這才成一個工業。尤記得2016年,杜汶澤在網上撰文,講到本土電影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翌年他執導《空手道》上畫,他接受訪問說:「本土電影?應該差不多收皮了!應該差不多啦。無論質素,觀眾的歡迎程度,以至各方面因素,都應該差不多,走得了!」他說很多本土電影,要開拍得找明星幫手,免收片酬,每一齣都是Special Case,已經算不上是正常運作。那年他本來說還在籌備另一齣電影,三年過去,已無聲息。如今他全力製作自己的網台節目。
去年12月報載香港電影由年產200-300部,跌到每年50部,當中七成沒賺錢。撇開疫情不談,電影圈開工率足不足,跟圈中人一談就知。因為申請補助,於是有了統計數字,圈中前輩告訴我現在全個香港電影行只有六千人。六千人當中有幾個都在做電影,還是影/視/網兼做,不得而知,目前我沒有這個數字。
這麼一路說來,你以為我認同「香港電影工業」已死?不,就是有幾千人,仍未斷氣,怎能叫死。若2016年杜汶澤形容香港電影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今天只可能更危險。不過香港電影工業死不死,已經不那麼重要,只要港片不死,那才重要──連伊朗這麼惡劣的環境都一直出到電影大師、出產優秀作品,但像導演巴納希(Jafar Panahi)被禁拍電影至2030年,但在2015年仍能自導自演《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如果能有此生命力,那香港電影怎可能會死?
說香港電影工業死不死並不重要,是因為要在香港拍商業電影越來越難,甚至新一代能由本土拍到北上,也沒有幾人。全職電影人不少都得北上搵食,留意拍本土電影的好些導演,其實沒有全職投入拍片,像陳詠桑(《逆流大叔》)、黃浩然(《點對點》)、黃修平(《狂舞派》)、周冠威(《幻愛》)的正職都是老師。
黃修平沒有做全職電影人,而每幾年一齣作品,我們來看看新作《狂舞派3》。2013年《狂舞派》上映,在坊間造成不少討論,氣氛頗為熱烈,其實影片在拍攝、敍事、人物描寫上都未算成熟。那年電影上畫宣傳做得實在好,一句「為了跳舞你可以去到幾盡」,配合那年頭的社會氣氛,在年輕群眾之間的確受落。回顧近十年港片,2010年《打擂台》、2013年《狂舞派》都寫勵志(2018年《逆流大叔》寫中年勵志),到《一念無名》(2016)、《淪落人》(2019)關注弱勢社群,都幾乎捨棄了港產片最擅長拍攝的類型創作,在某程度上反映時代氣氛。製作雖小,但靠主題和一股衝勁、精神,仍能吸引到觀眾。
首集《狂舞派》不是沒有類型元素,但戲中的舞蹈──水平沒西方歌舞片的勁,戲中加入一點喜劇、一點愛情元素,觀眾也算喜歡。但回到現實面,電影預算500萬,票房也才1,300萬。如果回到電影工業的討論,像黃修平這個創作效率,幾年一齣戲,根本養不了他,其實是教職養活了他,再加上電影發展基金等資金來源,才能讓他滋滋油油的拍自己喜歡的題材。也因為他有穩定生活,足以糊口,才能完全捨棄《狂舞派》的成功,全新出發去拍《狂舞派3》。
當年《狂舞派》勵志,黃修平承認在片中刻意抽離現實元素,戲因此變得熱血又好玩,但同時帶點天真味道──他常自嘲離地,這是作為九十年代文藝青年的口味。黃在中大藝術系畢業,大學時是電影學會主席,但他笑言當年最想做的其實是「拍攝電影學會主席」,他最大的興趣,就是拍攝,不管預算有多少。這樣的一個狂熱電影人,最終竟然沒有全身投入電影圈,他只在年輕時在電影公司拍攝製作特輯(Making of)。早在中學年代,同學們看王晶的《精裝追女仔》,被他嘲笑,因為他已在看進念,看Derek Jarman,跟一班自命不凡的朋友混在一起──這句顯示了他自己也自命不凡。那個比如今洋化得多的八十年代,《號外》充斥着中英夾雜的文章,總有年輕人看完《號外》,看粗糙獨立製作的《年青人周報》,腋下夾着一張英國獨立樂隊黑膠。
年少的黃修平就是這種文藝青年。在舊日香港,這種人日後一是從俗,走入主流、在自己的眼光跟大眾眼光作出協調,像鄭中漢(鄭中基父親)在當寶麗金高層之前,是香港Band壇傳說中的三大結他高手,玩西洋搖滾。黃修平是另一種人,自言做不了不喜歡之事,這種自我認知,令他再喜歡拍片都不會全身投入影圈。說《狂舞派》成功,票房也不過1300萬,已是他歷來最高票房。文青拍片,根本不怎計算票房。他再拍《哪一天我們會飛》(2015)的規模較大,甚至本來想拍成合拍片,但戲中寫八十年代的部份殖民色彩太濃,過不了第一輪審批。當年電影上映,有觀眾認為這是港人的《那些年》,這可算是他與商業類型最接近的一次。但電影始終沒有賣座元素,票房1,100萬,比《狂舞派》還要少一些。電影也不算出色,那是後話。
黃修平說,七年前就有觀眾問他影片會否拍《狂舞派》續集,他對這個期待是感恩的。但若翻炒橋段再下一城,他自覺就是墮落的開端,因此開始撰寫劇本時,完全放棄了第一集的所有角色。事隔七年,《狂舞派3》直接跳過續集,主角不再是為了跳舞可以去幾盡的阿花,和耍太極戇居傻氣的柒良,而變成了演阿花的女演員Hana、演柒良的YouTuber阿良。阿花(顏卓靈飾)是因電影上映開始走紅的新晉演員,因為有點名氣,做事開始要顧及形象,也同時因為忙碌及審慎被舊日跳舞的隊友白眼,阿良(Babyjohn飾)更慘,上集傻傻討好,今集由夢想拉到現實的阿良,每到一處都在直播自拍,自戀又計算,幾乎成了反派。這個構思,他自言來自杜魯福的作品《戲中戲》(Day For Night),戲中拍一班電影人在拍戲,同樣真假混雜,疑幻疑真。
《狂舞派3》是群戲,主角還有真的在香港嘻哈界頗為活躍的Heyo、阿佛,二人在戲內戲外名字一樣,只是劇情有真有假。另外,還有Hana男友Dave(Mirror隊長Lokman飾)和跳舞老師奶茶(劉敬雯飾),最有趣的是一個跳街舞的角色,叫做佳仔。故事主線寫《狂舞派》成功後,地產商見獵心喜,在工廈區弄了一條「狂舞街」,找來《狂舞派》的一眾演員宣傳。面對現實,眾人各有抉擇,有的視之為機會,全面配合,有的不滿朋友墮落。戲中建構了一個「龍城區」(即觀塘),由上集夢想拉到現實,寫工廈創作人即使電影成功,每天仍然要面對現實的磨練。劇情假作真時真亦假,論創作勇氣,相當可嘉。
即使《狂舞派3》由夢想拉到現實,但戲中描寫的現實還是太幼嫩,並不深刻。戲中寫Heyo為了省租金,住在工廈卻不敢示人。電影寫地產商炒作狂舞街,找眾人宣傳,飾演反派,而至最後成眾矢之的,也還是簡化了問題。香港信奉高度資本主義由來已久,如此刻畫實屬老生常談,也欠深刻反省。另一邊廂,故事描寫女演員Hana拍拖不敢公開,跟娛記說話謹慎,對人歡笑背人愁,對狂舞街計劃越來越不滿等劇情,更是直白浮淺。比較好的一段是Heyo接了狂舞街宣傳,惹來好友阿佛不滿,後來阿佛為了發洩不滿,針對替狂舞街拍YouTube片的阿良。阿佛不滿這些工廈創作人出賣自己,逕自走到紐約Bronx,去訪問那些嘻哈老祖,拍成YouTube片,以牙還牙,直線抽擊阿良。這段故事,劇組真的飛到了紐約,約好了真有其人的嘻哈祖宗們做訪問。訪問是真的,但用在戲劇上,把既真又假的觀影經驗,推到極致。
有批評指《狂舞派3》劇情鬆散,其實文青拍片從來不重視劇情結構。而且黃修平的意圖,大概是想拍出工廈區創作人眾生相,倒是中後段回到故事主線,為了推上戲劇高潮,寫他們面對金錢誘惑(狂舞街計劃),眾人怎去面對,最後一場眾人在場中大鬧,雙方推撞,一眾工廈創作人全部歸邊,加入搗亂,還是再一次浪漫化了現實(如果他想拍的是殘酷現實)。
去年的台灣片作品多,水平高,頗受矚目。跟一個早前到過台灣了解的導演聊起,他大讚風氣很好,慨嘆香港開戲的,還是那堆年紀老邁的舊人,寶島影壇,真的有把拍片機會讓給年輕導演,而成績都也不錯。他說台灣拍片制度日漸成熟,也有計算,一般電影預算都不超過4,000萬台幣(《返校》過億是特例),像金馬最佳影片《消失的情人節》成本就是4,000萬。《消失》導演陳玉勳今年58歲,拍了二、三十年電影。在舊日台片走藝術片方向時,他是另類,因為只有他在拍喜劇(類型)。往日他遊走在藝術與商業之間,不知怎樣自處,但今天看到台灣年輕人都在拍類型片了,很感到開心。的確,像許承傑拍《孤味》是家庭倫理片,票房就達1.8億,這一個若能持續,就是工業。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往日在港片最黃金的年代,侯孝賢、楊德昌在拍藝術片,被台灣一些評論大肆攻擊,直至作品漸漸在國際得了獎。今天回看往日,只有好作品能夠長存,也沒有誰敢說「沒有電影工業」的那段日子,台灣電影沒有成就。近兩年看金馬奬,感覺是台灣因為沒有經歷過拍電影賺大錢的年代,拍戲沒有以盈利行先,電影反而像一個終極影像殿堂,大家一比高下。
吳念真被稱為台灣最會說故事的人,是台灣新電影其一一個代表人物,前幾年訪問他,他就直言台灣二千萬人太少,他們計過,人口最好一億才養得起一個電影工業。吳念真奇怪年輕人都認為電影比較偉大,他就不那麼認為。於是他放低電影,去了搞話劇。吳念真從前寫的劇本很多都變成了藝術片,但他搞舞台劇從不避通俗。他執導的舞台劇當然受歡迎,據報現場每每有人看得淚涕並流,這麼說,他搞的舞台劇是屬於類型。
香港電影最「黃金」的年代,電影圈的價值是單元的,賣錢的導演才能開戲,於是才有了楚原那得獎感言(2018):「我破了香港票房紀錄,老闆馬上跟我簽了新合同,人工加了十倍,個個都說我是香港最幸福的導演。十幾年後,我的電影不賣錢了,拍完幾部仆街片呢,我想拍《天龍八部》,開鏡前一天方逸華撕了通告,不畀拍。入了Office她說:蝕了錢,由你來賠?最後兩句她說:楚原,你根本不懂電影藝術,你根本不懂電影。那時人人都話,我係邵氏公司最難堪的導演。」我們擁有過東方荷里活的稱號,年產幾百部電影。但同時在這樣的制度下,香港又出過像陳果這樣的奇葩,他最好的幾齣作品的藝術性,拿到全世界都不輸。
黃修平《狂舞派3》拍了1,200萬,以往績或影片類型計算,不大可能收回成本,更別說賺錢。幾可斷言,他不是屬於電影工業的。但那又如何?如果作品回應到社會,帶來思想衝擊,一切是不是就值得?新一代電影人是多元的,2019年新導演作品中,拍得最類型、有商業潛質的是黃綺琳的《金都》,但她票房只有500多萬。周冠威《幻愛》開畫票房慘淡,但最終收了1,500多萬。這兩齣都是愛情片,預算有限。愛情片成本有限,只要有好故事、俊男美女好演員,永遠都有觀眾,是電影工業的一個類型。
談夢想也很容易浪漫化。工業可不是隨口講,那是專業。天天操練,做到極致,才可能跟全世界競爭──數碼年代,你就得跟全世界競爭。在Clubhouse聽過一個電影人說,有次在海外談合作,對方直言:「其實我們不大需要香港作品。」他聽到後心頭一沉。談電影工業死或不死,不能逃避問題,對自己不誠實。尤其在2020年後,難當然很難,但若要問香港電影工業死或不死,死了沒有。都未斷氣,鬼知咩。未斷氣就要繼續做,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