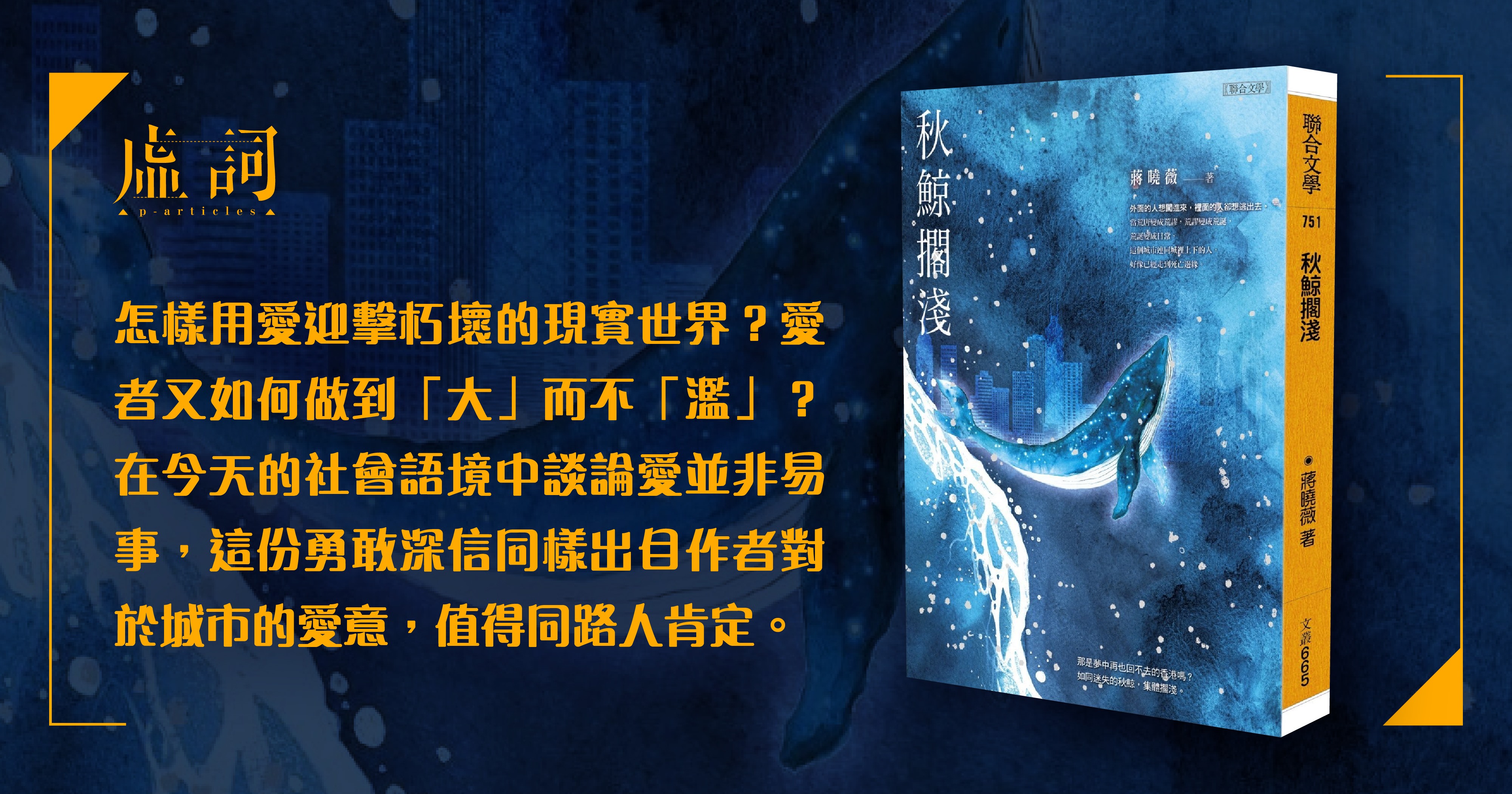荒謬當道,愛如何拯救之?——讀蔣曉薇《秋鯨擱淺》
書評 | by 張錦泉 | 2020-11-06
三年前在沙田大會堂觀賞完蔣曉薇的劇作《秋鯨擱淺》,步出劇場後仍覺得意豫未盡。幸好根據作者前一部作品《家.寶》的出版過程,小說版《秋鯨擱淺》指日可待。當劇場版的故事在腦海中已日漸模糊之際,今年九月小說版《秋鯨擱淺》剛好在台灣面世,深藏的回憶再次被呼喚,而這次讀者是透過小說文字分享作家對於香港乃至文學的思想與感情。
董啟章把《秋鯨擱淺》定位為「本土情懷書寫」,「情」固是小說的基調,但筆者卻比較關注與「情」相近而不盡相同的「愛」這一小說主題。蔣曉薇在不同作品和訪談中已多次解說自己如何深受卡繆的存在主義思想影響,在《秋鯨擱淺》中小說人物不只多次直接談及卡繆的作品,小說正文開展之前,作者也徵引了卡繆的名句作為題辭:「荒謬當道,愛拯救之。」頁底是香港島維港沿岸的典型建築群剪影。文字與圖像的配搭引起讀者忖思:在香港這個近年被認為荒誕變成日常、荒謬當道的城市,愛又如何能夠拯救之?小說人物 Fred 說的「Love can save it all」,此話當真?
《秋鯨擱淺》的故事圍繞中學教師游敏兒、新移民學生蘇月秋和上一代社運青年楊帆立三人及其家屬好友而發展,透過這三個不同年代的人物在當下香港的相識、碰撞和互入,小說一口氣論盡了英國作家C.S. 路易斯(C.S. Lewis)在《四種愛》一書中談及的親愛、友愛、情愛、大愛。其中最觸目的人物關係應是游敏兒和蘇月秋之間亦師亦友,接近同性之戀的複雜關係。人物互動背後所牽引的則是由中國大陸、香港、世界(小說以台灣和紐西蘭為主)三者構成的複雜龐大的空間網絡。小說從這兩位不同生命處境的「異鄉客」之目光來呈現當下的香港社會狀況,展開對於原鄉議題的思考。不過,比起「禁忌之戀」、香港教育生態等議題,筆者認為小說人物在介入他者生命的越界過程中產生什麼變化,「愛」的力量之火是否真的能夠重燃灰闇人間,小說談論的愛又是哪種形態等問題,是進入《秋鯨擱淺》的關鍵所在。
要回應關於「愛」的問題,首先需要聚焦在蘇月秋這一人物身上。從蘇月秋剛到香港時對城市的感受,到她在學校受到本地學生的歧視和欺凌,小說明確展現出香港和中國大陸兩種生活文化、價值觀念之間的分野。直到蘇月秋在無意中破解了老師游敏兒在中文默書堂上留下的「密碼」,借助可能是從岩井俊二《情書》電影轉化過來的傳遞書信之方式,得以走進游敏兒的世界時,蘇月秋才獲得被「救贖」的機會(對應於新移民身份的「原罪」)。及後,游敏兒為蘇月秋安排港產片放映會,又陪伴蘇月秋遊逛旺角和光顧傳統香港冰室,以舊式的、有點接近教科書模式的文化符號讓蘇月秋有機會進入(過去的)香港環境。作者非常用心地塑造蘇、游二人的關係,把她們的相遇和關係之間漸生愛意的過程娓娓道來。不過,除了比較易受人注目的蘇、游二人的關係外,筆者認為蘇月秋和同班同學葉卓靈之間的友愛互動也是另一個小說表現人物跨越差異的情節設定。蘇月秋和葉卓靈的相遇已突顯了二人在政治意識上的分歧,但是敘事者又憑藉「卓靈」一名的讀音暗示這個角色將會成為蘇月秋在香港校園中的好友。儘管葉卓靈也曾經因為其他學生欺凌蘇月秋,或學生之間傳播蘇月秋和游敏兒發展同性師生戀的謠言,一度誤會了蘇月秋。但是後來葉卓靈不只在化解蘇、游關係謠言上有功,並且在蘇月秋陷入精神低谷乃至自殺後,也對這位新移民好友的狀況表露深深的憂愁與悲傷。縱觀整部小說,葉卓靈與蘇月秋之間的關係也是隨著時間推進而變得越來越緊密。相比騷華、肥軒等其他香港學生的扁平形象,葉卓靈的人物形象反而比較立體,並且展現出她對於蘇月秋的接納和關愛。
法國哲學家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把「愛」視為哲學的根本「條件」之一,愛和科技、政治、藝術同屬為通向「真理」的其中一個程序。在巴迪歐對愛的禮讚論述中,愛由兩個個體的相遇事件所開啟,不同的個體藉著愛的宣言由原本的「一」(Un)合體成為大寫的「二」(Deux),從「一的場景」進入到「二的場景」,當中的意思是指人不再是獨體,差異被插入到原本的同一之中,構成新的世界。值的注意的是,巴迪歐所說的「二」的合體並不同於黑格爾的「辯證性綜合」,後者是從打破個體自戀的愛,走向一個包括他者的整體的愛(如婚姻),但是這只不過是用新的統一體來取替原本的「一」。巴迪歐的「二」更接近於德勒茲的「離散性綜合」,在「二的場景」中個體得到對於絕對差異的主體性體驗,建構起愛的主體,由此可以從一個去中心化的「二」的視域重新審視世界。在愛之中,愛者眼中不只看到對方,而是從差異性出發來重新看見和建構世界。因此在巴迪歐觀念中,愛不只是兩人之間的關係,它更是生命的和世界的重新創造,時常保持著打破「一」的激進姿態。
回到《秋鯨擱淺》,游敏兒代表的香港人正面對中國內地在經濟、文化、政治權力的強勢侵蝕和輾壓,因此在移情作用下騷華、肥軒、林老虎、茶餐廳老闆娘等人均表現出對於新移民的惱恨。但與此同時,葉卓靈和蘇月秋之間卻一直顯示二人能夠發展成熟的友愛關係,透露出從差異性視閾出發來建立屬於「二」的新世界之可能性。不過可惜的是,作者似乎過於側重游敏兒和蘇月秋的關係發展,無意進一步刻畫蘇月秋和葉卓靈或其他本地學生故事線。當然,作者這樣決定故事走向的原因也不難理解:一來小說不只要描繪新移民在香港的融入情況,還要呈現土生土長的本地人難以面對香港在回歸以後的變化;二來小說顯然不想局限在中港關係的格局之中,企圖連繫到不同地域甚至不同物種,最後表達一種類近於萬物大同的哲思。在這種思考方向下,作者在小說中設計了一個頗精緻的「月亮式」敘事結構。月亮不只是人物情感的指涉對象,故事的發展和推進也依照著月圓、月缺的邏輯進行,呼應人物的相聚、分離和復合。小說最後揭露月之圓缺從來都是人類的主觀想像和情感投射,以恆久不變的月圓狀態呼應卡繆筆下快樂的薛西弗斯精神,而月亮之「圓」也呼應小說人物屢次提及的「共同體」概念。不過,儘管小說結尾似乎帶出了突破文化身份對立的意識,例如透過游敏兒與其愛國父親的關係、楊閱與楊帆立的父女關係等親情之愛,來表現人物願意建立類似「二的場景」的意向,但是人物的意願只屬於行動的開端(如游敏兒重返香港和家庭),而且這個看似附有愛之精神的「生命共同體」到底是屬於巴迪歐的離散性綜合之「二」,還是黑格爾的辯證性綜合之「一」,在小說中仍是未知數。故此嚴格而言,小說到最後是否真的體現出愛對於整體荒誕世界的拯救力量,令人產生疑惑。
相反,蘇月秋因為承受不到游敏兒離開而割脈自殺一事恰恰表現出浪漫之愛的危機。蘇月秋和游敏兒的相遇、相識和相愛的過程,本來反映著兩個不文化背景、政治信念的人,在香港的荒謬社會裡同樣能夠成為彼此的安慰和救贖。可是當兩人的感情昇華到至高點時,游敏兒卻赫然拋棄一切離開香港。如果只集中在游敏兒的故事線,她遠走紐西蘭當然有著充份的理據,但她沒有為蘇月秋留下隻言片語,甚至讀過蘇月秋的信(愛的宣言)後才驚覺女孩對自己的愛慕之情,這卻與前文描寫二人的親密互動和情感產生斷裂。即使作者有表達游敏兒內心的愧疚,游敏兒默然無聲的出走可能為要鋪墊後文表現出「離開是發現深愛的方式」這一套觀念,這個轉折仍然使小說人物的形象變得前後不協調。當讀者以為港產片放映會、港式茶餐廳體驗能夠幫助蘇月秋進入香港社會的文化語境,改變她原初對香港的偏見,以為蘇月秋能夠透過對游敏兒的愛學會接納雙方的差異性,並且有機會創造新的世界觀時,最後發現原來那些體驗只不過加強蘇月秋對游敏兒的仰慕和依戀。蘇月秋渴求進入的是游敏兒的個人世界而非香港。這仍是巴迪歐所說的「一的情景」(游敏兒成為蘇月秋心中英雄主義式的情結中心),而非能夠開拓生命視野的愛情的「二的情景」。巴迪歐極力主張要拋棄蘇月秋這種浪漫主義式的神話,因為它只會帶向死亡,而非新的世界。另一方面,誠如董啟章在《秋鯨擱淺》序言中所言:「作為例外的蘇月秋,似乎沒有改變游敏兒對於新移民的普遍看法——一批改變香港文化而不是融入香港文化的外來者。」縱觀整部小說中游、蘇二人的互動,我們不難看到蘇月秋一直處於被啟蒙者的位置,接受著游敏兒、楊閱、楊帆立等「啟蒙者」的引導。可是這個啟蒙、引導意識,令人不禁揣測其背後會否是另一個大的「一」,而非包含著差異的「二」的世界。這樣的話便進一步確證董氏所言,游、蘇的關係未能為解決社會問題帶來啟示。
筆者認為《秋鯨擱淺》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在於小說敘事過度投入在浪漫情懷的建構之中。從《秋鯨擱淺》的序言和後記可見,作者對於小說甚至個人創作的浪漫意識具有高度自覺。小說的主要人物一律寄情於文學和各類書籍,他們都是文學藝術的大愛者,文學也順理成章地充當人物溝通和連繫的媒介。加上小說加插大量典故和童話,常常以互文方式表現人物情緒與生命處境。這些引文和書介式文字怎樣影響《秋鯨擱淺》整體敘事節奏和人物形象刻劃,是另一個可以再作探討的論題,但它們無疑為故事敘述塑造一種浪漫化的氛圍。小說不單單展現作者對於文學、書籍的濃厚愛意,更把這種文學之愛化作小說人物在荒謬世界中或保存自身,或獲取抵抗力量的途徑。
不過,文藝可以成為抗爭者的精神砥柱,同時也有可能成為人們逃避現實的方便之門。游敏兒和楊閱能夠從社會、哲學書籍中認清現實世界的實相,從卡繆的作品中攫取與荒謬抗衡的動力。甚至當楊閱仍處於昏迷時,楊帆立透過「說書」來建立和女兒之間的感應方式,以文學、文字進行一次次的「招魂」儀式。但是另一邊廂,蘇月秋在面對生活環境的迭變時雖然能夠在文學中覓得心靈慰藉,透過圖書館空間建立了和游敏兒、楊帆立等人的生命關係,她卻沒有在文學中找到面對現實的力量。蕭紅的飄泊身世讓蘇月秋感同身受,但是蘇月秋並未能建立起像蕭紅那般獨立自主的堅毅意志。對文藝的大愛果真能夠成為身處荒謬現實中的救贖嗎?筆者認為《秋鯨擱淺》給予的是既肯定又否定的回應,關鍵在於文學閱讀者能否創造文本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連接,而非像蘇月秋般沉溺在浪漫、神秘的意識世界之中。
愛和浪漫的結合,也使《秋鯨擱淺》後半部分的故事走向具有神秘色彩的意識世界。上半部分的小說敘事仍然能夠從不同人物的視角出發,觀照香港的現實環境,儘管他們的視角偏向單一和負面。相比之下,小說後半部分內容卻漸趨虛幻化,在「黑潭」的那一段情節更使讀者產生各種故事設定上的問題:黑潭為何突然出現倒塌危機?那一尾兀然出現的鮟鱇的象徵意義為何?如果三位主要的女性角色可以在夢中溝通,那麼她們與各自父親的問題又是否可以藉夢境的連結來解決?筆者能夠理解小說後半部是要表現主角積累大量傷痛、壓抑、悲愴後,藉著夢境「深潛」到意識空間中感受與萬物的連繫,重覓突破現實困境的力量。可是當敘事過於依賴潛意識的迷幻世界,欠缺現實作為人物頓悟和蛻變的基礎,只會使那些具有強烈反思性質的人物獨白變成喃喃囈語。即使小說最後可以靠作者清新流麗的文筆來支撐,故事也難以挑動讀者的共鳴。加上《秋鯨擱淺》也有過於依賴人物言說的情況,在浪漫情懷下人物的言說方式像是發表一篇篇生命宣言,這或許是小說受到過多戲劇層面的影響。這種人物說話的方式即使偶爾能夠使讀者感到痛快淋漓、感動莫名,但是大量的直接抒情和直白宣言在後半部分卻使人漸漸覺得沉重和疲累。
《秋鯨擱淺》的故事結束於游敏兒重新回到香港,準備正面對抗日漸異化的社會環境和已成夢魘的父女關係。蘇月秋則取替了楊閱的位置,成為另一位在意識空間「修復」自身的人物。月缺月圓仍有規律地變化著,但生命已經在圓缺中不斷移位和成長。離開或駐守,衝鋒陷陣或潛藏養晦,同樣出於愛。巴迪歐談到愛和藝術的關係時曾言:「重要的作品,宏大的小說,則往往建構在不可能的愛之上,愛的體驗,愛的悲劇,愛的破裂、分離、終結,等等。但是,關於愛的延續,卻總是言之甚少。」蔣曉薇在《秋鯨擱淺》中展現了多種愛的模式,其中不乏真知的靈光。雖然最後小說選擇停留在以愛作為個人面向荒誕世界的內在精神動力上,本文所思考的「愛之拯救」在小說中暫時仍然停留在個人層面,未能向社會的深層問顯挺進。但是這或許也可視為一個起點,這起點既指向對愛的思考上,也指向作者的小說創作。事實上,愛如何延續?怎樣用愛迎擊朽壞的現實世界?愛者又如何做到「大」而不「濫」?我們確實不能苛求小說一一解答,這是每一位有感於香港的人要自行思考的問題。在今天的社會語境中談論愛並非易事,能夠迎難而上,足見作者的勇氣,這份勇敢深信同樣出自作者對於城市的愛意,值得同路人肯定。職是之故,除了把《秋鯨擱淺》稱作「本土情懷書寫」外,筆者更願意視之為一部寫給文學和舊日香港的「情書」,也是一篇對於未來香港的「愛的宣言」。重點是,在未來的日子愛與文藝能夠帶領我們走到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