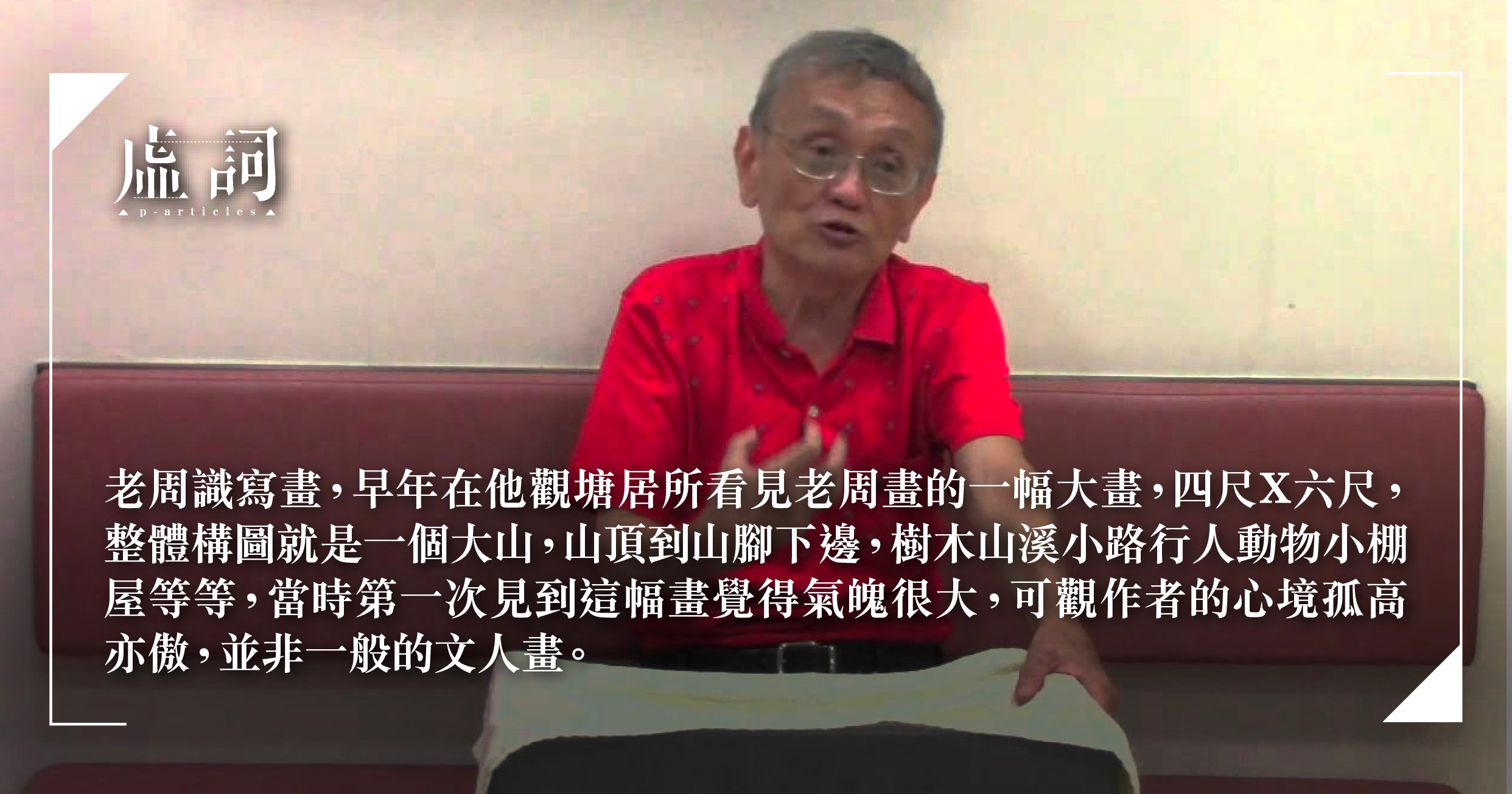悼周魯逸:香港最後一個毛左
故友周魯逸在東莞樟木頭逝世,消息從當地友人的網上得知。老周是獨來獨往的文化人,50年代60年代後生的香港一輩文化人,多會知其名,浮生拾紀,頗念故友,亦不失為一代讀書人的一些寫照。
老周用筆名魯凡之於八十年代報刊寫文章,在下1981年任職財經日報總主筆兼編副刊,老周是作者之一,好學深思人,也是當時愛長篇大論,談述南美新左派馬克思主義的作者,總是什麼葛蘭西一大堆,哈派馬斯啦位置之戰,也貫徹于他和馮檢基搞的民協。新左思潮歷來在大學的理想主義青年堆中有些市場,老周有鋪做青年導師的癮,尤其他是中國式的毛左民族主義者,長期思考便往那條方向去鑽,他的筆耕,同路者便視為文化清流,貫徹始終。
當年處理老周的稿也很頭痛,就是引號「」特別多,並不屬於好的文字。雖然他是毛左,其實到當時毛澤東的思想已沒有什麼好談的了,時值開放改革,老周對當年的農業承包制什麼一大堆的確花了功夫,鄧小平趙紫陽的一套,現在都成為歷史陳跡了。
老周讀師範出身,沒有長時間教書總是東奔西走跑單幫文化人,也遊學過巴黎,王耀宗兄時也談到他們歐洲生活過的時光。老周是戰後一代生的民族主義者,對中國古代歷史文化就有着基因性的執着,但我觀察是毛左那一套蓋過他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晚年住進內地更樂此不疲。黎則奮說周是香港最後一個毛左,只對一半,七八十的毛左老頭仍不少哩,只是遠沒有老周書呆,教條頑固則老樣貨式。只消看兩端已可蓋其餘。
老周愛談自己五十年代已是天生的民族主義者,拉扯父輩怎地山河歲月亡身南北,肯對我深談是因同于此道,那些輩代又幾乎必然是毛澤東思想青少年,又必然反殖(後來作深層理性思考)。他崇毛到一直為文革尋找善良動機的解釋,這也是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不可救藥通病,有天的文稿,內文還講毛澤東那套,居然還寫出願為天子門生。我當時一看內心不屑笑不合嘴,有鋪咁嘅癮真難頂!但老周很能夠講,有一晚他和曾澍基教授(已身故是我們那代有能力當經濟大師的人),彼此就馬克思裏面談政治經濟的一個論點,辯論了足足有40分鐘,全過程完全不停一句接一句,說話的速度也快,那種流暢程度和記憶力,我們坐着的幾個朋友真是嘆為觀止。
老周識寫畫,早年在他觀塘居所看見老周畫的一幅大畫,四尺x六尺,整體構圖就是一個大山,山頂到山腳下邊,樹木山溪小路行人動物小棚屋等等,當時第一次見到這幅畫覺得氣魄很大,可觀作者的心境孤高亦傲,並非一般的文人畫,卻寫着作者自己對理想桃園的憧憬,不能用好或者不好來形容,也確實創作。顯然老周在師範是讀藝術的,故人已去,老周安息!又聽隣童吹笛,那年代同輩友人又少一位了。
(文章轉載自《透視報》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