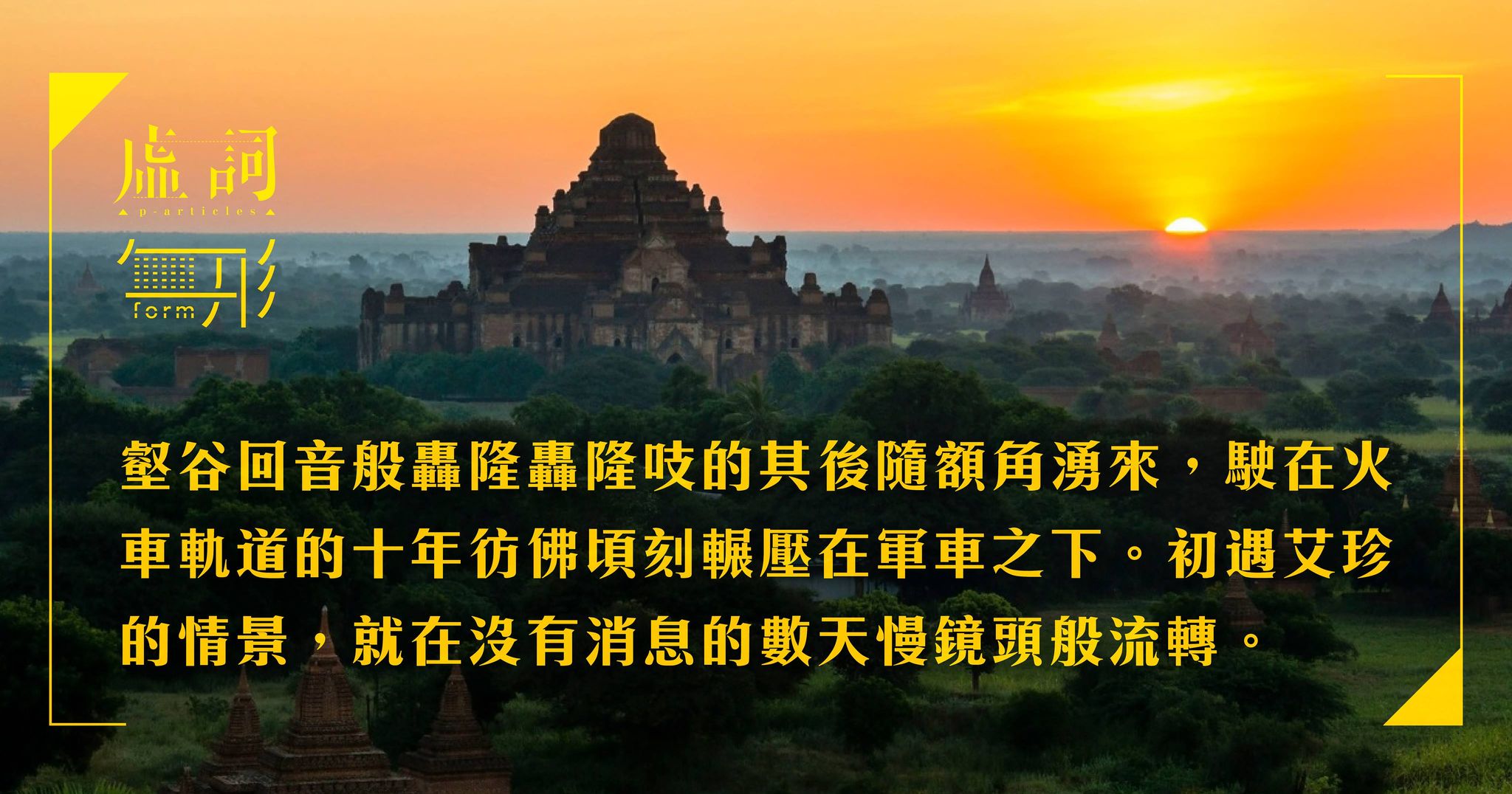【無形・致死難與抗爭,緬甸】緬甸雜憶
準備踏入二月的前一個晚上,我還在社交媒體上看見艾珍當日的動態,她在仰光以北勃固的某個城鎮,帶著朋友沿伊洛瓦底江遊覽故鄉,照片上如常的悠然從容,由是翌日讀到新聞報道傳出軍方發動政變,影像之反差讓人霎時錯覺是則玩笑。壑谷回音般轟隆轟隆吱的其後隨額角湧來,駛在火車軌道的十年彷彿頃刻輾壓在軍車之下。初遇艾珍的情景,就在沒有消息的數天慢鏡頭般流轉。
那個下午我在象徵仰光甚或整個緬甸的佛塔大金塔內遊晃,繞著金光閃耀的大塔蕩了幾個圈,直至塔的四周漫漶成晚霞的橘藍,地面從腳底傳來一陣微冷,始慢慢從席坐地上前來拜佛的信眾間找個位置,坐下。邊旁同樣是低垂的頭,有些雙手合十不顧周邊紛攘步履靜靜的誦著經祈著願,不遠處也傳來一眾女子唱經的聲音,是聽著會讓人淚水逕自滑落的清寂。我從未聽過如此能洞悉人情又撫平內心蕪雜的音韻,是以當我走向更近聲源的位置坐下、艾珍朝我這邊來打招呼時,當刻更渴望的或是讓這緬文唱經聲滌洗深處的什麼。可後來和艾珍聊天的舒心安全又讓人難以拒卻,如我心中典型的緬甸女子般她善心而腼腆,彷彿想挨緊碰觸人心裡什麼,卻又緩緩的讓自身安放。剛搬來仰光的她是個年輕的英語教師,因得一所學校聘書而從勃固小鎮搬往大城,安靜的她朋友不多,教學中心亦離大塔不遠,因此她幾乎每天來漫步,順道練習英語。
大概像許多當地人一樣,艾珍虔誠,篤信善惡有報,在勃固的家人每年總會供奉小錢到佛塔寺院,讓小沙彌或僧侶們的修習不間斷。她每天早上亦會四處送食物予街上的貓,這是她視之為日常的小佈施。像我路途上遇過的每個不拘小節的緬甸人,他們恍若以助人為樂。有一次我在舊蒲甘看佛塔看膩了嘗試驅電動摩托車前往新蒲甘時,可能是我膽怯一直靠邊駛,竟遇上沙粒積厚的一段路踉蹌地連人帶車翻倒。儘管我立時提起身把車拉起,本來往另一方向行走的路人卻調頭來幫忙把車推往行人路上,更駛至他們住處。即使身上無傷,仍堅持讓我歇腳再上路,彷彿他們正前往去辦的事無關重要,時間長得像日出日落般蔓生至山的邊緣。
像不少國家的男子一生總要服役當兵一次,在緬甸,男子一生必要做的事,是到寺院當僧侶過一段靜修日子,寺塔長廊於他們而言像是通往成人禮的時光隧道。不知是否因此,感覺他們格外敦樸閑靜。我在曼德勒南面阿馬拉布拉的千人修道院遇到的年輕僧侶,在觀看信眾佈施僧侶列隊領飯的人潮散去以後,與我聊著寺院的生活時說,每天早上四五時醒來,吃過早點後讀經,有時上課聽道,而為守著午後不用餐的戒法,約十時多再用餐一次,然後基本上是靜修休息時間,其間只喝水。未過二十歲的他待在寺院逾六年,言談間盡是對外面世界的好奇,一直在問我關於香港的事。倒問他為何不還俗?他帶著稚氣的笑容說住在寺院裡,其實也可以外出。
那天在暗藍天色下我和艾珍分別以後,沿路也遇到一個前來搭話的緬甸人,暗夜裡我同樣感到他們亟欲與外間連接的訊號,他說順路能陪我走往民宿附近的教堂,便一同從大塔下直往南走。遙遙路上,他邀我到一家路邊攤坐下來喝茶歇腳,並開始談起年輕時跟隨老闆到訪亞洲各地的往事,說著住過怎樣的酒店,遇上如何熱情的人,我邊聽邊在嘴裡嗒著面前一杯小小奶茶,回味幼時初嚐母親同樣放在銀壺裡煮的奶茶,同樣加入煉奶,過份的甜,與港式奶茶不同。我們顯然回味著各自不同的過去,在紅紅綠綠的塑膠椅子間,藍綠帳篷內的白燈光照射下,我突然想到這種在仰光大小街巷能找到的路邊攤,不就是當地最能讓人促膝聊談的咖啡廳嗎,(或是說奶茶廳)。
距離上次踏觸緬甸的日子久遠,許多細節像遺落在坑塹裡迷濛,在回溯的過程中我一直想著,在如此凝滯的純真世界裡,艾珍篤信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會否終如所願,如熬過的多層茶香,回以甘甜。但願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