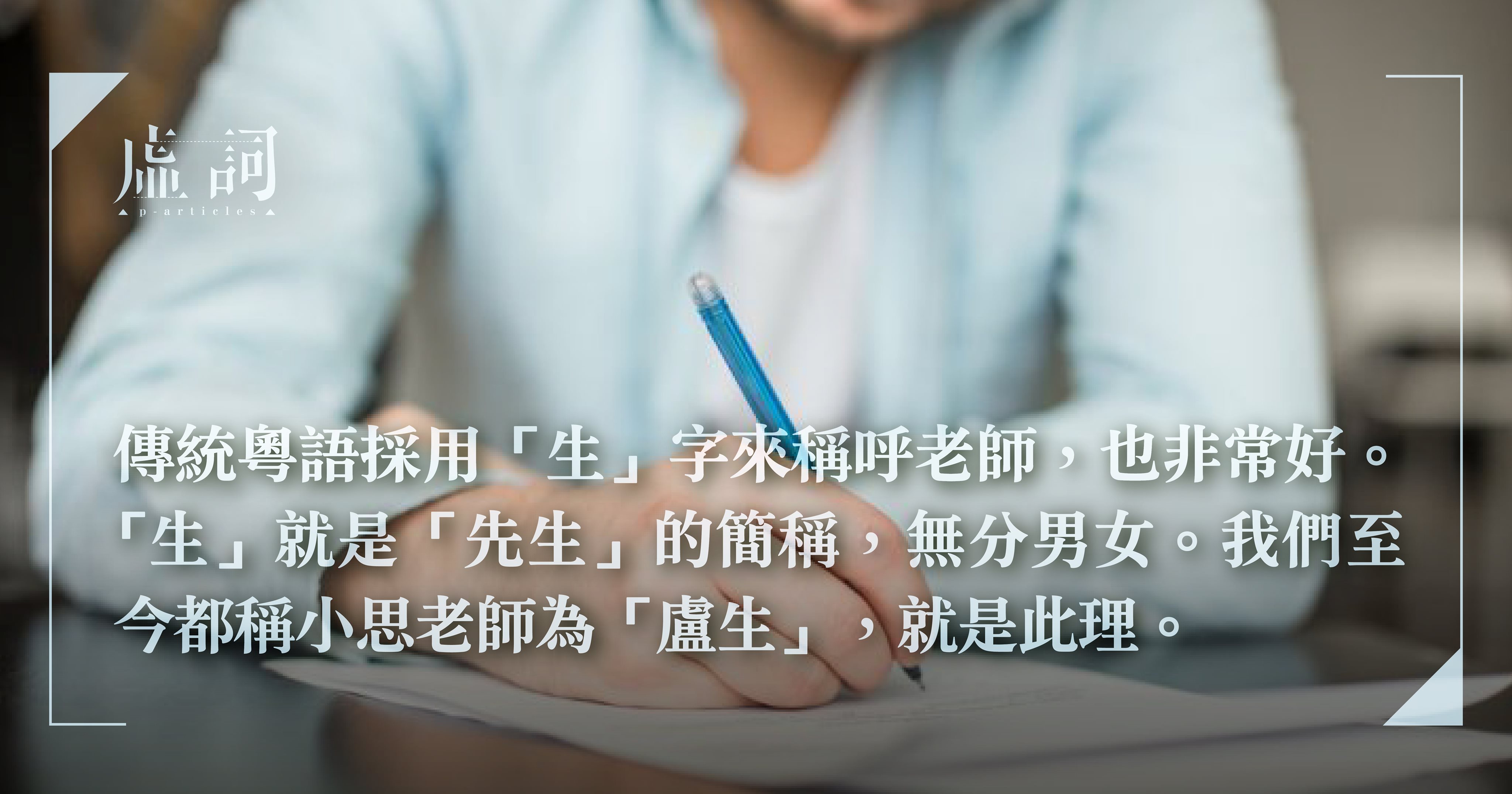寫信稱兄道弟的禮數
我有一位師弟說:「在歐洲(尤其是耶教體系和英國)是非常講究Prefix(禮節稱謂)和相應的祝語的。不過美語就比較隨便。傳聞當年甘迺迪總統面見英女王錯稱王夫為『Your Royal Excellency』,被王宮侍官暗笑無知。」傳統歐陸那種講了三分鐘還沒講到句號、聽者也不知道主語在哪裡的老式英法德意西俄語,老美必然覺得很麻煩。不過,因為美式簡易,就誤以為一切西式稱謂都很簡易,乃至動輒批評中式稱謂為繁文縟節,這未嘗不是出自一種「圍城」心態。
回到正題。前文談到信件的收件語和提稱語,本文再補充幾句。由於對行文稱謂、格式的不熟悉,乃至於中西格式的混淆,往往會出現一些錯誤。正如我們說過,「惠啟」、「惠鑒」、「足下」等用語,既可用於平輩,也可用於晚輩。但用於晚輩時,是為了拔高對方的輩分以示尊重,那麼收件者理論上也應該意識到這是一種抬舉。
這種情形,有點像中文學界對「兄」字的運用。年齡相仿者,固然會互稱為「兄」(哪怕是稍長對稍幼者),但年齡頗有差距、乃至輩分不同者,也可能用到「兄」字。最常見的是,學者往往將並非自己門下的學生、後進(自然也不會太親近)稱呼為「兄」,但對方理應神會心領,不會以「稱兄道弟」的方式來「回敬」。
個人經驗,也許因為我平生第一次收到「兄」之稱謂的信件是來自一位年高德劭的學者,所以自然而然就開悟,知道「兄」字是不能亂用的。不過,我真聽過一些關於師生間「稱兄道弟」的笑話。如以下兩則:
其一:某師寫信予某生,稱生為兄;某生回信,呼師為弟。
其二:導師致函學生,抬頭稱「某某賢弟」。學生閱後激動流涕道:「老師竟然和我兄弟相稱,我博士了!」
無可否認,有些人際關係的親疏很難拿捏。因此我覺得在中文學界內,最簡便的方式便是稱呼「老師」。長輩固然受之無愧,平輩、晚輩也無妨,因為可以依從他們的學生之口吻,一如妻子以子女口吻稱丈夫為「爸爸」。如此便皆大歡喜。何況就教育事業而言,教授乃至主任、所長、院長、校長都是一時的,只有老師之稱呼才是永久不變的。
傳統粵語採用「生」字來稱呼老師,也非常好。「生」就是「先生」的簡稱,無分男女。我們至今都稱小思老師為「盧生」,就是此理。(民初歌曲〈讀書郎〉:「只怕先生罵我懶,沒有學問,無臉見爹娘。」現在可能要改為:「只怕學生罵我懶,不過課檢,怎麼上課堂。」)
此外還有一種情況,我寫電郵給學生輩,函文結束處祝頌「學安」,對方回函也同頌「學安」。雖說「活到老、學到老」是硬道理,但學生向老師祝頌「學安」,畢竟不大符合語言習慣,還是回頌「道安」、「教安」為佳。
落款署名亦復如是。我在讀碩士時,有次收到系上陳雄根老師的一張便條,落款僅為「雄根」。如此真可謂古風。不要說宋太祖、明太祖祭天時會自稱匡胤、元璋,即使臺灣領袖也會自稱中正、經國、登輝、英九。但我們也理應領悟,縱然他自稱如此,我們還是採用尊稱的好。
這種習慣在今時今日就不同了。比如學生或記者首次致函,稱我為陳教授,我回函就自稱三字全名(我一般不喜歡在落款處加上單位職稱和學位)。到第二次往還,我可能自稱兩字名,以融洽氣氛。但這個時候,我更期待的是對方稱呼「陳老師」或「WS老師」。可是一旦我落款「WS」二字,對方第三次來函便往往逕稱「WS」,不加任何名號。十次之中有七八次如此。相比之下,如果不加名號,我更樂見被稱呼為Nicholas或Nic。畢竟於我個人而言,直呼中文名和直呼英文名完全是兩種感覺,就像直呼「我愛你」和直呼「I love you」的差異。(回想以前本科念商學院,習慣上對外籍教授直呼其名〔first name〕。我一開始的認知是,先要得到他本人許可,才能如此。但令我略感怪異的是,有些人縱使與這位教授素未謀面,卻也同樣直呼first name。經了解後,才知道是因為first name來來去去不過是Peter、John、Mary、Susan,而某些姓氏實在太長了,不易讀。)
另一次,一位非親非故網友突然發訊息給我道:「CWS,你的專欄我讀了很受用,不知何時結集出版?」稱謂與內容之間真箇充滿了張力。以全名來稱呼,如果不計背稱,只有一種情況比較合宜:那就是非常親近的人――無論長輩對晚輩,還是平輩之間。因此我思索了一下,終於沒有回覆訊息。
不加任何稱謂地自報全名,一般用於第一通函件,或者是在電話剛通話時的自我介紹,這是基本禮儀。但有時打電話,我很害怕這種情況――
我:XX同學嗎?你好,我是CWS。
學生:嗯。╱是?
有同仁說,面對這一「嗯」實在沒辦法;但為了予對方以提示,不得不在自稱時加上「老師」的名號――雖然這樣的確不易啟齒,卻有沒有更好的方法。我在想,如果司馬光從北宋穿越到今天,打電話時是否也要自報家門道:「我是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
至於用去姓稱名的方式來稱呼對方,就當代中文而言,涵義也各各不同;但傳統上以這種方式自稱,大抵是一種謙遜。傳統華人文化講究謙遜,而現代青年則日益自信滿滿。某年訪學,我認識一位本科生,覺得他會寫舊體詩,很有才氣。有天他問我寫不寫,我說自己寫得不好。他於是接著問:「你的舊詩寫得不好,怎麼研究古典文學呢?」我只好回答:「是的是的,將勤補拙罷!」
這種情形更不止發生在學生輩。有一次,星雲法師在九龍灣道場會見一批學者。法師謙稱自己天份有限,所以成就也有限。這時有位(大概是歐美回來的)學者應聲而問:「既然你天份和成就有限,那弘法事業不是很困難嗎?怎麼辦?」法師道行高深,只是微笑著答道:「雖然我天份有限,但還算比較精進。」我當時心中一跳,一則以憂,一則以喜:憂的是不知那人究竟聽明白法師的話沒有,喜的是想不到自己以前的回覆跟法師一樣。
行文至此,想到清末民初的一則掌故。光緒二年(1876),狀元張謇(字季直,1853-1926)前往淮軍將領吳長慶軍中擔任文書,稍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一文一武,成為吳長慶的左右手。吳長慶命袁世凱對張謇執弟子禮,因此袁對張一直非常恭敬,每次寫信給張謇都尊稱「夫子大人」,當面則稱「季直師」。民國建立,袁擔任大總統,致張書信改稱「張老先生」或「季直先生」。到了洪憲帝制時期,擬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稱呼又變成「季直兄」或「仁兄」。張謇調侃說:「謇今昔猶是一人耳,足下之官位愈高,則鄙人之稱謂愈小矣。」七律打油曰:
本叫老師兹叫兄。昔兄今日直呼名。
雙名驀地連尊氏,單姓無須冠某生。
喜汝增年復增學,愧余無矩也無成。
細思寧可聊裝嫩,不欲垂垂秋氣橫。
(按:標題為編輯擬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