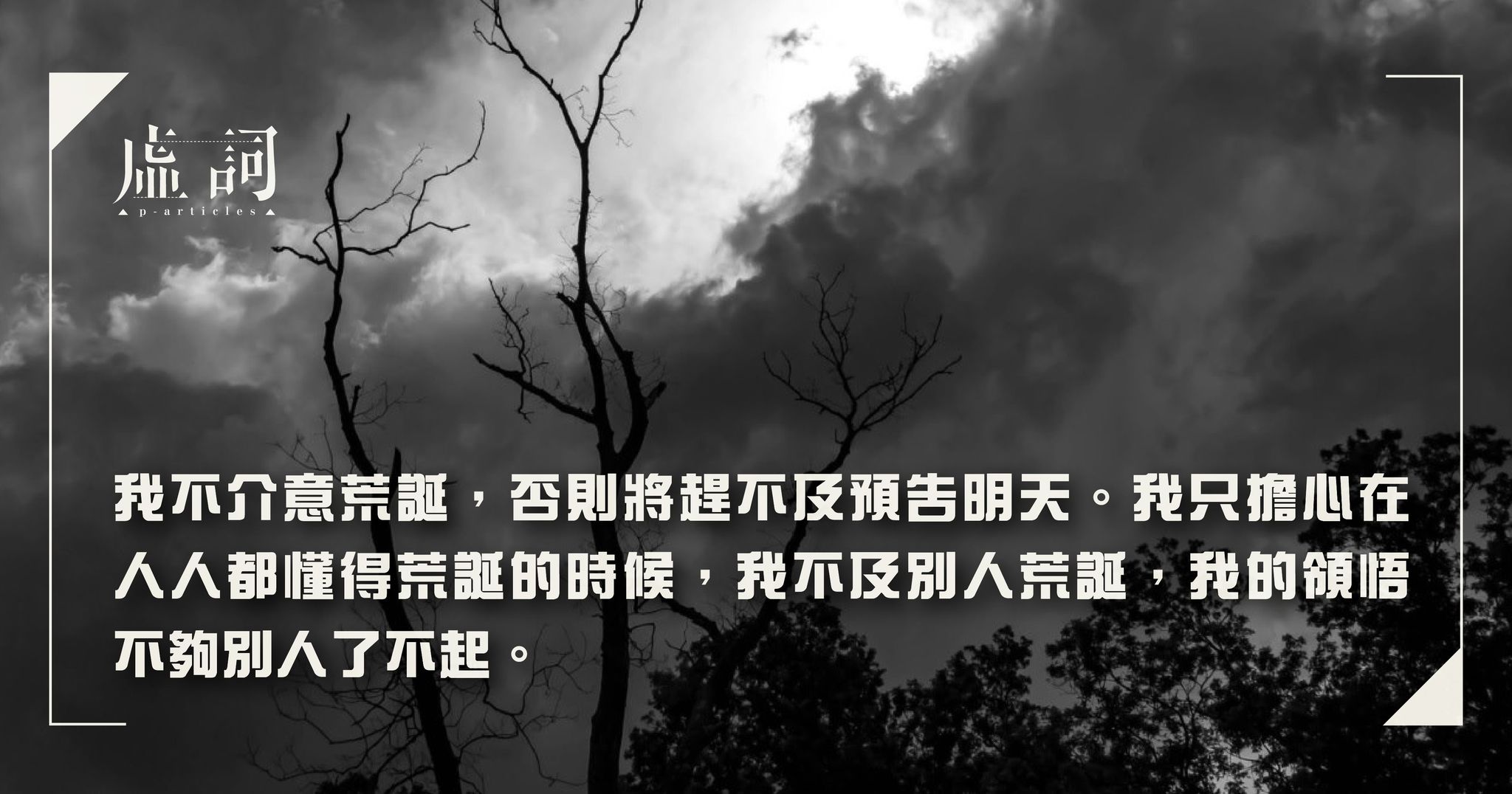在這個荒誕時代,不夠荒誕的人只合做平凡的人,像被擠進同一軸承裏的圓珠,滿身是油,為大軸的轉動而摩擦,卻無法摩擦出一點感受。 (閱讀更多)
【鄧小樺專欄:閃爍其辭】那些艱難與珍貴的異質,值得被歷史記住
看著幾位朋友的創作成果,鄧小樺心裡很肯定,他們就是壞時代的好收成。在黯淡的時代裡,有人持續做他們堅持的事,值得被歷史記住,而且我們作為旁觀的讀者與觀眾就已得到力量。 (閱讀更多)
詩三首:宋子江 X 洪慧 X 律銘
詩歌 | by 宋子江、洪慧、律銘 | 2020-08-22
在惶亂的城市梳理我們的家,每天好像都面對著無力。宋子江、洪慧、律銘以詩紀錄。現實,了無意義。所有當代史都只是古代史。 (閱讀更多)
【虛詞・偷】蒙面騎士
可是後來我又收集到她梳子上的頭髮,還有她與我擦肩後留下的一絲,覺得有分類的必要。我把不同情況取得的髮絲一條條地貼在日記本的不同頁面,統一於右下角標示著日期、時間還有來源。我告訴自己,這只是一個不會傷害人的怪習慣。確實,這世上根本沒有人知道這件事,而琬怡更沒有損失分毫。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