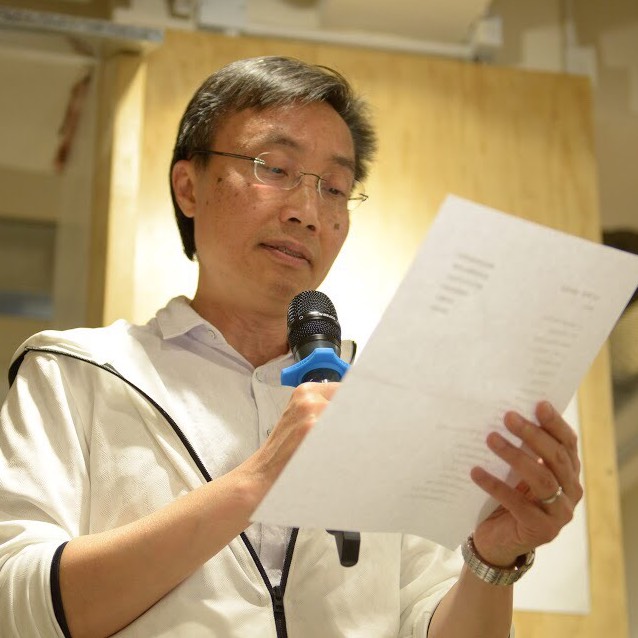【無形.無形】我地
恍惚已成了喃喃的咒語,憑風散落:這裡土地不足,居住空間狹窄,一般住所的面積比任何一個都市都要細小。我們住得逼壓、我們活得困窘……一開始我是想談土地的,卻不由自主的轉到生活空間去,兩者也許是二而一的,但地為甚麼那樣難說?習慣了在多層高密度的大廈生活,已經變得太離地了?不是說,九層之台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嗎?足下是甚麼?累土又是啥?在我生長的這塊邊疆沿海小地,贏取過它特有的傳奇,也曾是世界的焦點,但照城裡人的口吻說,對土對地卻知得奇怪也不奇怪的少。所知的,似乎都不過是資源、領土、主權、商品、財產等東西。也許,這都不是土地的本真。已有太多關愛與仇恨在上面的城,是時候細想下邊的地與土了。
能寫、想寫的總是在地面上所過的日子,所遇的人物,所見的光影,所聞的音聲,所嗅的氣味。這一切似乎就構成了真實的所有。萬有引力,卻不容許人真的可以浮游半空,儘管這也是個不壞的感覺。若然不滿意這些虛浮現象與狀態,也不知道怎樣著手寫些別的、總是沉積在下邊、毫不起眼的土。乾為天,坤為地,天高地厚,人存活兩者之間,生成了冠名的地方,也積累了過去與歷史,然而對地對土所知貧乏。因為我們不願放下身段?就讓自己慢慢地、慢慢地沉下去?如埋下的種子?像朝土裡鑽的蟲?將認知視角,靜穆無聲地調低。把自身活生生的存在帶入黃土,反正這是最終的歸宿?逐漸看不見人臉了,緩緩地亦失去了他們的軀幹、下肢,最後只瞄見人們的鞋?走往低點,才有新開始的可能?官方的香港地質史,一說便是四億年。沓遠深奧,亦枯燥無味。如何直接簡單的描繪那個地那個土,呈現到這裡來,就算只是一個輪廓,勾勒一些情景,浮凸起來,彷彿可摸觸以手,如一個可思可感的實體。
在偏僻的角隅上,尋找一個人物或許容易,發現、以至描畫一個「物人」困難。把物變人,給予法人地位,在南美洲,在南亞次大陸,在太平洋西南的島嶼,都做過了。讓物,以另外一種意義無所依附的,獨立存在。厄瓜多爾的森林,再不是眾人爭奪的資產,因新法律而擁有了自己生存權利的個體。新西蘭北島毛利族人的樹林與河流,也有了「人」的法律地位。印度立法把海豚視為合法的人,不再容許把牠們囚禁,作觀賞或娛樂的表演。都說是為了生態保育。把物與非人同化了,視之為人,是擬人法?擬人法不還是以人的所思所感,加諸外物?終究是人的勝利,繼續以人作為中心向四方擴張開展? 物還是不能安然為物,強要變更自己,才有一丁點的平等?
當前這個城熱烈討論足下的土與地,重心是在地殼之上的。談供應,論需求,一切皆用一種滿足城市迅速發展的姿勢,在改變整個生態,在創造社會的進步,同時這種進步,也就正消滅了一切人與地的互即互入、互涉互存……不知是不是受了土地沉默的呼喚,近年陸續有新的聲音,對城如何翻土用地提出了不同的思路。這些聲音漸漸疑竇,所謂地的匱乏,是真實還是謊言?有人存心囤積閒置土地,待價而沽?移山填海的造地破壞,又可有必要?聲音又問,為何不先發展已受污染的棕地?卻要逼迫僅有的農地與農村,令既有的生活社群流離失所?聲音縈繞延綿,追問無止境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後果,必會帶來資源共享的理想生活、能永續的生態環境?聲音或許最終只會變成雜音,不被本已嘈吵喧嚷的城聽入耳裡。當微風吹過,隱隱約約的細語迴響,水源土壤都不再、都不在了,惟有離去飄散……
地上的國,土上的邦,曾合零為整,也有化整為零的時候。地面的交錯、抗衡、爭鬥不停轉換變化。地下何嘗又必然是個靜止的世界?地上盡是樹系的領土,枝再繁葉更茂,也離不開主幹骨架的領導,等級層次分明。地下卻是根莖蔓衍,盤根錯節,主次難分。在地,可以尋回失落的平靜?重拾生命的自由?
厚德載物,大地厚實包容、載養萬物,不以求報。傳統道德勸人效法土地的自然法則,不自私、不佔有、不執著、不落偏,為而不恃,生而不據,功成而不居。但這還是人的角度、人一廂情願的想法?怎樣理解地崩裂變,地層錯動引發的毀滅?天地無常,把土把地凝固在一個人的想像形態中,就可以把握幻化的全貌?
若然可以,嘗試向山學習思考,仿石的敏感領悟?不過,如何知道大地會思考、頑石能想像?一切又再淪為文學的幻覺?人的知識有限,怎樣以有限,構想無邊無際的物?或許,也不全是沒有邊際的。人與地共存於同一的時空裡,離不開彼此的互為因果,相生或相滅的互動互變。
眾人許多個晚上與晨昏來到這塊地上,呼吸還夾雜著金屬的氣味。有人趁未冷的時候,往更遠的方向走。留下未去的人,看見了零亂的石堆旁,長了幾株歪歪斜斜的桑樹。雜草也長滿花,猶如粉色的浪從腳邊穿過。荒野之外遠遠有朦朧的山脈。石塊發出淡淡的濕土記憶。從地上吹來的風糅合了叢林的芬芳,撫平了他們的心。以前創傷了的土,跟眼前的石堆地,可以是連繫的,即使有高山、河川與圍屏的阻隔。他們想起他們曾經有過的技能,開始執拾石頭。不知從哪兒找來粗糙的工具,便把周遭的土翻掘起來。地開出了坑的時候,溪水便來了。一夜之間,水已及膝了。他們讓山坑魚、福壽螺、淡水蜆留下來,以後拿水勺向田畦澆水。稻便這樣長出來。未許有任何組織,不過是各自為政,任由風在他們臉上吹拂,讓沉重的器具在手上身上留下疤痕。只是土地所涵藏的,誘導了各人不約而同,於合適的季節安心到臨。相對於鋪設水渠、電線與築石屎路的隊伍,預先在土地上做了許多許多勘察檢測的工序,這些翻土人與地的關係,就隨意隨緣多了。也不全然是神秘的召喚,地與人兩者的相遇,少不了是人自身理智與本能的推動。但人僅取所需的,不是為了擁有,倒安然地自在。人與地的牽連,造成了場域,地的自然秩序沒有把人完全吞噬,人的感情、思維與想像可以參與其中。即使土地的沉寂、厚實,抗衡著人的理解與探索,但正因為地沉默的反抗、不順從,迫使人在既有的方式以外思考、領會,以至行動。讓只屬於人的文字,也能騰出空間來思索物,將地與土包攬在與人共生平權的變化形成過程之中。人是難以理解地的,只在自己的理念與情緒間怔忡兜轉,但也懂得自身以外,有更大的生命、價值與美感。不斷的失敗再失敗中,還不能描繪,卻未許沒有剝落的感覺與零星的快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