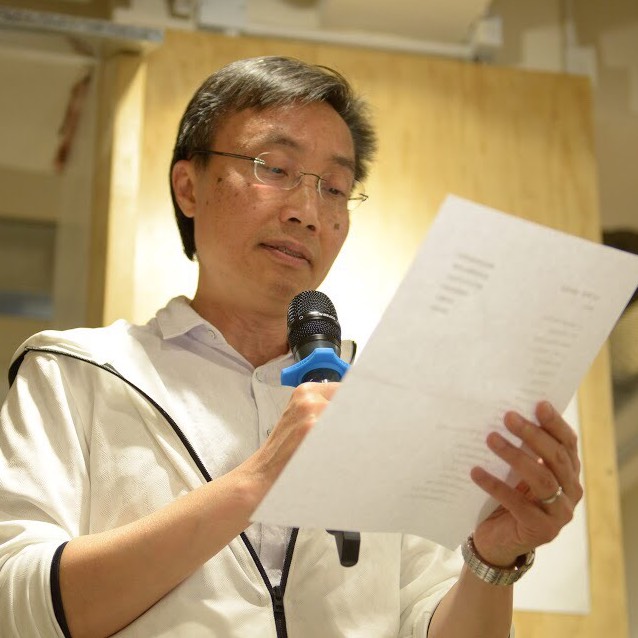【虛詞.酒店有落】走房
已經不是第一次了,與子女及他們的女朋友、男朋友一起往外地旅行,妻為了分配酒店房間的問題,煩惱了一陣。上次到L城,妻租了一間酒店式公寓,三個房間,因為大女兒的男友沒有同行,妻以為讓女兒與兒子的女友同房,兒子自己佔一個房間,問題便解決了,想不到兒子會問:為甚麼他不可以跟女友一個房間?那邊廂,女兒也質疑:為甚麼弟弟可以自己享有一個房間,她卻要跟她不太熟的人擠在一個狹窄的空間裡?結果妻就讓女兒獨佔了一個房間,兒子和他女友的房間裡是一張分上下床舖的牀。妻對兒子說,你們的房間狹窄,晚上最好不要關上門,空氣就不會侷促。妻晚上故意走出共用的客廳去喝水,看見兒子和他女友房間的門是關着的。
他對妻說,年青時我們往酒店同住一個房間,哪有人阻撓的?你算了吧!他對妻說着,心卻在想,年青時我們怎會跟父母一起去旅行?又怎麼會像現在的年青人那樣,一切事情彷似理所當然?
在家或離家,成長中的他總是被教訓:這裡是學校,不是你的家,要好好的遵守紀律!這裡是公眾場所,不是你的學校,請保持肅靜。這是圖書館,不是你的私人空間,不准喧嘩吵鬧的!然而,即使在家裡,他也一樣受責備:這是你的家,不要亂放東西!弄髒了梳化!他大學時讀到規訓、控制社會的理論,分析人如何從小到大、由老至死,都在不同空間中被訓練、操縱,以至懲處:家庭、學校、工廠、辦公室、公共領域、養老院、醫院、墳墓甚或骨灰龕。讀着讀着,他雖身有同感,但心裡卻有一角僥倖感。他認為自己找到了一個不被外邊操控的空間:女友大學宿舍的房間。
那個年代,男生晚上是不許留在女生宿舍裡的,而且宿舍都是雙人房,也不方便跟女友怎樣。不過,他的女友是比他年長的研究生,又是宿舍的導師,可以獨自佔住一個單人房間,他就可以暫且用作時鐘酒店了。在眾多限制下的小小歡愉、丁點兒的自由放縱,他只是渴望可以延綿下去。
大學生活是短暫的,大學生的親密關係也多數不能持久。他沒有了免費的時鐘酒店,不過也很快有了新關係。經濟能力有限,他帶女友往離島的渡假小築。房間設備簡樸,窗外是沙灘,看得見海景,可以了。這裡是酒店,不是左不許、右又不准的地方,你想怎樣便怎樣罷!
酒店於他,從來都不是甚麽龍門客棧,有幸或不幸遇上三山五嶽的神祕陌生人,引發一宗宗的罪案或傳奇。他的酒店只有房間,華麗的大堂他沒興致停駐。他記得已經拆卸的六國飯店,只因為房間裡層層厚重的垂地黑窗簾。他做第一份全職工作時,沒空約會,晚上偶然會跟女友入住。大概五百元一夜,可以接受。疲累的一夜,房間在窗簾的掩蓋下,完全暗無天日。他睡得很熟很死,慶倖明天是假期,夢想可以這樣永續下去。他的酒店與世無爭,不是任何一個社群的縮影,儘管沒有女友作伴,他也不會入住酒店。
日常生活空間狹窄,他有假期便與女友往外地跑,住各式各樣的酒店,臨海的、繁華街景的、有露台的、有小型按摩池的、郵局改建又三尖八角的……即使在房間裡不過是做相同重複的事。能夠不重複,他遐想,除非入住的是不同伴侶。他在職讀外國的遙距碩士課程,有幾個星期要到那邊的大學上課。他留宿的大學城,正巧有所修學科的全國周年學術會議,在城裡的酒店舉行。他與外國同學一起去湊熱鬧。那門學科的全國精英都來了,他和同學們聽著名教授的專題演講。在接待酒會上,同學們都在暢飲,他聽着外國女同學笑嘻嘻地談艷遇。女同學說,她剛找上了那個專題演講的教授,很快便上了他的酒店房間呢!另一個女同學隨即大叫:我才跟他在房間裡幹了!你是甚麽時候去的?她們兩個人帶醉地互相調笑、尖叫。他在旁喝着他第三杯紅酒,分不清是真是假。
他進入了高等教育界,開始單獨到外地公幹、開會。一個人在酒店房間裡,他偶然感到寂寞。通常與開會的人,應酬到很夜,回到房間立刻便睡了。也有不能入睡的時候。他瞞着妻,把一、兩個避孕套放進了手提行李箱內,眾多的個人旅程中,他一次也沒有用上。回來,靜俏俏地把避孕套從行李箱裡取出,將它們放回原處。一個人在空蕩蕩的酒店床上,受着時差的煎熬,彷彿聽到隔壁的呻吟。他想起有人長期被軟禁在酒店房間內,只有受拷打盤問的時候,才有機會遭帶往另一個酒店房間。這裡是酒店,不是你以為可以快活的地方,聰明的快快招認!反正全世界都將要知道,你是來嫖妓的!
一家人旅行,兒女還小,四個人睡在同一張床上。兒女熟睡了,妻怎樣也不肯跟他纏。她感覺不自在。與家人旅行,他居然寂寞。兒女快迅成長,家庭旅行,盡量找兩個相連的酒店房間。一門之隔,隨時互相照應。妻還是感覺不自在。與他纏,也不暢快。實情是,他也漸漸有欲卻無力。
酒店房間不斷轉換,每打開一道房門,他看到的都是一式一樣的床:被單都攝進了床褥下。沉悶的整齊。這裡是酒店的床,不是你的地方,雙腳不可以亂伸岀來!他愈來愈不確定,哪裡才是自己的地方。
妻沒有堅持,問女兒與她男友,給你們一間只有一張大床的房間,可以嗎?然後讓兒子和他女友入住上下床舖的房間,提醒他們,晚上最好不要關上房門,好任空氣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