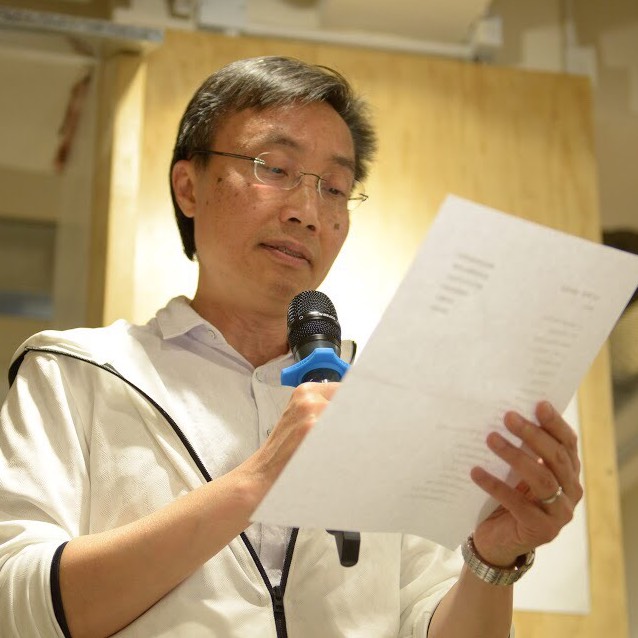【無形・離留之間】文學 × 視藝展覽——夜行紀錄
循勇指往的方向,素然依稀看見荒村在紊亂橫生的樹叢野草中隱現。輪廓迷朦的幾幢破屋,光暈掩映下,彷彿隨空氣與時間微微搖晃。黃昏的氤氳裡,茂密的林蔭埋藏着連綿的暗影魅域。素然在殘留的矮牆角落瞥見一個穿長衫的身影掠過。梓南開了機,隨意紀錄早已不在的社區。回到工作室看毛片,素然才省起問有沒有見過長衫人?梓南瞠目不明所以。
尾指這段時間特別感覺麻木僵硬,指關節好像上鎖了,難以轉動屈曲。素然覺得應該與壓力有關。她心裡不以為這是甚麼大問題。即使自己的健康早已不是最佳狀態,尾指不適,無論如何也未至於造成大病。她不單要到拍攝現場跟戲,還有無盡的聯絡工作要做,要耗上幾刻鐘為尾指見醫生,實在太不划算。年前她與愛倫打羽毛球,愛倫不小心食指遭球拍打個正著,呼呼叫痛下以為關節脫了,去急症室等了三個鐘,竟然還留院觀察一夜,要待得明日十時後醫生巡房,看過X光等報告後才可以離開。愛倫性急,頻頻說自己真笨,回家捽捽跌打藥酒,不就沒事了,那要浪費這些時間?還要請假留院?愛倫瘦,不吃東西也是為了瘦。因為她瘦,素然才逼她到急症室檢查,現在倒有點怪自己好心做了壞事。這麼多年的朋友,愛倫當然不會說出口。人的相處也不過是妥協與默契。
素然不怎樣相信命運這種東西,也知道人總不能都在順境之中。行了衰運,接下來就可能是順風順水的路了。作為監製,她這樣安慰其他工作伙伴。她當導演時,卻總是很頹很灰,好像只能看見自己想看見的,沒了觸覺敏銳,傾向悲觀矯情,近乎失魂。素然入電影學院,只是為了做創作、編劇。學導演,是必修課程一部分,她得過且過。被逼得緊時,甚至想過轉去創意寫作系。英文詩,她有若干習作,曾經躍躍欲試。沒想到,畢業後回來,居然有人聘請拍MV、拍廣告。她告訴愛倫,好境時勢,阿貓阿狗都有公司聘請拍片。時勢逆轉呢?愛倫問題尖銳。素然泰然回應,我就做監製。
她和愛倫相交多少年了?住同一個公共屋村,念同一間小學及中學。最後亦不約而同考不入香港的大學。那年代,入不了港大、中大,就只有讀理工、浸會。愛倫決定念理工的Comp Sec。素然一直心儀電影,卻沒去浸會。父親執迷外國大學,即使家境並不富裕,認為大兒子已送出國了,二女兒也該往外地留學。父親不是新派人,送素然到外國,不等於性別平等,只是姓龐的,男好女好,一定要比其他人活得體面,教養優良。畢竟父親以前在大陸也讀過一年工專,明白教育重要。素然從小的教誨,女孩子不要招搖與出頭,一大堆的不許這樣、不該那樣,還要默默收藏自己。唯有遠離家庭,她才感覺自由。素然不相信父親不愛她,成長路上卻難免惶惑,不把她的存在真正當作存在,為甚麼又要把她生下來、養育為人?這些問題,一個人在外國才會想。她與愛倫一起成長,相近的家庭背景,接受近似的教育與關愛。如果不是離開過,素然偶然問自己,我是不是如愛倫,真心信任既有的一切?
那次她認真的對愛倫說,我才不reproduce。我只produce。愛倫的戀愛史平淡中帶點痛,曾遇過一個舉止端莊的男生,挨近她,和她密切交往,目的可能只為了要掩飾不能出櫃的身分。這都是愛倫敏感的疑竇。未到那一步,愛倫已不讓他再接近。她對男人實在也厭倦了。還是會想像自己有生育的一天,跟素然談起冷凍卵子的可能。
監製不能說不是創作。導演只是用自以為是的視野,建構覺得就是如此這般的影像敘事世界。監製不然。她每次都像在重寫別人的小說,但一定轉為全知觀點,讓她跟每一個角色,以至推動進程的戲劇情節,都保持着社交情感距離,但又不可以太疏遠,否則無法理解感受他們的生成與變化。既同情,又要批判,猶如繼承了經典寫實主義的傳統。有些時候要激勵雞冠垂了下來的導演,有些時候又要言辭懇切的勸慰已變得很不耐煩的受訪人或演員,以至場面調度的細碎安排。素然不只要考慮藝術創造,亦要兼顧受眾的反應與興味,要面對發行、宣傳、放映的問題。作品造大了,愈要思考投資者的視角。在緊迫忙亂又渾沌的過程之中,大家各自在自己的崗位上落魄失魂,素然卻是擔當個具法力的召魂師,要離散迷亂的三魂七魄最終歸位。
不過,她自知本身的法術不完美,道行未夠,每一次製作完成,片也剪好了,魂魄其實仍在漂移浪蕩,多是花果飄零的境况。這是素然個人的玄思妙想,只放在心裡,不說出口的解嘲。她當然有俗世的版本。對愛倫,對創作團隊,素然說她只是二房東,管理協調各個獨立劏房户,追求成為完完整整一家人的可能,大家共存共榮,不能讓大業主以重建藉口一掃帚趕走,把家園毀於一旦。肺炎大流行,她又有新比喻:她是漂流郵輪的領航員,船長與眾船員因屢次無法令船隻靠岸,落得不知所措,她的任務是要一條船的人,繼續齊心,相信彼岸究竟還在前方。兩種說法都很有危機感喎!拍片真是這樣慘情的?愛倫不知在提問還是下判語。然後還說,你不是不信急速成不了事嗎?一條船上,有人要快,有人不怕慢,你怎樣處置?
她的工作室坐落在頗陳舊的工廠大廈裡,每次夜深一個人離開,素然選擇不搭那些轟隆轟隆地響的運貨升降機。夜靜時份,運貨升降機的機械操作聲音太過聒噪與嚇人,何況還要使勁拉開上下合攏的厚重閘門。素然哪有這樣的力氣?而且尾指偶然在痛,碰上金屬,感覺不是很好。她走後樓梯。工業大廈的後樓梯其實比一般樓宇的寬闊好走。但大廈本身殘舊,走火樓梯的保養與清潔不是很理想,特別在晚間,氣氛暗影就有點迷魅陰森。素然不是小女孩,一個人照顧自己許多年了,這樣的環境怎會害怕,況且是團隊的地頭。一步一步的下樓,在昏沉的燈光下,只聽見一個人腳步的回音,那種節奏讓她似要緩緩走入休眠的狀態,是完結了一天的儀式。這道後樓梯曾是她監製的恐怖片裡,其中一個拍攝場景。港產片市道低迷,財困的男星自編自導兼自演小成本的《盂蘭怨咒》,要找一個可靠卻不昂貴的監製,就找上了素然。她對恐怖片毫無興趣,只是為了工作,但看見男星終日在片場神不守舍,用手機迷惘地不停發放及接收訊息,又不時燒香拜神,彷彿中了邪咒,她才不得不提醒他,不要過份入戲。
素然不像哥哥,小時候父母不許外出玩耍,哥哥會想像出很多遊戲來,兩兄妹要扮演不同角色,依照哥哥構造的劇情來玩。素然不明就裡,多數不怎樣投入,令哥哥不高興,甚至喝罵她。哥哥有時索性自己一個玩耍起來,演繹眾多角色,舞刀弄劍,披着毛巾作斗篷,在狹小的屋內跑跑跳跳。素然坐在廁所露台的痰盂上,看着哥哥在碌架床上下飛舞,時而興奮,時而又好像面容憂傷,她實在沒法理解。許多年後,短暫地當上了導演,素然才明白,困頓在自己構想出來的宇宙內,並不讓她快樂。意義和秩序一己是建立起來了,卻是孤獨呆板的執念,與外邊的變異流動沒有聯結的。她決心不要做這樣的作品。怪力亂神,不去臆測想像,不困頓在自己的幻夢世界中,素然覺得就不會懼怕。她決心只為眼見目睹的害怕,或不害怕。每晚回家,一亮燈,便看見那群小蟑螂四方竄散。心慌亂的,豈只是這些小動物。有時素然甚至感到,自己好像撞破了牠們的好事,搗毀了熱烈進行中的派對,成了可厭的入侵者。她完全沒有野心,要消滅這些已存活千萬年的昆蟲,僅僅希望牠們不來探訪。然而,眼不見,不是不存在。
手機微微地持續在袋中震動。剛才一場驟然的大雨,令兩人變得狼狽。梓南本來只忙着碌手機,只有素然無目的於白日的午後在村口蹓躂。蔚藍天空上盈盈的白雲朵,日照燦爛但不凌厲。她抬頭目睹大片灰雲瞬間橫過頭頂,如來黑掌抹額,大顆的雨點便急促的拍啦拍啦沙沙地打下來。沒有人帶上雨具,都匆忙尋地方躲避。兩人在簷下定過神來,看見對方濕了的頭髮,還在滴水。素然才發現,手機在袋中響動。
性格令她不做強勢監製。不想做,也沒能力做。素然不是每天都在講視野的管理人。看不見、看不清的,不能強說看到。曾經合作的獨立影片導演都較她年輕,然而素然不扮前輩,也不當家姐或母性的角色。有任何問題,盡力坦白平等地溝通。即使不是沒有波折困難,每次製作最後都算能迎刃而解。跟梓南不是第一次合作了。上次素然只是耐心的提梓南,紀錄片不是前線。我們在熱火朝天的前線上拍攝,但真正的意義不在那裡。梓南嘗試明白,與素然協調。因為年青,有時較衝動。事後一段時間,梓南說拍這個題材,有點為了與頑固的父親對著幹。他有想過,街上的衝突其實是家裡的延伸。他也自嘲過去多拍劇情片,熱情主導,為人物想好了對白才開機。紀錄片開了機,很多時也在空等,人物與故事許久都未現身。
跟勇的故事,倒訓練出梓南的耐性。開機他就結結巴巴的說不出話。或許是燈光,或許是鏡頭,讓他不舒服。勇說。梓南以隱閉鏡頭,大量採用自然光,和勇談。或只拍勇的動與靜。不過,日間不容易找到勇。素然以為要花唇舌說服梓南不要放棄這個受訪者。梓南反而不斷說,勇古怪,卻有趣。
《壞時代真心記》引起頗多關注,最後還拿了紀錄片大獎,梓南卻不是很快樂。素然與他跑了幾個國際電影節,也應邀到外國多個民間機構和大學巡迴兼座談。素然感覺梓南沒有因此沾沾自喜。旅途上,梓南坦白向素然說,自己每次坐在黑暗放映室與觀眾一起重複看這齣紀錄片時,愈發心情忐忑,內心難以平靜下來。有觀眾說理解了真相,有觀眾表示看見了希望。梓南卻覺得自己當時沒有意識地傳播着焦慮與恐懼,擴散着憤怒仇恨的情緒,在萬縷心結中艱苦掙扎,走不出來。他知道激情的陷阱,卻又不願若無其事地活着。
素然最初以為梓南可能是鑽牛角尖了,把紀實太感性地劇情化了,兩端不顧比例的任意放大,可能是成名後遺症的一種壓力反應。但多次聽了梓南訴說的苦惱,自己也反覆在影展巡迴中看片,素然開始發現道理該愈講愈明,怎麼敘述像愈說愈糾結複雜。她嘗試較客觀地解釋,也許拍攝的對象其實遠比他們能理解的宏大龐雜。那段緊密時間的追蹤描繪以至之後的重組剪輯,只表現出製作者的情感和理性線索。在不斷翻看作品後,才曉得素材大大逸出他們勾畫的意義範圍之外。
猶如某種補償,素然推動梓南尋找另外的可能,去再講這個沒有講清的故事。或許不是刻意的找意義,只是回到生活,回到日常,回到根本。不知怎樣,創作團隊遇上勇。他似乎自自然然地出現了,但一些關鍵時候要找他,又不是那麼容易聯絡上。梓南和素然一直在山腳的專線小巴總站等候他。各人的心情這天似乎都很美好,沒有因為勇久久仍未現身影響了情緒。郊外葱郁的草木環境,恍惚的似近若遠的聲音,把他們轉換到習慣了的意識之外。素然與愛倫有定期行山,沒有刻意要挑戰體能,通常走易走的行山徑。郊遊季節,遊人較密集,愛倫又喜歡閑談,素然不怎樣細聽在廣域裡的各種來歷不明的聲音,即使音聲進入了耳蝸,也不以為意。梓南起初都專注在手機上。世間紛亂,隨手指操控滾動的色彩視窗,隱約有某種秩序,前置是要人讀得失神。
他們在西北的朗地拍過勇種植水稻的情況。一頭蓋額掩耳的銀髮,勇長水靴上瘦削的身形在晃動的水稻間消失,又徐徐回來,回到鏡頭前。梓南沒有如過往拍攝社運般,用很多搖鏡。對勇,鏡頭多是靜止的。彷彿一種懸念,勇的節奏中屢屢浮現停頓。初秋的早上,眾人都添了外套。勇穿了兩件長袖薄衣,上排的紐扣沒有結上,深色皮膚包裹着突顯的胸骨。他背負體積頗大的電動噴器,在植物的根及其他部位噴灑有色液體。勇是農夫第二代,現在要重新學習有機耕種。梓南特寫拍勇修長手指上的一顆小昆蟲。素然留意到他僵直的尾指,但不在鏡頭內。勇歎息這時代氣候異常,蟲患嚴重,農夫生活困難。梓南畫外音問,那為甚麼還賠錢地繼續種植呢?勇一刻間答不上話。
從英國小鎮回流,勇仍只習慣鄉郊式的生活。年少時隨家人移民,舉家轉做餐館生意。吞吞吐吐的對話中,創作團隊知悉勇並不喜歡異邦的人生,始終念念不忘兒時長大的村落。唯一他說得肯定,離開如行屍走肉,回來為了拯救靈魂。他們無從在勇的描述中洞知鄉村的全貌以及其他生活細節。印象和臆測之間,村應建在山裡。好幾家人本已熟稔,為了避秦,由某地一直逃往南端,及至大海之濱。有家庭昂然渡海,奔向更遠的岸;有家庭疲倦了,如勇的父母兄姐,選擇在山與溪之間結盧而居。既不是原鄉人,避居山中只為免卻爭地的衝突。勇和家人自小艱苦,精力都耗在山坡開墾出的數幅梯田上。憶記中也養家禽牲畜,家人甚至到城中打散工,似乎都無法安安穩穩過活。那是兒時,不知真相,也可能生計勉強湊合,但喘息過後,還是覺得山裡暫居未能釋懷安心;也有可能為圖改善生活,尋覓更好的物質與價值。因由認不清了,少年的勇便同家人再遠遷外地。勇說,家人其實未想過放棄山村。偶然回來暫居,依然願花心力金錢修葺舊居與荒田,直至多年後整條村的住户全已離去,剩下日漸腐朽失救的舊屋和泥地,在山氣與暮靄中沉沒。
淡淡的霞光靄氣慢慢從四周圍攏過來。素然只怪自己恆常睡得晚,氣血低,腦筋有若短路,視野也模糊起來。風起時,勇一貫的木訥,也會忘形地描述,山會彌漫着濃膩醉人的迷香。雲霧吹散,那陣味道仍久久嬝繞,在身上,皮膚與髮梢徘徊。那時候,勇會痴纏的抱擁着母親或姐姐,良久不願放開,就為了聞她們身上的淡然香氣。霞暉從林蔭的隙縫間射進眼簾,更分辨不清周遭樹影幢幢包圍的環境。她把意識稍稍放在嗅覺上。只是含糊輕拂的草葉味,山徑的初段仍繾綣着濕氣,氣息普遍下沉。梓南時而開着攝錄機,時而關上,機械的眼如一合一張的眼皮,依然比眾人看見他們看不見的模糊渾沌。
愈入山中,路愈拔斜,體力需求漸大,他們開始少話了。是素然她們愉快地吃着從村口買回來的茶粿時,勇才在視界上現身的。他微笑着,眼睛輕掛着歉意,說有事情阻礙,耽誤了時光,大家要立刻動身上山了。等待勇的白日裡,梓南與素然走了一遍山腳下安靜的村子。不是假日,村裡只有老年人在閑躺,屋子的大門都半掩或敞開。室內沒有亮燈,隱若看到一般生活的家具器皿。狗懶洋洋的對他們這些遊人毫不理睬。梓南心血來潮,忽然說他要沒有對白、沒有旁述的紀錄,讓影像自行說話,要像盧米埃的默片味道,故事敘述只是潛在的,任被拍攝的對象和人物發揮本身感動的力量。素然只挽着嘴笑。
他們放緩了步伐,豎起耳朵,接收走在前面的勇,疏落、間斷的話音。當地人的村後面,都有風水林。勇少時下山,記得多是從那裡穿過。他們近黃昏出發,避過了日光的猛烈,悶熱如潮水退去。漸離開了村走近勇說的風水林,已感到一絲絲陰森涼氣。素然事後記不起,她們是怎樣走進風水林的。殘留的影像是一排高大矗立的樟樹群,齊整地包裹了枕木步道。她們一個跟一個,走入勇形容的古道。有別於想像,她總覺得有雙眼睛在看着自己,閱覽着所有,一舉一動,都被這種視角觀照著。也許是自然。他們攝錄周邊情景,眾物也在無聲回看,都成為了風景。風水林前的黃昏,遠山一片沉寂,眼睛只看見風景的剪影,四周變為粘粘軟軟的澄黃浮動。暈紅濃濃也不得不在遠方慢慢消溶。暮色漸變蒼茫,朦朧幻化又滲着若隱若現的微明。夕陽的燦然金光已漸盡,素然的心也累了。
是叢林中的殘餘憶記?走過一片金黃暮煙包裹的綠色與泥黑,猶如經歷了草莽茂林在不同的、斷裂又壓縮的時空中,向彼此生長、膨脹、增生、擴散、吞噬、內旋、轉翻、塌縮的變異延緩狀貌。在一片昏黃中,連綿延展的樹影暗魅令彼此無法清楚看見,素然莫名地感覺悲傷寂寞。父親的死亡,並非毫無預兆。多次進出醫院,最後讓他回家療養,本意就是不用家人奔波,靜心陪伴臨終病人。只是素然的母親年紀也大了,父親自知康復無望,如一隻徹底鬥敗的惡獸,脾氣完全失控,母親更無力照顧,還是要把父親送返病院。那段時間,素然剛開始監製工作,經常要往外地跑,一去便一兩個星期,回來已不怎樣跟得上父親的病情發展。之後她盡可能隔兩、三天探望父親,在外時與家人密切聯絡,跟進父親的情况。她還以為自己已充足作了心理準備,但仍是哭得崩塌,整個人彷彿坍垮掉了。因為趕不及見父親最後一面,她深感歉疚。事實上,她曾經反叛,不聽從父親苛刻無理的訓誨,即使每一次都不是公然的。父親離去,她才發現自己的人格價值,全都承受自父親。自我貶抑甚至抹殺,常覺得其他人比自己重要。她掙扎過,不斷找尋自身的價值,有時候似把握着了,然後又禁不住在內心否定了它。看着它消失,才覺得是自己。她沒有恨父親,反而感到對他虧欠,沒有企及他的期望。不能企及,因為她一生,也不可能變成父親的兒子。
他們吃力地連攀帶爬走了一段上坡路後,穿過了茂密和浮華蔭影,來到較寬闊空曠的土丘,看見了渾然的山勢。幾棵細葉矮樹在土坡上醒目的佇立,隱然帶着柔和芬芳的味道,似是對剛才的辛勞溫婉的撫慰。葉子輕輕震動,勇推了幾下比他略高的樹,說這裡曾經有棵闊大的細葉榕,風雨倒下來後,相隔這些年月,才生長出一株株年青的樹。憩息了一陣,梓南啟動了航拍機,在眾人頂上嗡嗡嗡嗡煩悶地響着。勇引領着各人踏過已被野草掠奪了的蜿蜒泥路,他們察覺到有些石頭曾作路墊的痕跡。村路早已不復存在,僅剩這裡殘留的沙石和塵埃。
荒村逼近,山也變得不再遙遠,不知源頭的聲音,從山的深處穿過浪盪的風,散落在沉靜的天空裏。太陽已經差不多完全退到山後。梓南以搖鏡環迴四周,像要捕捉風的形態。航拍機傳到手機上的即時影像,夕照餘艷仍籠罩着荒野樹叢,整個村落在一片虛幻的暈紅光中飄蕩着,他們的身影迷迷惘惘。棄置的山村並不像她們構想的廢墟。幾幢磚屋只留下數堵破牆的輪廓,蔓草與泥石佔據在頹垣之中。但轉角處,還有三兩間房屋外貌看似完整。勇說有其他村民曾回來試圖保存舊物,也有城裡人閑暇走入山中,自發耕種,推動他們想像的農村復興計劃。他們父母一代不是原居民,對新人的進來,沒有太大的抗拒。勇示意再往山裡走,去看曾經養活他們的梯田。大家繼續往裡走,旋即聽見流水的聲音。
拐個彎,眼前便是反射着星光的淙淙活水。山風橫邊吹來,帶着水濕的氣味,他們都感到陣陣涼意。沿着從山谷流下來的溪水再向前走,便看見斜坡上夷平了的數幅狹長田地。他翻過土,希望土壤可以重生養殖起來。勇在暗黑中重重踏在泥土上,轉了好幾個圈,然後坐在地上。素然足下感覺到泥土的濕潤。未拔出苗的土地上彷彿已散發着持續的葉香。勇說父母以前種茶,但他已經無從憑以往的記憶複製他們種植的方法。現在他只打算零星地種一些菜及果,隨著季節的轉換做出適時的應變。他不知山村能否復活起來。他回來,只因為不捨,心裏其實沒有藍圖。勇柔和地撫摸着土地上撑起的竹枝。
山裡總是多霧的,涼氣逐步圍攏過來。素然和梓南沒有計劃在荒村裡度宿,勇指示她們走下山谷,便可到逹沿海的公路出市區了。梓南自恃曾挑戰毅行者的耐力比賽,晚上爬山對他不會有難度。他提醒素然「黑泥白石光水窪」,小心留意環境便不會有差錯。況且他們有備用的攝錄照明。
溪谷的地勢慢慢往下沉,星光下,周邊並不算漆黑。但樹林茂密,也擋去了不少光影。她們一路往下走,都聽到水聲。水不緩不急的從石間流過,在高處陡峭的地方造成了一些小瀑布。更多時在安靜的水窪中迴淌。下游那方是沉默的山徑,一直延伸到渺然的暗夜。除了水聲,依稀有斷續的蛙喊與蟲鳴。素然把日間綁在後面的頭髮放下來。她們一起往下走。幽魂的魅惑,彷彿無限陷落。沒有說話,只集中精神走路。回頭看過一兩次,荒村早已消失無蹤,也沒有任何燈火人跡。眼睛已適應了黑夜,山在暗黑中還是可以看見的。但素然走得不算很穩健。梓南沒有問,不由分說,抓住她的手好幾次。
山風在夜裡偶爾吹得強勁,她有點瑟縮的走着。素然感覺某種物質穿過黑暗的帷幕和塵埃來到她的身體裡。僵硬的尾指開始抽動。梓南走在前面,沒有注意。他剪得很短的頭髮露出了後枕,讓素然看見腦勺與頸項上微微泛光的汗滴。素然的心怦然的跳動起來。她看見自己和梓南赤身的互相攬抱着。梓南吻她,撫摸她。她聽到暗夜中潺潺的溪流。水聲柔和,也帶著猶豫。
好感沒有讓素然稍減對年輕男子的不信任。山谷對面應該是連綿的山峰,這一刻沒有人看見。有形的事物能夠存在到甚麼時候,沒有人知道。素然不情願將自己的信或不信,投放在不知道存在到甚麼時候的事物身上。她曾經相信父親,相信權威,因為父親的權威,不管自己喜歡不喜歡,好像總在那裡,給了她一種安全感,即使在連自身也看不到的徹底漆黑裏。
盲目不是完全看不見,卻以為自己能夠看見。在暗淡沒方向的空間裡,她連時間的意識也漸漸失去了。沒想過愛倫是她的對手,喜歡上同一個男生。甚麼也沒有發生,她們都熟知對方,依傍彼此。心底卻一直以為自己比愛倫優勝,學業、樣貌,以至政治覺醒。她其實勢利,崇拜權力與地位,面對比她強大的力量時,又軟弱的覺得自身的無足道。
她覺着身體内有某些曾經蓬勃茁長的東西,正在慢慢地消散。她自知流着父親客家人的血,那些流徙的靈驅迫她向外跑,曾給予她勇氣。雙腳儘管在暗黑中不停挪動,她的心卻已經很厭倦了。父親走不動時,還可以把她和哥哥往更遠的那裏送,讓他不安分的靈借助她們繼續追尋美麗的新世界。如今她不願走了,就只能困在這裡苟活。來到這樣的黑暗,她知道,就不能再回頭了。所有聲音被吸進冷意的暗黑空間裡。她的聽力好像已不在了,只有耳窩內微弱單調的頻率。除了沉默,沒有別的。她試圖呼叫,不為求援,只想聽見聲音。凝聚的空氣發不出任何聲響。或許她的聲音已被吸進無邊的虛空黑暗裏。
然後有甚麼東西在她臉上撲動。草的碎屑,抑或是有翅膀的飛蟲。她感覺着,再讓感覺徐徐消失。她好像聽到了捉摸不住、由深處來的聲頻。突然有一個念頭,如果沒有了如許的動盪和不安,歌舞昇平,她不過在做讓人麻木消費或無關痛癢的製作,一切作為更變得可有可無。眼睛看見的四周圍,是朦朧的受暗黑吞滅了的景象,也好像甚麼都沒有。她相信看不見,不是沒有真實的存在。她們湊得更近了,觸感着彼此身體散發的暖意。漸行漸近,微光中,她們看見對方掩映的臉龐。不再去想以後會發生甚麼了,只是默默前行。
他們經過了築起鐵絲網的土地,穿越了行車天橋下的通道,見到地平線上浮泛的幻影與燈光,猶如某種冷硬的覺醒。遠處閃耀着一片絢麗浮華的虹光耀彩。素然不知,原來鬧市離這裡這麼近。不,梓南說,那是邊界,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
離留之間:文學 × 視藝展覽
展覽日期 10 月 30 日至 12 月 6 日
地點 香港藝術中心 包氏畫廊 4、5 樓 (灣仔港灣道 2 號)
開放時間 早上 10 時至晚上 8 時
開幕酒會 11 月 13 日(五)下午 5 時至 7 時半
參展作家及藝術家:
離開 | 回來 |
西 西 × 盧樂謙 | 顏純鈎 × 劉彥韜 |
也 斯 × 李家昇 | 羅貴祥 × 張才生 |
黃碧雲 × 葉 雯 | 董啟章 × 黃國才 |
游 靜 × 鄭淑宜 | 胡晴舫 × 林欣傑 |
潘國靈 × 白雙全 | 陳 慧 × 楊沛鏗 |
廖偉棠 × 鄧啟耀 | 呂永佳 × 郝立仁 |
寫作坊
日期:11 月 29 日(日)下午 3 時至 5 時
嘉賓:袁兆昌
公眾導賞團:逢周六、日下午 2、4、6 時
導覽時間每節約 30 分鐘
學校 / 團體導賞團:
周一至五 學校 / 團體可預約任何時段
亦可報名逢周六、日之公眾導賞團,
歡迎致電 23336967 或電郵 hk.literature.season@gmail.com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