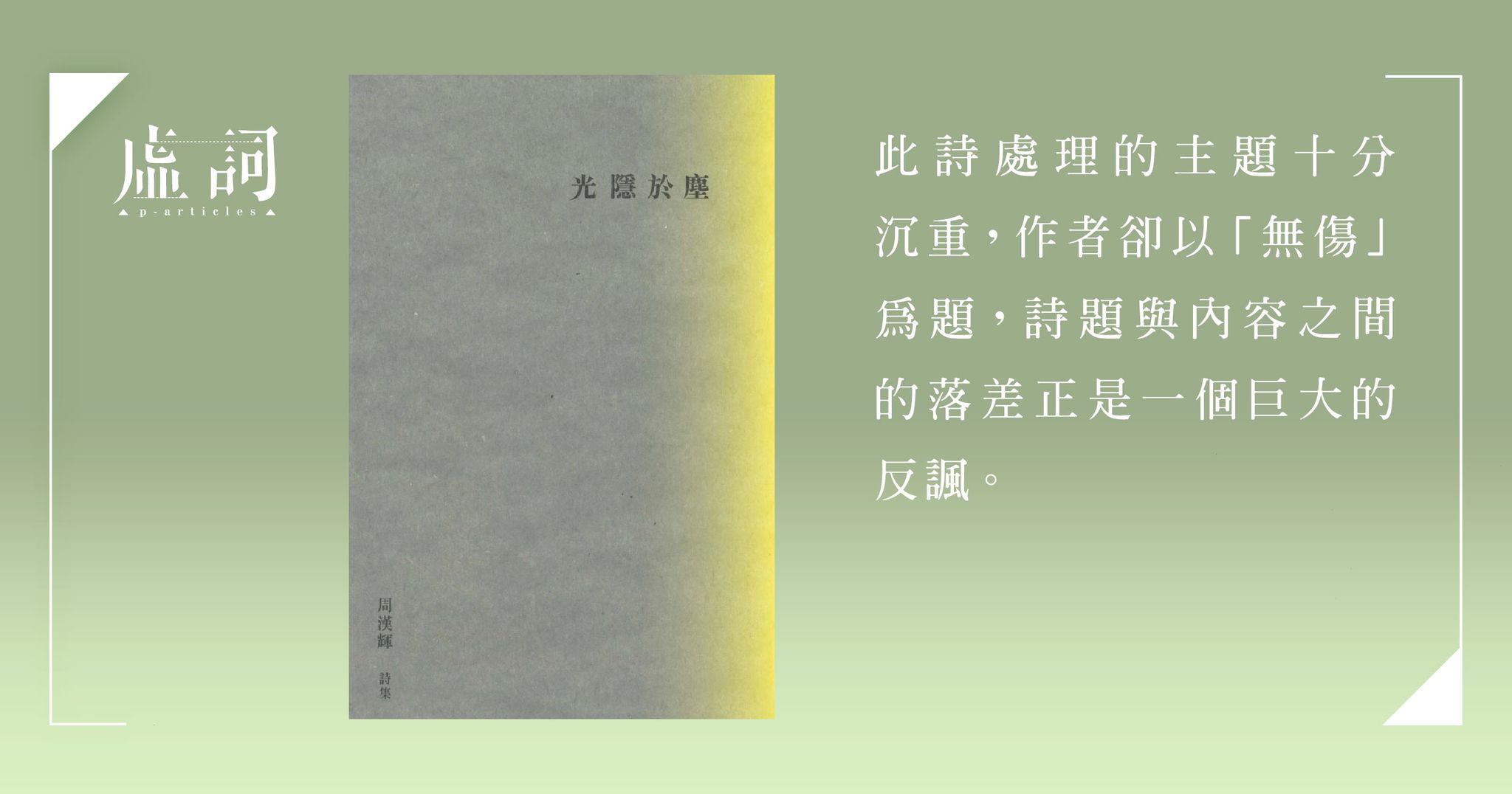被消失的痕跡——讀周漢輝〈無傷〉
I leave no trace of wings in the air,but I am glad I have had my flight.
——Rabindranath Tagore
「假如時間能夠倒流,就能……」。這應該是每個人都曾幻想過的事情吧!寫作是對時間的記錄,是以文字的形式為歷史長河中發生過的事情留下肉眼可見的痕跡。自赫拉克利特(Herakleitus)起,人們便開始以流動的水作為時間的喻體,以強調時間的單向流逝及連綿不絕。文字由時間所形塑,當然具備與時間相似的特性,但作為媒介的一種,文字亦有超然於時間之上、創造另一種感知方式的可能。香港詩人周漢輝便常常在其詩作中進行這種「時空的實驗」(註1),以敘事的方式讓故事和回憶如影像般不斷流動,慢慢進入書寫對象的生活甚至內心。
這一文字實驗在他的詩作中主要仰賴鏡頭的運用,他曾多次表示自己受侯孝賢等電影導演影響(註2),在寫作上有意學習電影的手法,甚至在2010年,他出版的第一本詩集便以「長鏡頭」命名。因此,當人們討論其詩作時,都難以回避對他詩作中鏡頭技巧自覺運用的探討。黃柏熹在為周漢輝所寫的一篇專訪中形容周的詩「像一個凝望開去的長鏡頭,默默地凝視著生活諸相,並轉換成平實的詩句」(註3);詩人韓祺疇更在〈角落裡一雙眼睛正好斜望你:敘事詩作的鏡頭運用──以詩集《光隱於塵》為例〉(註4)一文將周漢輝詩作裡的鏡頭手法細分為「蒙太奇」、「倒向回轉鏡頭」以及「空鏡頭」。本文承韓祺疇一文,並以詩作〈無傷〉為例,細談該詩作當中的鏡頭運用,以及所產生的新的敘事效果。
此詩共十四行,每兩行為一節,每節即為一個畫面。據周漢輝說,這首詩最初的版本並非如此,原本像他多數的長詩一般沒有分段,以散文式的手法一氣呵成,後來經過許多次的修改和剪裁之後才定型為如今這個版本。單看第一節,「細雨後街燈亮起,你/也醒來,向光點了點頭」,像一個再平凡不過的景色描寫。但當我們繼續讀下去,就不難發現「把胸骨塞回皮肉下」、「卻見葉子飛回枝頭」、「斷樹們一一接合自己」、「雨水是朝天灌溉的」這些意象都在告訴讀者,這是一首倒帶式寫法的詩作——作者代入書寫對象的視角,在「你」被折斷的大樹壓死後逆著時間而上,回溯「你」未死時的故事。
也就是說,這是一首有異於慣常敘事時序(時間朝向未來流動)的作品,作者借用文字創造了一種完全相反的敘事可能。也正因此,詩作中的用字除了最直觀帶給讀者的含義之外,更含有一種類似於「反辭」(註5)的表意效果。而且,不知作者是否有意為之,這首詩中用字的最終指涉又總是比其字面上的意思更為殘忍,例如第一節的「你也醒來」實際上是寫「你已死去」、第二節的「胸骨塞回皮肉下」實際上是寫「胸骨斷裂,刺穿皮肉」、「止血」實際上是「淌血」、「吹掉傷痕」實際上是「傷痕綻裂」、第五節的「斷樹們一一接合自己」實際上是「樹木一一斷裂」、「雨水是朝天灌溉的」實際上是「雨水朝向人間傾倒」、「陽光是收成」實際上是「陽光並非收成」。作者把傷害、死亡、斷裂和匱乏等令人愕然的畫面掩蓋在溫和的字詞之下,再輔以畫面與畫面(鏡頭與鏡頭)之間極為短促的嫁接,營造一種十分克制的敘事語感,緩緩地追述,不動聲色,卻欲蓋彌彰。
此外,詩中另一處,詩人亦嘗試在語句之間為敘事對象「你」創造另一種生命的可能。詩句「工人們收拾電鋸,斷樹們一一接合自己/那麼雨水是朝天灌溉的,陽光是收成」,前一句是詩人作出的前設,後一句則是基於這個前設而存在的可能——如果工人們收拾電鋸,如果斷樹們接合自己,那麼雨水就不會向人間傾倒,陽光就可以是收成了——詩作到此似乎為讀者帶來了一點點希望。眼看著書寫對象「你」可以在作者假設出來的時間裡免受雨災、有所「收成」,但最後兩節卻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反轉,讓前面的一切抑制和假設都落空。
周漢輝說他曾多次在教學寫作班時向學生播放Coldplay的The Scientist的音樂錄像,音樂錄像中的主角隨著音樂的進行不斷逆著時間後退。在視頻倒放的情況下,視頻中的許多動作(諸如單車騎行、人物走路、汽車滾落山腳等)便會帶給觀眾一種有悖常識的視覺衝擊,例如單車會逆向行駛、人物會倒退走路、汽車向坡頂滾動等。但除此之外,錄像中亦有一些動作並不會因時間的倒帶造成視覺衝擊,例如籃球被傳球時的軌跡,又或者主角在0分45秒至0分52秒站定唱歌時的動作,都看不出與正常時間裡的動作有任何相異之處。〈無傷〉這首詩也是一樣,詩作中,雖然工人的職業、健康、生死會因為時間的倒流而呈現不同於當下的狀態,但該名工人的處境卻始終沒有因為時間的逆流而得以改善。即使是在另一種時間可能裡,基層也並沒有脫離苦海,要麼死,要麼窮,時間的逆流只不過讓他從一種糟糕的處境,移至另一種糟糕的處境。
周漢輝在文藝復興基金會舉辦的「非正常生活節」中,曾以「時移空易:詩的天能」作為分享講題,分享會中他提到這個講題的命名源於荷里活電影《天能》。電影《天能》中,時間逆轉有別於時間穿越,並非從一個時間點跳躍到另一個時間點,電影中的「逆轉機器」只是改變了個體的時間前進方向,如果個體想要回到某段時間之前,他在時間逆轉後也必然要沿著時間之河逆流向上,經歷同等跨度的時長,而並非瞬間抵達。在這一過程中,個體曾經歷過的所有事情仍然在時間之流中持續進行。因此,無論個體溯流而上回到多久之前的時空,一旦「逆轉機器」停止運轉,那麼仍會按照原本的時序,把本已經歷過一次的事情再經歷一次。這與詩作中工人的處境極為相似。我們在文首談到,幾乎每個人都曾有過「如果時間能夠倒流,就能……」的幻想,當我們幻想時,往往會在省略號的位置幻想一個比現實處境更好的可能,以填補現實生活的某些匱乏。但〈無傷〉這首詩卻無法以這種理想主義式的結尾收結──詩人本想嘗試借用文字為書寫對象創造一種新的時間的可能,卻在詩作的結尾處發現,他的可憐的書寫對象在另一種時間之下的處境,一樣充滿了絕望。
此詩處理的主題十分沉重,作者卻以「無傷」為題,詩題與內容之間的落差正是一個巨大的反諷,韓祺疇曾指「( 這種手法是在)批判城市的冷漠,在一單樹木倒塌意外後,工人們清理現場,彷彿一切無礙」(註6)。這正是這座城市的隱喻,一些粉飾太平的人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美化、遮掩城市之中個體的傷痕,虛構一種繁榮和平的假象,好在詩人用他的筆將這些傷害以另一種形式保存下來。周漢輝的詩歌總是以基層的視角揭開這座城市的疤痕,即使是一本被下架的詩集,也總會有人曾經見證過它的存在,總會有另一種形式讓它得以保留下來。
2021.12.3夜
註:
1. 周漢輝接受「今晚See詩先」訪問對談時的說法,見「今晚See詩先」第六集節目「詩人之天能,周漢輝之光影逆行」。節目鏈接:https://open.spotify.com/episode/1645CmVysQyB724IxnKElP?si=nUnqOTwBR5S8m1Bw0yhDAg
2. 周漢輝在專訪文章〈慢慢走在塵世間,寫在深河裡浮沉的人們——訪詩人周漢輝〉中說「我記得侯孝賢導演,曾分享他一個小時候的經驗,影響了他以後做導演。小時候,他很喜歡爬上芒果樹,當向下望時,就發覺自己好像從時空抽離。他看到有人走過、有人乘涼,好像用了另外一種眼光去看世界。滔光去說,現在我也希望用另一種角度——一種抽象的角度,去看這世界。」專訪文章刊於《微批》,鏈接:https://paratext.hk/?p=99
3. 黃柏熹:〈凝望城市的「沉默」人物——訪詩人周漢輝〉,刊於2019.11.4期《虛詞》。
4. 韓祺疇:〈角落裡一雙眼睛正好斜望你:敘事詩作的鏡頭運用──以詩集《光隱於塵》為例〉。文章鏈接: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2/20210220.html
5. 陳望道在《修辭學發凡》將「反辭」定義為「說者口頭的意思和心裡的意思完全相反……是用與本意相反的話來表達本意的一種辭格。」
6. 同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