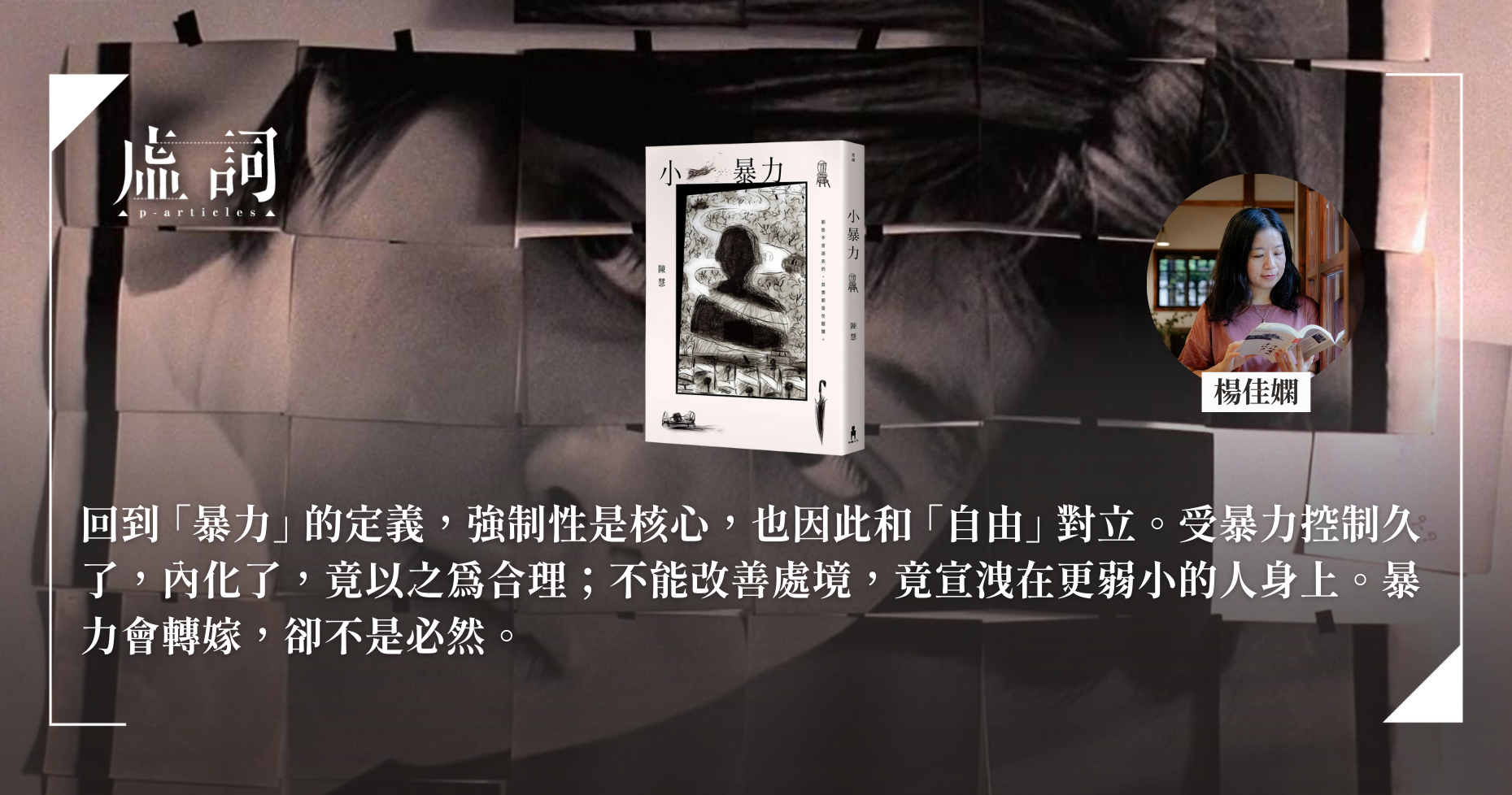【新書】陳慧《小暴力》序〈暴力與自由的賦格〉
個人在最傷痛的時候
才會變成鳥兒
或者一隻或者幾隻。
——淮遠〈保證〉
什麼是暴力?
查閱《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暴力」指「激烈而強制的力量」;而《家庭暴力防治法》則解釋,「暴力」乃「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根據以上,暴力具有強制侵害性質,且不單傷害身體,還包含抽象、生活等層面。那麼,暴力有沒有大小之分?根據什麼來區別?參與人數?發動者的位置?影響的規模?由個人來施為是小,由國家發動是大嗎?或者,暴力就是暴力,看似微小,也可能積累為大,而大規模的暴力,又往往落實在許多微小的惡行上?
陳慧最新小說《小暴力》,主要通過小顧、白大順、洪安安、洪啟瑞、周郁芬、李立中、夏木、金理高這八個人物,講述暴力的流動,從上一代到下一代,從職場、歡場到家庭,遮蓋於親子關係或黑暗房間,而街頭上,陌生人之間,看似暴力的作為卻反而蘊含著愛——暴力的反面,就是愛嗎?我們要怎麼分辨呢?——有些暴力,會以愛之名加諸於你我;有些愛,卻不得不以暴力型態現身。
小說裡的幾個年輕人,各自有來處與身分,卻未必按照搭好的框架來生長。小顧考上台大,本可以成為普通意義下的有為青年,卻跑來讀警專,從基層警察當起,默默在日常勤務之外進行隱密的正義;白大順是黑幫領袖白龍的兒子,洪安安是政壇有力人士洪啟瑞的兒子,兩人卻有一雙早熟之眼,思索著如何從現實突圍;從香港跑到台灣、自稱叫夏木的青年,黑衣遮蓋著受過的外傷與內傷。而小說裡已經在險惡紅塵中打滾經年的大人們,多半糾纏於名利欲望,期望能控制更多人與事。李立中想當系主任,金理高勤於服務為了尋求認同,洪啟瑞不惜拿兒子當工具為了能更好地運用妻子娘家的政治資源,好讓他在產業界與政界上下其手。唯一的重要女性角色周郁芬,還保有清明之心,從利己的大人世界中走出來,和那幾個年輕人走在一起。她本來是夏木的母親,後來,她把洪安安也納入羽翼,甚至,願意做一個聯繫者,傳遞者,行動者,因為黑衣夏木的張皇和疼痛,喚起她想起昔日的香港,走入今日的香港。
表面上,《小暴力》似乎講的是年輕人怎樣對抗父親,女人怎樣對抗男人,基層怎樣對抗體制。難道陳慧想回應現代文學裡「救救孩子」(甚至是女性解放、讓下屬說話)的呼聲?不,陳慧願意讓受壓迫者擁有更高的動能,讀者將發現,孩子知道自救,女人可以出走,基層也有他游擊、滲透的策略。看似對抗的兩個世界,其實只是一個世界,端視你看到的是哪一種價值。洪啟瑞擁有的只是工具理性,所以不把人當人看,連兒子也不放過,李友中和金理高過得不快樂,起碼還有一點人性的軟弱。周郁芬呢,她曾失望地從香港出走,離開愛人與兒子,在台灣她坐進婚姻的艙內,狹小然而安穩,然後她再度出走,獲得了久違的自由。在新的自由裡,周郁芬知道她不單單為了夏木,而是為了夏木「們」,受侮辱與受損害者們,同情共感,甚至共軛,「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她說這是文學高揚過的騎士精神,「老派的態度,但並沒有過時」。
回到「暴力」的定義,強制性是核心,也因此和「自由」對立。受暴力控制久了,內化了,竟以之為合理;不能改善處境,竟宣洩在更弱小的人身上。暴力會轉嫁,卻不是必然。
也有人拼命想逃出暴力的輪迴,連結其他受到暴力擠壓的人。
《小暴力》密碼之一,開頭已有提示,靈感來自楊德昌《恐怖份子》。熟知這部經典電影的讀者,想必早就發現了小說角色命名和人際關係,和電影有其相類,故事卻是新創。已移居台灣幾年的陳慧,也對此地荒謬時事不能無感,每逢選舉必然浮現的論文抄襲爭議、所謂產學合作實則畫大餅分權力,也成為《小暴力》塑造人物事件的材料。過去提到陳慧,很容易歸入「香港文學」,不過,《小暴力》在台灣寫作,超過八成的故事場景在台灣,香港和它發生的事,成為隱微的心事、未來的基礎,可以說,這是一部擁有香港關懷的台灣文學。地域的標誌對文學並非毫無意義,是寫作者移地再煉的手藝。
最後想指出,「文學」在本書中是「自由」的另一種形式。洪安安,因為在廁所牆壁寫詩,才會與白大順相識。活在家庭暴力中,是無盡的閱讀與寫字讓他的心靈有逃脫去處,即使如《宋詞選》這樣看似「無用」的書籍,即使不一定看得懂,在抄寫中,「逐字搬到白紙上,胸臆間難以言喻的哀傷竟似有了出口」,於是他至少懂了另一個層次,方塊字「單一存在,意義不大,但只要通過組合、連結,就能被賦予無盡意義」。周郁芬再次出走,也受文學意外的流傳而驅動。
在這個絕地求生的台灣故事裡,「香港」和「文學」是兩條隱伏泉脈,它們自傷痛和回憶裡湧現,成為打開《小暴力》的另外兩個密碼。因此,淮遠〈保證〉裡的提問:「有什麼使牠們/飛得這麼漂亮?」才能有這樣的回答——
不是翅膀
翅膀從不能成為一種力量
只有痛苦和哀傷
是牠們能夠永遠自由自在地飛翔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