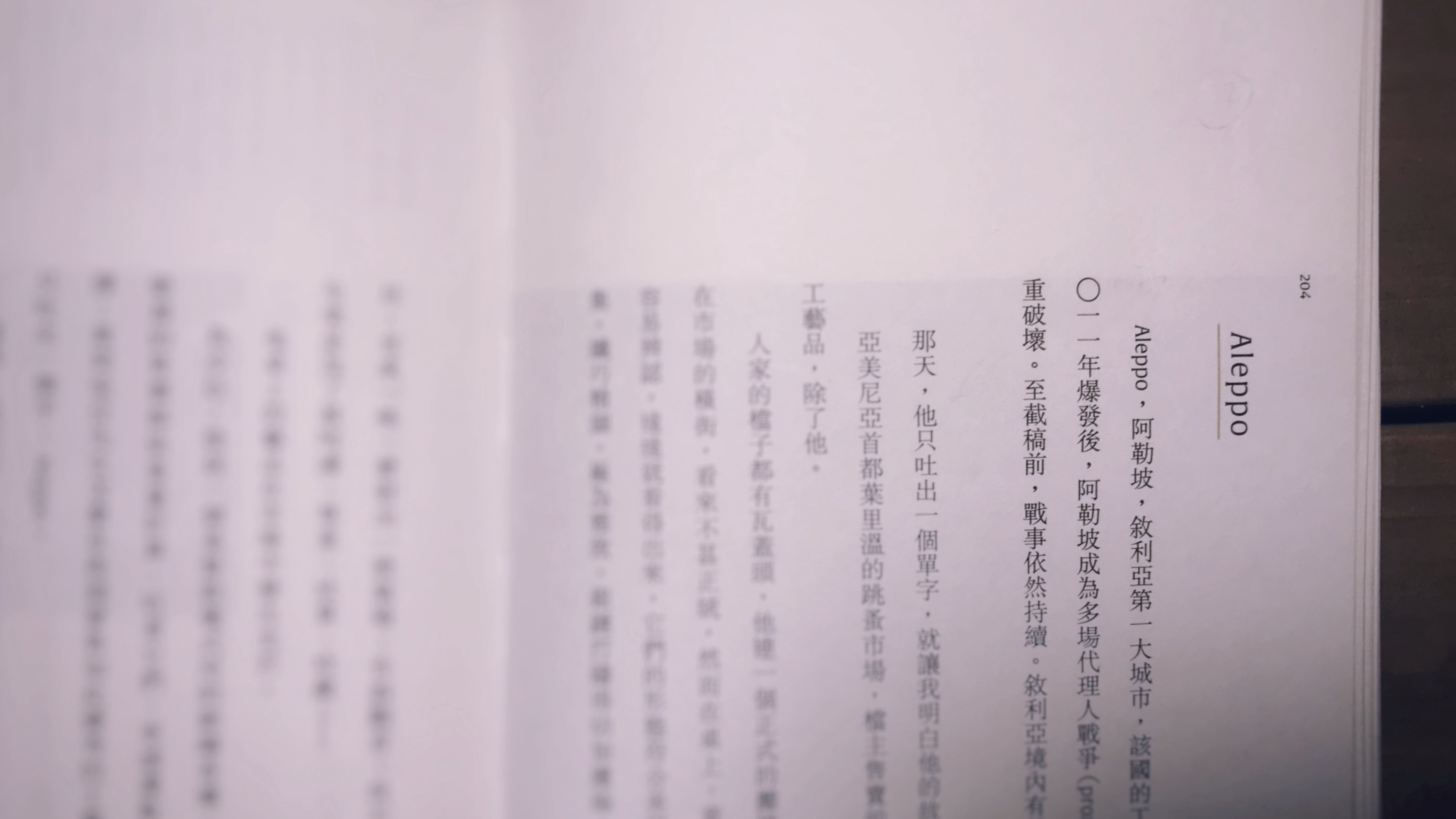潘國靈 X 卓韻芝:香港文學季開幕講座——我們總是迷路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0-10-28
香港人素來熱愛旅行,疫情下無法出國,Staycation隨即成為熱潮,有航空公司甚至推出Flycation,一個半小時的環港遊,彷彿是模擬了旅遊獨有的遊移狀態。今年香港文學季的主題碰巧名為「遊移字得」,意指在遊離與移動之間創作得以生成,這個與現實語境互相矛盾的主題,不禁讓人疑惑:當我們無法再遊離移動,寫作又如何可能?這晚文學季的開幕講座「我們總是迷路」,便邀請了袁兆昌作主持,潘國靈與卓韻芝作嘉賓,一同分享遊移、迷路與文學之關係。
在講座開始前,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鄧小樺先作開幕致詞,點出「遊移」的意義在於穿越邊界,透過身分、國族、地理、歷史的分野,我們得以構成自我。縱然今年受疫情所困,肉體的遊移並不可能,鄧小樺卻認為以「遊移字得」作為香港文學季的主題更顯其重要,因為「遊離與移動不限於物理空間,亦在乎心靈。閱讀與創作不受地域所限,是一種自由自主的內在移動實踐,因此外在受限,卻讓我們對自由有更大體會,竭力尋找一個更多變化的自我、更擴闊的心靈。」是以,文學與遊移是互為因果的雙生兒,哪裡有文學,哪裡便有遊移,又或說,文學總發生在遊移與停駐之間,又或是突如其來的迷失之中,是次講座裡,潘國靈首先分享了他浪遊於城市的經驗,再由卓韻芝分享她在山野迷路的驚險之行。
跟著作家去旅行
不同的遊移方式決定了我們的旅程,潘國靈開場便隆重其事地亮出簡報,娓娓道來不同類別的遊人。自言是半個浪遊人(Flaneur),既是旅人(Traveller)亦是遊客(Tourist),有時更是「人文朝聖者」,潘國靈「總是徘徊於停駐與流動、寓居與在路上之間」,只因為「在鐘擺的狀態中,才找到力量」。他接續分享了不同階段的旅行經歷,如大學畢業後的英國之旅,成為了日後旅途的「起點」,標誌著年少時遠闖他方的慾望;終在紐約旅居一年後,寫成《第三個紐約》。無論旅遊、遊學、旅居、公幹還是閉關寫作,這些形態不一、出發點各異的旅程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總是離不開文學。
潘國靈喜歡帶著書本遊蕩,他「很少有完全摒棄書的旅行」,因為「書也是行李的一種,有時你去一個地方,便是因著讀了一些書。」曾為杜拉斯遊歷湄公河,為John Lennon到訪Liverpool,亦因著語言之美而到巴黎,在紐約時,潘國靈甚至找到了Jack Kerouac寫出成名作《在路上》的公寓、詩人Edna St. Vincent Millay暫居的狹小房子,又找到了數十間「垮掉的一代」到過的酒吧。這些書籍與作家帶領旅人開拓新路徑,又反過來豐富他的文化想像。如潘國靈在捷克酒吧體會到《過於喧囂的孤獨》的「狂歡」;在陽光猛烈得近乎刺眼的希臘,想通何以《異鄉人》的莫梭會因為陽光猛烈而槍殺阿拉伯人;在雅典往長島的茫茫大海上,他失掉時間感,繼而想起傅柯說,最後的「異托邦」是船。這些體驗與文學密不可分,即使閱讀與當地無關的作品,如他在英國的火車看《罪與罰》,又或在奧地利看里爾克《給青年詩人的信》,卻意外地豐富了旅程的體驗,如他所言,「在旅途中閱讀的書本,會從此成為旅程的記憶」。
城市作為文本
潘國靈的旅程是文學世界與現實世界的對疊,他以「城市作為文本」作喻,說明兩者之相似。他形容有些城市和書就好比「經典」,要作好準備才可前往,因此「旅行要適得其時」,在一定的年紀去中歐,才能真正體會到當中的沉重歷史。於是,潘國靈亦稱去年開始踏上中南半島之旅,是一種適得其時。旅程的開展彷是身體的呼喚,「我在某個失眠夜,在朦朧的意識下無故訂了隔天去緬甸的機票」,於是他兩手空空,連電話卡也沒有購買便上機;後來到訪河內時,又在首天的行程跌壞了手機,唯有用紙本地圖在城市裡遊走。這些經歷讓他醒悟,原來我們賴以為生的科技並非必需品,甚至乎是另一種枷鎖,讓我們無法放下自身的包袱或牽掛,得到真正的離開。他續說,「原來人在自以為缺失的狀態下,依然能夠生存。」
或許真正的行李只有書,潘國靈又指出,城市或書都講求緣分,「有些書藉,有些地方大概終生都不會到訪;有些即便是到訪了,亦未必會重臨。」有幸重逢的話,舊日的經驗也將變質,「縱使城市沒變,書沒變,旅人卻必會改變。」旅遊與閱讀的本質有如曇花一現,這又讓潘國靈明白到旅遊書寫的重要性,因為「去旅行就如看書一樣,唯有在字裡行間你才真正置身其中,當你完成一本書或旅程,它就會快速褪色,所以必須在路上紀錄,或者在事後重構,其餘的就只能任它消逝。」
旅人與作家合一
旅遊書寫是一個稍縱即逝的過程,旅遊作家亦不是一個必然形成的身分。潘國靈把作家籠統地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從不旅行的作家,如終生在里斯本的一條多雷斯大街居住的佩索亞,他笑言「佩索亞沒有旅遊,但有神遊,因為沒有東西能阻擋詩人,平凡都是詩意。」有些作家卻經常去旅行,如綠騎士、黃碧雲、胡晴舫、李昂、阿城等等。潘國靈即使周遊列國,但他卻從不自居為「旅遊作家」,因為他認為這個身分也是「曇花一現」的。他以社會運動為喻,說明自己「在參與社會運動時,往往只覺得自己是公民,很少會覺得自己是個作家,然而總有些時刻這兩個身分合一,就能寫下一些紀錄。同樣地,當旅人與作家的身分合一,就會產生旅遊書寫。」潘國靈繼而謙稱,《第三個紐約》便是在「身分合一」的情況下完成的,後來為了寫《寫托邦與消失咒》,他甚至把自己困在北京的一間酒店裡閉關創作,這又讓他想到,一般人會在假期裡安排旅程,作家卻總想著要寫作,羅蘭巴特在《神話學》裡的《Writers on holiday》中便提到作家放假是勞動的悖論,作家與旅人的身分,有時又互相衝突。只是,當旅程結束,一切又隨即消逝,因為「所有旅人的身分都是暫借的、過渡的,最終都一定有歸期。」
虛構的旅行
潘國靈説旅人總會回家,卓韻芝亦認為,當我們在去旅行時,最終必然會説「返屋企」。主持袁兆昌便指出,「卓韻芝的《峰迴路轉》不只說旅行,當中也涉及童年,是一本與家有關的旅遊書。」講座中,卓韻芝率先朗讀了自己在《峰迴路轉》裡所寫的序〈無章的生命,無限的比喻〉:「旅行的起點與終點,是家,並且必然是家,否則的話,移動可能是遷徒、升學、流浪或放逐,是作為起點與終點的家,定義了旅行。」換言之,旅行只是以另一種方式「在家」,短暫脫離並不實在,因為每趟旅程終必折返。然而這個「家」對卓韻芝而言,又有如潘國靈所言的「行李」,是她在日常生活中所負載之物,亦包括她讀過的書、嚮往的作品、既定的觀念,又或是生活模式,就如她年輕時,因杜魯福而去巴黎,因費里尼而去意大利,因博爾赫斯而去阿根廷。(本來卓韻芝還預備了一些《峰迴路轉》的宣傳片跟觀眾分享,可惜因為技術問題無法放映,特別在文末補回影片,與讀者分享。)
旅遊製造的短暫逃離似是而非,在卓韻芝的文學創作中,亦試圖打破這一道牆。她說,「旅行文學有趣的地方,是它有一個框架,當讀者看的時候,會假設這必然是真實的,所以我嘗試打破真實與虛構,在我最近創作了一篇中篇小說中,就是以虛構的情節書寫真實的旅遊經歷,故事中講述兩個自己一同去旅行,當然現實中的我只有一個。」
迷失總在意料之外
當潘國靈在「無意識」的狀態下買了一張去緬甸的機票,卓韻芝也是在潛意識的召喚下走進了山野。「不知從何時起,我突然喜歡上行山,甚至會為行山而去一些特定的國家,但如果我這個無章的生命去到這個階段,我的肉體竟然先於我的想法要前進,我覺得我要聽從這個呼召。」
山野之旅總會遇上迷路,這讓卓韻芝無法認同「沒有迷失這回事」的說法。去年三月,卓韻芝便經歷了一場凶險的迷路經歷,當時她獨自前往英國北部區的Lake District登山,「我以為山路易走,既不必攀山涉水,還可接收Wifi訊號,於是信心滿滿,忽發奇想,連八元一張的行山地圖都不買就登山。」誰料走著走著,眼前突然一片迷濛,被濃霧圍困的卓韻芝拿出指南針一看,發現前面北方竟是懸崖,當時仍有途人經過,她大可問路求救,然而她堅信要靠自己尋找路徑,「我自覺只要一直前行,總能走到目的地。」於是她拿出電話,在網上搜尋了一張低清地圖嘗試定位,卻發現在低溫的環境下,手機的電池量急劇下降,本來自信滿滿的她,終於不安起來,唯有硬著頭皮向前行,「我發現腳下的泥地漸漸變成泥濘,耳邊還有呼呼的巨響,原來,我走上了一個瀑布頂。」
在這稍一不慎就會墮下的瀑布峰嶺旁邊,只剩一條約兩腳寬的小路,卓韻芝前無退路,唯有鼓起勇氣,試探小路路況,幸好泥土尚算結實,唯獨不知中段路況如何。在這性命攸關的時刻,她拿出了電話,「我用僅餘的電池,拍了一條短片給老公道歉,然後便把電話關了,爬了下去。」她手腳並用,幾乎坐著垂直滑下斜坡,好不容易滑到一半,才看見前方有鐵欄杆,終於鬆一口氣,「我知道,我再次回到文明世界了。」死過返生後,迎面走來一對父子,他們的從容對比起卓韻芝的狼狽,有如諷刺。
於是,當卓韻芝抵達城中小鎮後,儘管已是全身發冷,她仍執意買了一大杯啤酒,並堅持在室外把冰鎮啤酒喝完。她一邊喝酒,憑藉寒意強迫自己清醒過來,一邊回想整天的旅程,這才發現,「其實那座山很矮,我也不真的那樣冷,霧不那麼大,天不那麼黑,我之所以恐懼,全因路況出乎預期。我和那對父子明明在走同一條路,於他們而言可能只是一次熟悉的散步,於我這個外人而言,卻幾乎要與親人生離死別。」意外過後總有收穫,這次旅程讓感悟,「迷失是存在的,而真正的迷失總在意料之外,無法計劃。在這個失衡的經歷中,我卻得到最多的體驗、最意想不到的啟發。」
走路,走的是心路
另一次讓卓韻芝印象深刻的行山經歷,則成為寫作題材,寫進了《峰迴路轉》中,那是在加拿大西面的Victoria Island,她背著35公升的大背包,徒步走了六天。本以為需要澗水而行,怎料河道乾枯,甚至沒法洗澡。與預想的不同,卻成為了她最辛苦又最快樂的一次登山經歷。「行山的過程中,體力消耗是不能控制,早午氣溫的驟變,或是路況的改變,已能大大改變你的消耗量。這種不可預計性,才是最消耗人的體力和意志。」於是,當卓韻芝提筆寫《峰迴路轉》前,她便提醒自己要在書中表達「意志的力量」,「所謂走路,走的其實是心路,是你的心在行,是你的心控制你何時疲累,何時想放棄。如果你能控制你的心,或用開放的心態,意志就不會那麼容易被消磨,你就能走更遠的路。」因此卓韻芝的山野之旅,其實更像一場心靈的出走,相對於近年的行山打卡熱潮,卓韻芝自言根本不會帶相機登山,「我不需要相片,因為我的靈魂已與這座山連結了。」
所謂「遊移字得」,說的也是一場心靈之旅,即使今年無法自由穿梭於別的城市或山野,甚至在自身的地方與街道,亦受到規管,但我們依然能在閱讀與寫作中不致迷路,獲得內心的自由。
卓韻芝《峰迴路轉》影片:
卓韻芝《峰迴路轉》1
卓韻芝《峰迴路轉》2
卓韻芝《峰迴路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