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們翻起第一片土——董啟章、甄拔濤、袁兆昌談《自由如綠》
專訪 | by 李卓謙 | 2018-08-10

董啟章為《自由如綠》創作了〈楓香〉。
「香港文學是城市的文學。」這種印象或許太過根深柢固,以至當我們想數出一兩本香港書寫自然的作品時,幾乎都會為之語塞,糾纏半天或許只能道出吳煦斌的名字。訪問幾位參與撰寫《自由如綠》的作家,幾乎都不約而同說到,在香港寫植物/自然的作品,不是沒有,但實在少。
如此,由廿四位香港作家寫廿四種植物的《自由如綠》就成為了異數,更是史無前例。相較在台灣已經發展得頗蓬勃的自然書寫,香港或許只是剛剛起步,董啟章說這是一本播種插秧的書,而不是收割的書,「這本書或許能夠打開一個局面,由原本沒意識,再以寫作去接近,而每個作家又有自己的風格,自己對待事物的方式,出來的結果不是要展現香港作家對植物有多熟悉,而是香港作家很努力嘗試去認識植物。所以對我來說,這是一種開墾。」
董啟章:自然已融入我的時間感
談到董啟章與植物交集最多的作品,自然是《博物誌》,他在書中以豐富想像力將人與自然物結合,寫下一篇篇異想天開的故事;在《自由如綠》中,〈楓香〉的構思也是衍生自《博物誌》裡的〈楓樹〉,環繞一對夫妻的日常,而故事中虛弱的妻彷彿又與被城市過度規劃與整頓的樹木,有一種同病相憐的悽涼。
董啟章書寫植物方式有幾個階段演化。他的成名作《安卓珍尼》講述一位女學者走進山裡去尋找一種雌雄同體的生物,儘管生物是虛構的,但也必然牽涉到對山野環境的描寫,那時他會親身到大帽山觀察環境,亦進行資料搜集,但他說那時植物與作品的關係還是比較表面,只如場景佈置一樣。直到構思《博物誌》時,他開始透過植物形態進行聯想,以植物給他的感受,結合想像力來創作極短篇故事,作品的幻想色彩濃厚,「認識植物時是資料性、事實性,但寫的時候會變成幻想、想像色彩的東西,當中可能有象徵成分,有純粹氣氛營造,或是隨意聯想,但都是環繞植物去發掘,看看可以變出甚麼。」
寫下幾本長篇小說之後,董啟章發現自己的小說裡存在一種時間模式,就是他很多長篇都是由夏天開始,橫跨一年四季,又在夏天結束,《時間繁史》與《學習年代》也是如此,在季節的循環中,自然生態、氣候等元素都自然而然地融入小說裡,他甚至開始覺得,自然景觀在作品的呈現並非一種點綴,而是與小說角色經歷的生命形態有某種內在關係,「我追溯不到是何時開始,如果馬後炮一點說,或許這些自然景物已融入在我的時間感中。」
甄拔濤:從一棵樹看宇宙內涵
劇場編導甄拔濤的〈柏林的金魚〉在文體上別樹一格,採取一句一段的方式,對白夾雜敘事,既像劇本也像小說,甄拔濤說這種寫法源自劇場新文本一脈,新文本打破了從前寫實劇、荒誕劇的寫作方法,只要你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形式,怎樣都可以,「以前的人會覺得劇本寫時地人,其實唔需要,編劇唯一需要處理的就是語言,語言當中已經包含所有你要知道的事,可能有人不覺得似劇本,但其實這樣已經能排一套戲。」
構思〈柏〉期間,拔濤正為《灼眼的白晨》重演做準備,五月在柏林待了兩個星期,散步時忽然想到,可以用《灼》的寫法來寫〈柏〉,他假設《灼》裡一位死去的角色並沒有死,由此發展出新的故事。以異地戀作為故事的根基,最終選擇了代表「青澀」的人心果。「人心果給我的感覺很raw、很green,它有potential變成更mature或更完整的東西,但本身蘊藏了很green很fresh的能量,我就想,不如將它變成一個角色的性格。」於是便有了林林這角色。
關於自然的著作,拔濤未必讀得很多,但有一本卻始終印象深刻,那是Chet Raymo的《穿越宇宙的一哩路》,作者是大學教授,他寫自己由家步行回大學那三十分鐘的路程,途上所見的一花一草一磚一瓦都是通向天文、生物、歷史與文學的門徑,短短的路程原來已蘊含了宇宙的內涵。直到現在,他走在路上的時候,也會格外留意路邊的野草與樹木,它們是如何以不同方式展現頑強生命力。
袁兆昌:我們踐踏自然而生
袁兆昌〈逃出露兜葉〉寫一位賣金絲貓的老伯,「我」一直只是從旁人口中得知這位老伯,卻不知他早已身故,而且還每天在橋下看見他,小說以回憶敘事的結構來營造懸疑氣氛。養金絲貓是袁兆昌讀書時代的回憶,那年代的小孩喜歡養金絲貓來互鬥,而金絲貓就是養在由露兜葉摺成的小籠中。袁兆昌由此借題發揮,寫小孩如何看待生命與死亡,也牽涉一點人對死後世界的恐懼。
由植物進入生物,人如何把生物捕捉、豢養,又虛擬一個自然環境讓牠們生存下去,「當時我們不知道,但其實小朋友會將他們的慾望投射進去,金絲貓容易養,又可以讓牠們互毆,其實是在滿足一種叢林法則。」袁兆昌說。由此他帶出兩代人對待自然的分野,「以前的小朋友沒有公共或自然的概念,他們只是見有東西可玩就拿上手玩;而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會與自然有多一種親近,那種親近是來自他們的環保意識,比如知道塑膠飲筒會對海洋生物做成傷害,現在的年輕人對自己的生活多了戒心,知道應該保護大自然。」
袁兆昌認為我們並非隔絕於自然,只是有時忽略了它。「我們成長的公屋,幾十年前也是個天然、自然的地方,所以我多少覺得我們是踐踏自然去成長。」他懷著這種自覺去寫這篇多少有點懺悔意味的小說,懺悔的對象除了是被我們忽略大自然,更是那些我們忽略的、讓我們有機會接觸大自然的人,例如那位賣金絲貓的伯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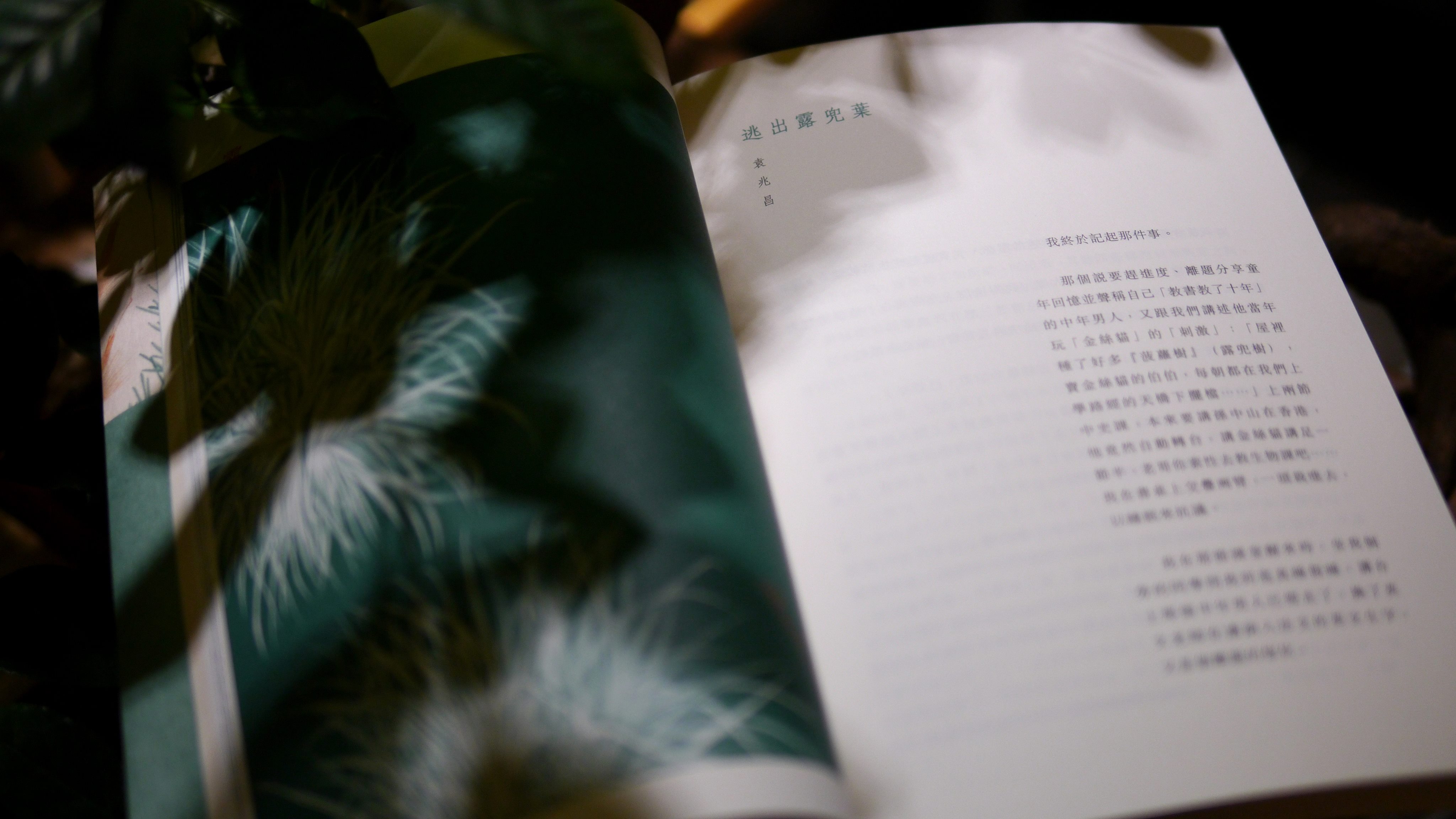
還是要問︰我們為何書寫植物?
集體創作在香港並不少見,但以植物為題的則很少,袁兆昌說:「西九所建構的是一個非自然的東西,另一方面卻像葉公好龍一樣,重新接觸大自然,也不是一件壞事,不過我們要再思考,我們是利用自然,抑或與自然相處。」甄拔濤認為《自由如綠》是一次新鮮的策劃︰「這件事有趣的地方是,它有點像contemporary art,就像策展一樣,策劃的方式本身已開啟了一些想像力,而一本充滿想像力的作品就這樣誕生了。」
說到底,董啟章認為我們不應該忘記人與自然的連繫,「我們以為人是獨特的,與植物動物在本質上不同,其實不是,我們是一樣的,只是有不同層次的演化,書寫植物讓我們不要忘記自身與自然的聯繫,如果斷了這種聯繫,我覺得我們會失去對自己本質的理解。」於是《自由如綠》作為一種有意識的嘗試,或許能夠打破城市與自然二分的局面,讓我們從另一角度對待香港文學、對待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