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同志,跟住去邊度?】詩的酒徒岑子杰:我以文學的心態寫發言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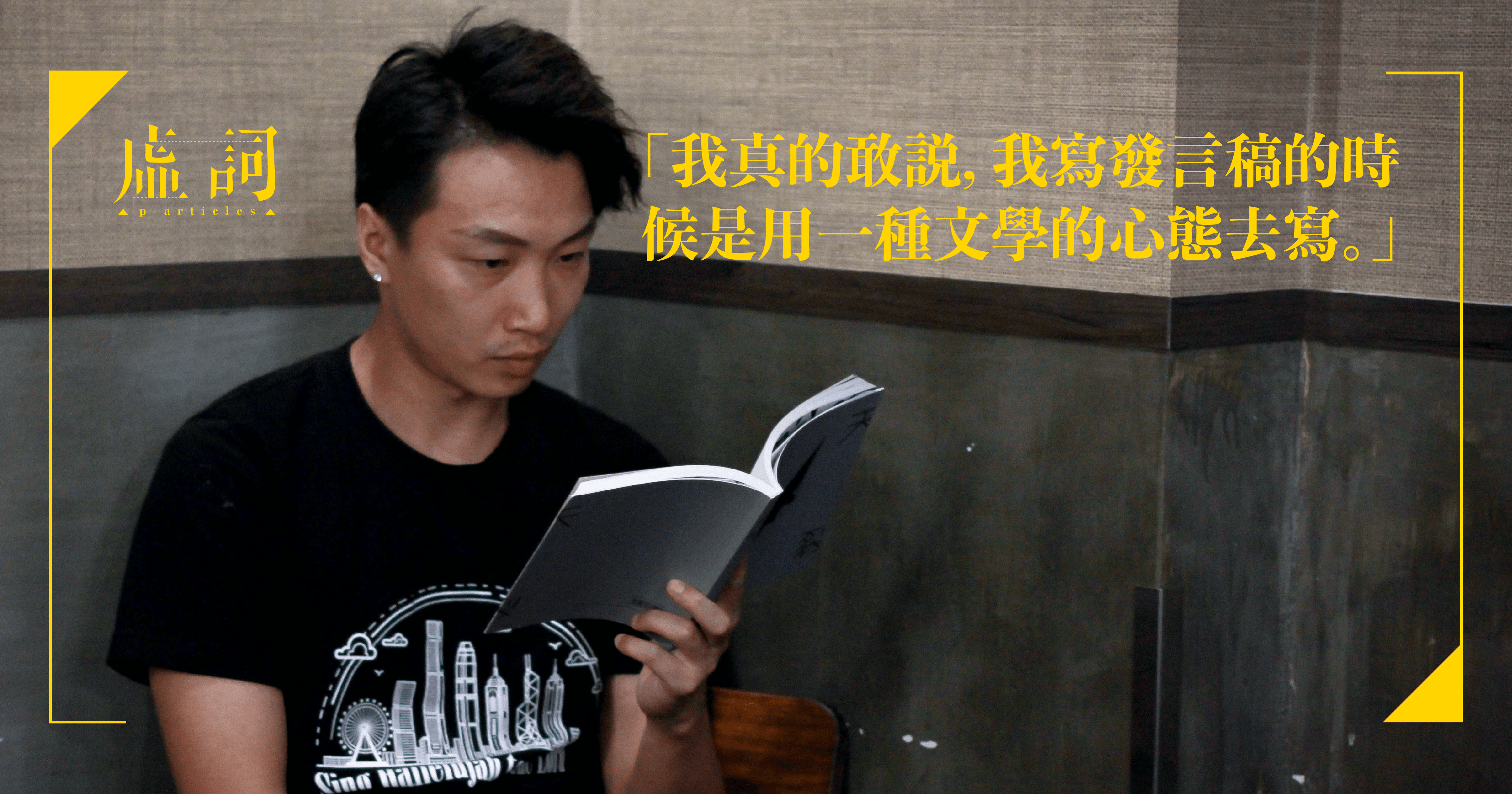
攝:黃柏熹
訪問在岑子杰二度受襲之前。當晚正值特首林鄭月娥首場「社區對話」,民陣召集人岑子杰坐在筆者面前,正看得入神;不是新聞直播,而是一本香港同志詩人的詩集。後來他提起自己逛書店的經驗:「當我打開一本好正的詩集,讀到一首好正的詩,我會心跳加速、站不穩、超級興奮的⋯⋯我看到靚仔也沒有這樣的狀態!」
經常在鏡頭面前發言的政治人物自有他的魅力。岑子杰這時表現出來的,卻是說起心愛事物,不免變得雀躍的神情。或許很多人都沒想過,岑子杰除了是同志,是社運人士,也是一個喜愛辛波絲卡和李清照,自小學開始一直迷醉於文學的文藝青年。
「好的文學應該令人醉。」
「我覺得,好的文學應該令人醉。」訪問裡,筆者最深刻的是岑子杰這句說話。沒有一定程度的文學閱讀經驗,大抵不會輕易把這種說話說出口;當你知道岑子杰的文學資歷,絕對可以肯定他夠資格。
岑子杰小學時期因為無聊,TVB 又不好看,隨手拿起一本《唐詩三百首》, 從此愛上讀詩,後來便是《詩經》與《宋詞》。「小學時我已經懂得背《長恨歌》。」讀到中五,課本上的詩他都一早背過了,《燕詩》、《木蘭辭》、《古從軍行》,他在筆者面前一一背誦起來,「其實沒有刻意去背,讀過數十次便會記得。」
岑子杰說,小時候喜歡李商隱,長大後覺得是一件「好撚造作」的事:「『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考杜鵑』,其實真的不知道到底在說甚麼;但他的文字真的很美,文學上好像是一個不可解而美麗的東西。」後來喜歡白居易、李清照和納蘭性德,中三開始接觸新文學,第一首讀的是洛夫的〈子夜讀信〉,然後就是北島,「最反叛的時候當然要讀北島啦!再後來便是夏宇,當時會想:為何這個人的詩可以那麼殘忍,卻又如此美呢?」
「一首好的詩,就像〈甜蜜的復仇〉吧。『老了的時候/下酒』,那一份既甜蜜又帶有仇恨,對於失落的那種,想忘記又想保持,想保持又不想再受到傷害的矛盾,足以令你感受三百年。」他說的時候,語氣甚至帶有半分醉意,想是仍在那三百年之中。
迷霧同志 文學中辨認自己
岑子杰是同志,中三、中四才知道自己的性取向。在異性戀主導的社會,身為性少眾,從來都要經歷「發現性取向」的歷程。那時,同志文學為他打開了同志生活和情感的窗口,讓他看見一道被社會主流壓倒的風景。
岑子杰最初讀的是台灣同志作家許佑生的小說,後來也讀了《 1 和 0 的故事》、《突然獨生》等香港同志文學作品。中學時期還未開始接觸本地同志組織,同性戀的生活和愛情,在他來說都是未曾知曉的經驗:「我很難把小龍女變成一個靚仔嘛。就算我把小龍女變成靚仔,也不是一個同志的愛情故事,因為同志的感情有它的特色。」
他以同志詩人陳克華的詩作〈我們總是愛人一般相遇〉為例,詩中提及一段先做愛然後才發展關係,最後發現彼此不適合的故事,「不是說異性戀沒有這種事,但同志對性的枷鎖的確比較少。這樣想來同志的愛情故事會是一個蠻好的倒敘。」當然,這裡說的「順敘」只是異性戀的劇本,而我們打從出生以來就活在這個故事裡面。
「你明白嗎?作為一個同志,我很難幻想自己的愛情生活會面對甚麼。那時讀同志小說,令我感受到不同的愛情模式所帶來的糾纏、掙扎和傷痛,譬如是得到家人支持的感動。現實中你當然不敢把同性伴侶帶回家。」「文學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在事情未發生前讓我們『搶先看』,又或是經歷一些永遠都不會經歷的事。還有一種情況,當我們 cannot find the right word 去表達自己的感受時,文學,尤其是詩,就能充當描述的功用。」
從文學中辨認自己的位置和情感,不獨是同志的境況,香港每逢有大型抗爭運動,《雙城記》的名句、顧城的詩等,都是熱門的示威標語。我們與文學的距離一直很近。「其實我覺得 2014 年的一代社運參與者很適合看北島。當你看著周融,『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當你看著陳健民、戴耀廷,『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只是還未有人死,可能下一步就是『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然後,當你萬念俱灰的時候,是否真的可以大喊『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呢?」
「當我在運動的過程中再去感受這一首詩,箇中的痛楚其實⋯⋯」他沉默了一會,「那些文學家早已替你好好的總結成句子了。」

愈投入社運 愈遠離文學
話題無可避免地回到正值沸騰的社會運動中。岑子杰坦言,文學閱讀於他來說非常消耗時間,而且需要集中精神;現在香港每天都有新形勢,每天都要消化新的資訊,他身為民陣召集人,追看新聞和回覆短訊已經花了大部分時間:「當你真的有時間坐下來,只會想抽煙和放空,而不是看書。」
當然,文學世界中有過不少描寫專政社會的反烏托邦作品,《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我們》,箇中情節常常被人引用來比照現實裡的政治體制。不過,文學畢竟是文學,我們已經知道,現實可以比文學更荒謬。「現在把一些事件或事物意象化、抽象化的功力是很強的,例如『yellow object』,甚至把一個人物化了。我覺得這都能激發人們的靈感,可惜沒有時間可以走進去。」岑子杰說,「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理解當下正在發生甚麼事,工作也是回應相關問題。當我很認真地回應這些問題時,我便離文學愈來愈遠。」
他又以李清照的〈聲聲慢〉為例,詩中描寫的正是李氏的生活片刻,雨水打在梧桐樹上的聲音,觸動了詩人的情緒:「文學應該是這樣一回事。但在香港,我沒有傷春悲秋的時間,最後就只有政治上的沉重。」
「希望可以寫出一篇留在歷史上的演講辭。」
岑子杰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身份——他是一個寫詩的人。少年時曾經在文學比賽得獎,偶然碰上心情沉重得想拋開一切的時候,就會寫詩:「對上一次已經是今年四、五月的時候了。」不過,訪問裡他不時提起「覺得自己寫的不是詩」的想法。
「現在最常寫的發言稿,絕對是文學!」岑子杰這時的語氣非常用力,「我真的敢說,我寫發言稿的時候是用一種文學的心態去寫。」他形容,文學是創造一個途徑讓讀者身歷其境,感受作者的情緒,然後帶領讀者找到自己的感受。「我的語彙比其他從政者豐富,他們習慣說『遺憾』、『憤怒』、『譴責』,我會說『警方嘅邏輯,係好難畀我用我嘅智商去跟從到佢嘅思維』。而且我會有很多情感的描述,其中一次是 6 月 13 日的記招,聽畢後就會知道這是一種文學的表達方式⋯⋯」
這時,岑子杰突然發言人「上身」,重新唸一次記者問到他會否跟 6 月 9 日晚衝擊的示威者割蓆時的回應:「現在政府告訴他們,就算你再努力,有一百萬人出來,政府都不予理會。他們還能做些甚麼?他們的失落,不是我所能體會的。在這份龐大的失落當中,他們把自己的感受化成激烈的行動,我覺得,是否認同都好,不能不被理解。我只能感受當中的傷痛⋯⋯」
唸畢後,他又回到輕鬆的語調,笑言:「看似是一個即興的回應,其實我是寫稿的。」
雖說是創作,但這篇發言稿並非沒有根據的虛構。6 月 9 日當晚他在添美道看著警方清場,想阻止警方但甚麼都做不了;後來跟一些示威者聊天,了解他們的感受和想法,最後匯集成發言的內容。「發言稿特別的地方是,我不只是描寫自己的情感,而是一個共同的感受。」外國把政治人物的發言稿視為文學,港人熟知的「I have a dream」,本來也是馬丁路德金的演講辭,「最近我最常看的是丘吉爾的演講,在這個時勢裡非常舒壓。當看到最後一句——『We will never surrender』——會不知哪來的充滿著動力。」
的確,社會運動總是由各種不同的情緒交纖而成,鏡頭下政治人物的一字一句,隨時會成為鼓勵群眾繼續前行的力量。岑子杰愛文學如愛酒,自是非常明白如何透過言語使聽眾迷醉;有時,甚至連自己都沉醉其中。「希望有生之年,我可以寫出一篇留在歷史上的演講辭。」他最後說。
*岑子杰已報名參選 2019 年區議會選舉沙田「瀝源」選區(R02),另一報名人士為黃宇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