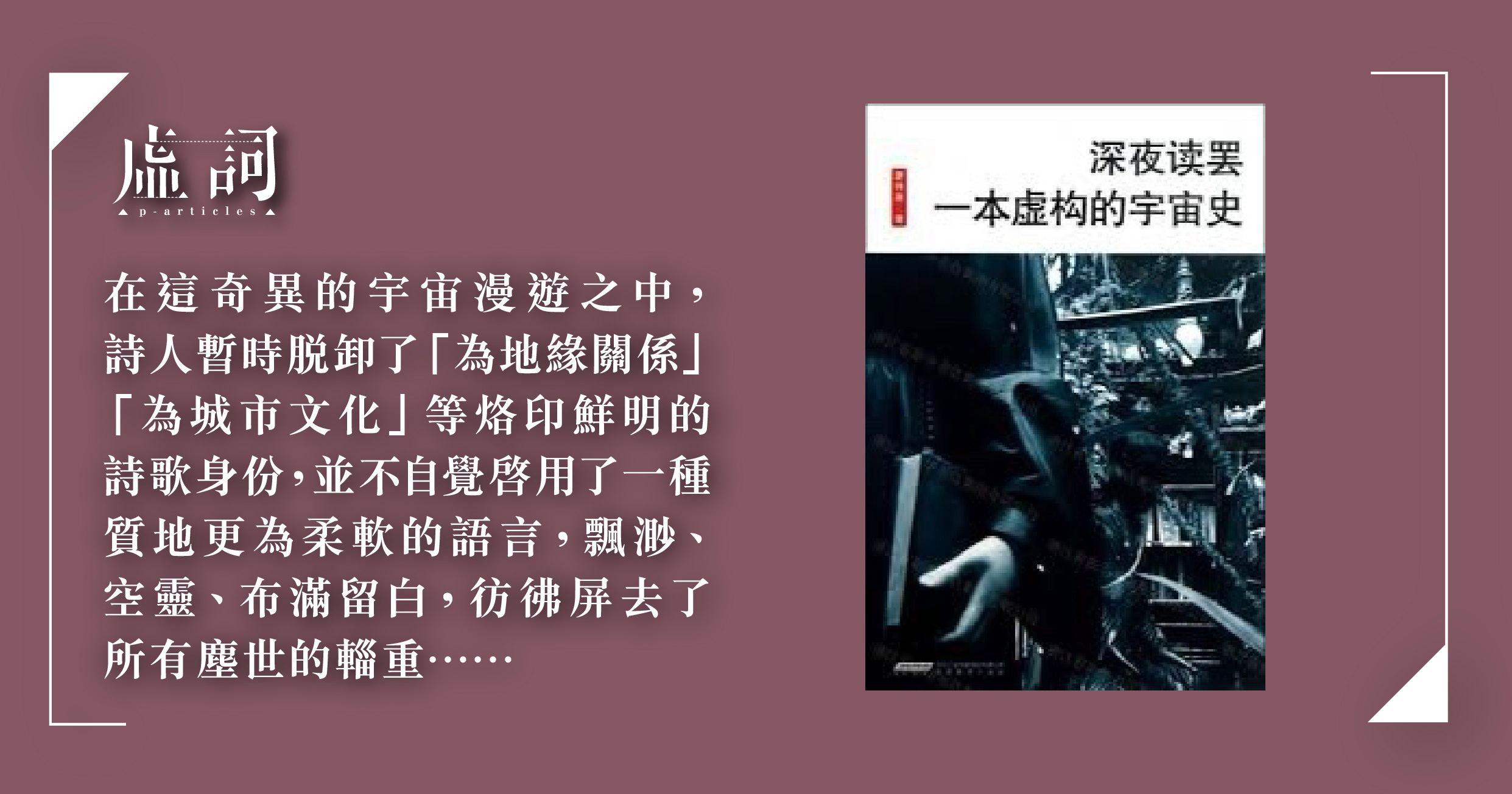口述如何「真實」?——讀何兆武《上學記》與《上班記》
書評 | by 梁世韜 | 2023-01-13
梁世韜讀何兆武的《上學記》與《上班記》,認為這兩本書被稱為最不可或缺的知識份子記錄也絕不為過,即使歷盡苦難,何兆武仍在回溯歷史,直面荒誕,誠實以對,探問在現實政治環境下不宜提出但至關重要的問題,有如耳提面命,警醒我們要免於虛無,免於放棄求真。 (閱讀更多)
《參差杪》作者被忽略的面向
風緣嘗試用一個比較不傳統的方法切入,談張婉雯的散文集《參差杪》,認為文章調子的幽暗反映作者世界觀的灰霾,但作者的幽默不是嬉笑而是對世界真實的深刻確切認識中找到其荒謬詼諧之處,讓人放心讀下去亦會讀到會心微笑。 (閱讀更多)
評《蒙面騎士》:拿起槍是為了放下槍的革命
書評 | by Louis @ Gunslinger 不曾遠去的硝煙 | 2022-12-23
哪怕冷戰以降的群眾運動大多以失敗告終,但是受壓迫者的境況和這些男男女女因不公而生的怒火終究是不會消散的,他們的怒火必將會展現出來,永不消滅,《蒙面騎士》一書正是訴說這個故事,戴錦華先生對薩帕塔運動精神的推崇,對女性主義的渴望和高呼「受夠了就是受夠了」的筆觸,更是教人動容。 (閱讀更多)
示我明鑑:《典型夙昔—前修緬思錄初集》讀後感
書評 | by 陳躬芳 | 2022-12-18
《典型夙昔—前修緬思錄》共分八個專輯,收錄了孔德成先生、王叔磐教授、吳匡教授、李傑教授、黃兆傑教授、李勉教授、陳捷先教授和石立善教授(等八位已故學人的相關事蹟,包括回憶錄、口述歷史、雜談、隨筆、札記等體例。這些的追憶錄或以自述或他人敘述的方式進行書寫,窺見一代學者對家國社會、治學教學、待人處世及人格修養等方面,呈現出他們一代的傳統知識份子,雖歷經近世的顛沛流離,仍保留著他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的氣魄。無論在香港、台灣、新加坡以及海外各地等始終對根屬的地方有一份安身立命之心,以真實的生命歷程印證近現代中國的種種變革及苦難。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