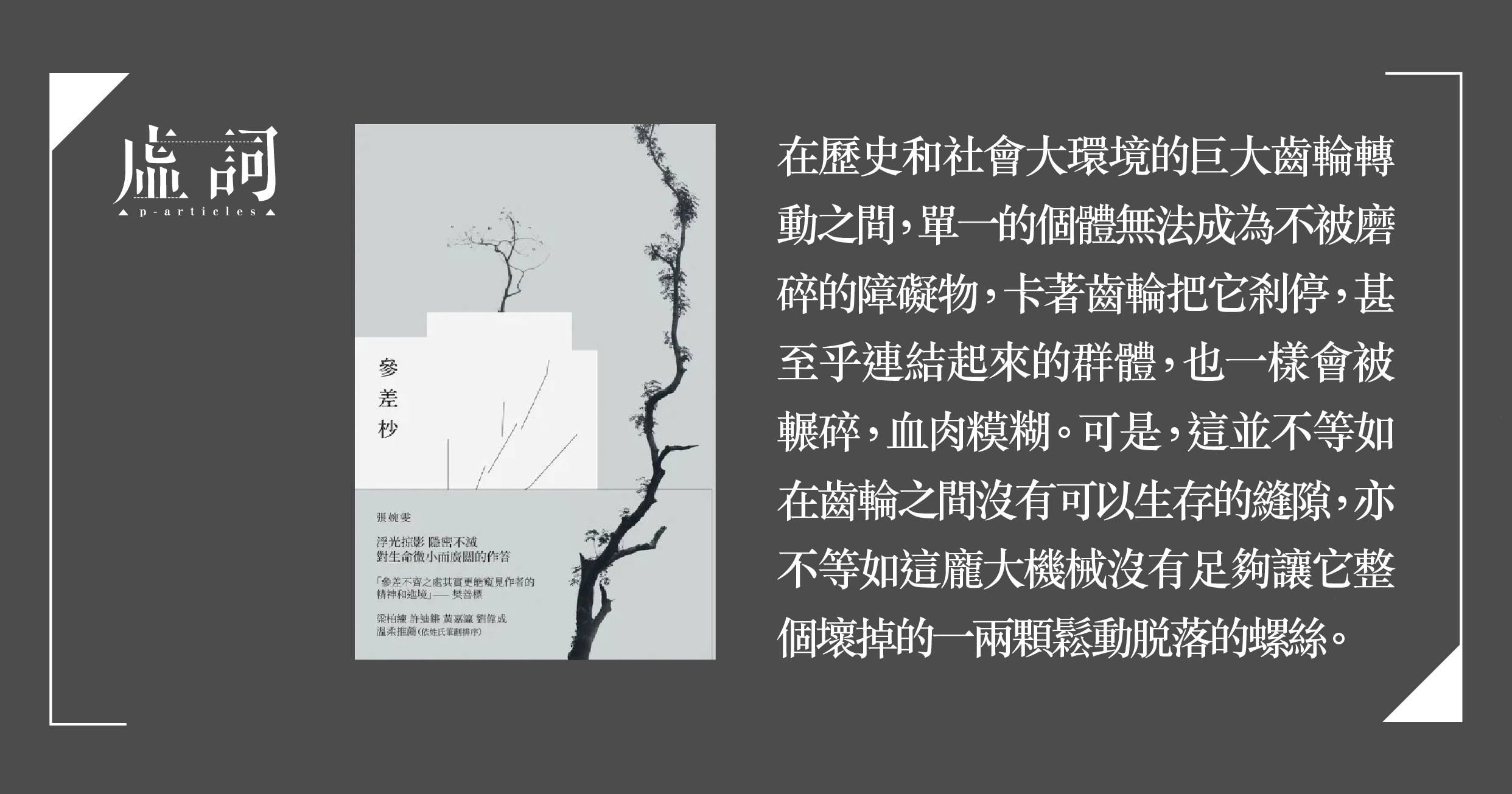杪,樹枝之末端。樹下抬頭看天,會見到這些參差不齊的幼弱枝葉在編織天空的圖案,又恍如頂著頃將倒塌的天空。如遇疾風暴雨,樹杪能屈能伸,狂亂的舞姿或許讓部分已經走過磨人歲月的殘枝脫飛,但那些新枝嫩芽,卻往往在風雨過後英姿煥發。張婉雯的隨筆集《參差杪》,就是有這種溫婉和頑強,一如作者本人。 (閱讀更多)
「他」(不)和XX一起吃早餐 ── 讀紀大偉〈早餐〉
紀大偉〈早餐〉榮獲第二十一屆聯合報文學獎極短篇小說獎首獎,內容不難理解,丈夫「他」、妻子和兒子,三人家庭,妻子憂鬱及患有神經衰弱,兒子還在學;這位丈夫晚上不回家而在情人家過夜,但第二天早上必定回家做早餐給妻兒吃。我們很容易便會把這篇小說當作是個三角戀和外遇的故事,但細緻地閱讀,便會發現這篇極短篇小說,細節是多麼的深藏不露,並指向小說的核心。 (閱讀更多)
【2022諾貝爾文學獎】書寫是死與生的創造──安妮.艾諾《Happening》
安妮.艾諾(Annie Ernaux)大熱當選,成為今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黃柏熹細讀其半自傳小說《Happening》(L’événement,中譯《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形容小說是以「敘述」(narrative)為目的,讓記憶和回憶的過程──包括所有遲疑和內心掙扎──都得以被赤裸呈現的書寫。赤裸的意思是,它總是分心和分裂的,這邊廂以冷靜的口吻敘述往事,那邊廂在剖析回憶之於自己的意義和其不可能性,突然停頓又重新開始。 (閱讀更多)
【無形.老派街市之必要】不知曉你的床邊是否溫暖──略談孫維民《床邊故事》
書評 | by 崔舜華 | 2022-09-20
從小,我們的床頭堆疊著各式各樣的故事,那些古老的童話、神話與傳說,一度讓我們感到離奇翩綣,心神搖蕩。後來,當我們學會了一個人睡,或是一個人醒,手機與被褥俱冰冷而孤獨,再沒有一個簡單的故事能夠撫慰我們的睡眠與不眠,能夠從語言中遞出能量,讓我們一覺天明。孫維民的新詩集《床邊故事》,包含著這樣一個簡潔的願望:願所有長大後的我們,能從詩的話語中,溫暖我們的床,以及夢。至於詩要怎麼說故事?詩人不做典型的敘事示範,而是讓出空間,容納需要故事的人,在詩意的微光下,暖一張床。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