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詞語以任何方式落下吧——談《帕特森》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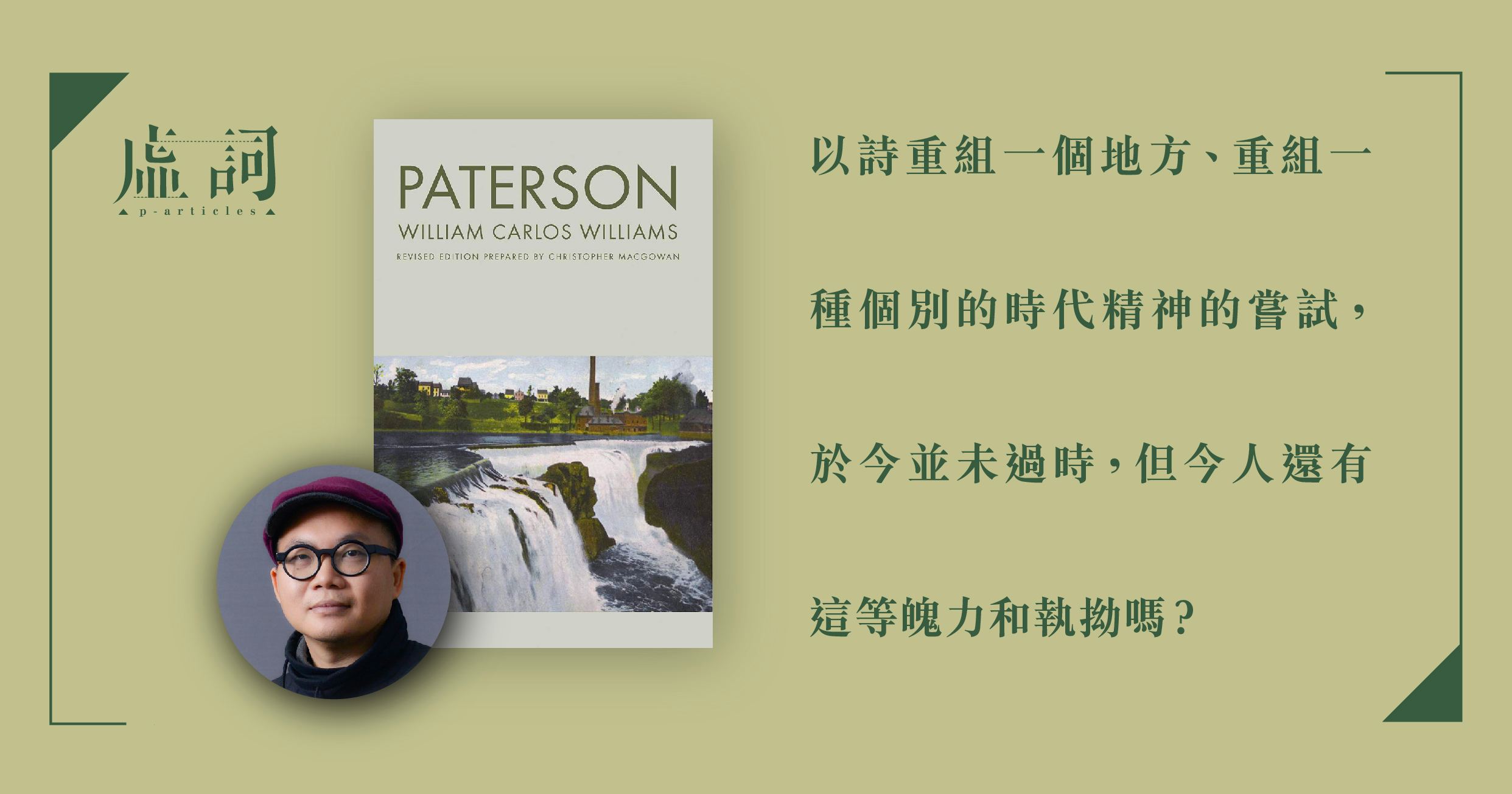
292142511_1740013976331904_4761285818758239055_n.jpg
威廉斯·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帕特森》(Paterson)是美國二十世紀本土詩歌最重要的長詩,也被視為後現代詩的濫觴。七零年代曾經有翱翱(張錯)的繁體中譯本,可惜已絕版罕見;最近終於由上海的雅眾文化出版了第一本簡體中文全譯本,譯者是青年詩人連晗生。
閱讀足本《帕特森》跟以前只選讀其中一些短章斷片很不一樣,非常的氣勢磅礡,一如詩中常常出現的瀑布。尤其是進入第三卷,第三卷寫得最好,但我們一般在一些選本裡邊能看到的都是第一卷,還有之前的一些評論比如哈羅德·布魯姆的《詩人與詩歌》裡面,也有談《帕特森》,但他只談到第一卷。
但慢慢讀下去,你才發現《帕特森》的重要性其實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放在整個當代美國詩歌的脈絡裡看。因為美國詩人會用長詩來奠定自己的位置,上世紀的詩人都很著重這一點,但長詩裡還有一個明爭暗鬥——所謂的開放的、非學院的詩風,跟學院詩之間的競爭。
像龐德是介乎於兩者之間的,艾略特那當然是學院風的,一般都會這樣劃分。但像威廉斯,他那些短詩都表明他是一個極端者不是折衷者,他要強調日常本土等等這些很美國色彩、美國特質的詩。所以當他開始寫這首長詩的時候,很明顯他想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來挑戰這個快被學院詩所壟斷的長詩,而且挑戰的非常成功。
很多地方你能看出來他有對比如說對艾略特的挑戰,有一些地方是跟《荒原》、《四個四重奏》某些主題的對寫,另外當然也有對龐德的延續,甚至直接加入了很多龐德當時還在精神病院裡面跟他的一些對話,還有他們私交的一些逸事混雜進詩裡。但其實他主要繼承的還是惠特曼,因為如果他要去繼承龐德,就很難超越龐德,但他如果他去繼承惠特曼的話,他就跟龐德站在同一條線上競爭了。
所以《帕特森》的重要性之大,在於龐德的《詩章》無以為繼的時候,他上來了。《帕特森》填補了二戰後一個非常重要的長詩的空虛的位置。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他把長詩的努力徹底地本土化——把它迫降下來。詩裡邊最重要意象當然就是「瀑布」的意象,「瀑布」是一個向下的意象,向下傾泄。這樣一個向下的意象,竟然能夠抗衡之前所有的史詩(除了《失樂園》)都強調的「上升」的意象,從《神曲》一直持續到《比薩詩章》(裡面都反復強調像「泰山」、「飛鳥」這種象徵意象)。但威廉斯用一個向下意象,把它徹底拉到了地上。
《帕特森》的形式也是四散、下行如瀑布的,這種形式我們並不陌生,如果看過龐德《詩章》的話,會覺得龐德已經運用得非常成熟了。這種形式類似「階梯詩」,但實際上他的階梯又跟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不一樣,馬雅可夫斯基的詩是很整齊的,真的就是像階梯一級級走下來。但威廉斯的階梯是分散的,四面八方的彌漫,把節奏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強調出來。如果我們用音樂來比較的話,馬雅可夫斯基的音樂呢,像是進行曲一樣,但像從龐德到威廉斯那個過渡,其實就是跟美國的本土音樂爵士樂一樣的,自由即興非常強大。
我曾經非常推崇查爾斯·奧爾森(Charles Olson),他是受威廉斯影響的黑山派的首席詩人,他的詩論叫做「放射詩論」。「放射詩論」其實就是對威廉斯詩風的一種延伸。「放射詩論」形象一點說,就是把詩包含的東西發散開來,像核輻射一樣的發散,然後是一個核聚變的過程,所有的力量通過這種像散漫的、詩歌世界裡散亂的原子,慢慢彙聚,最後產生聚變,產生強力的爆破效果。
所以如果看奧爾森的詩,還有《帕特森》第三章的時候,就能看到這種爆發的力量。第三章像是一個煉獄篇,裡面動用了洪水、烈火的意象,突然有幾段把它之前那種散漫的階梯詩突然收束,整首詩力度一下子加重。它收束成很整齊的幾節,一方面把二戰之後的美國所要應對的壓力呈現出來了,另一方面,這是對《四個四重奏》裡邊「燃燒的諾頓」的一種呼應。
可能誰都沒有料到威廉斯能夠做到這種爆發力,因為他的短詩很清新,甚至用現在的說法是帶有一點禪意,這種禪意充滿了斷舍離、極簡主義,沒想到它可以凝聚成一個這麼大的爆發力。
當然這跟它形式上的自由即興有關,越自由即興,言辭互相呼應起來、碰撞起來的時候,最後得到的結果反而更加讓人意外。比從一開始就按照比如說抑揚格、英雄體這樣格律去推進,其實得到的是一種更新的節奏、更新的力量。這種力量如果回到“放射詩論”來說,就是說從原子彈在現實世界爆發開始,我們的詩歌就開始要去尋找一種新的美、新的語調、新的說話方式。
在美國,威廉斯他們這種小鎮敘事、小鎮認同裡邊也包含著: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到當代的這個過程中我們都在呼喚的——我們要認識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我們要認識生活的地方。這比你認識一個神話,比認識《杜伊諾哀歌》裡那個世界可能更重要,這是美國當代詩很強調的一點。
這個形式的變化多端,即使在之前我看繁體豎排張錯的譯本,也還是能看出來。這種變化的形式能夠衝破中文對他的限制,即使我們都說詩很難譯。我在看《帕特森》英文版的時候,最有意思的發現就是它搖蕩在兩種文字極端之間,有的段落是非常簡單的口語,但有時候又突然推進到一些很晦澀、很龐德的方式,而且是不分青紅皂白地運用典故,會拼貼各種不起眼的典故。
這種種令這首詩的世界變得非常紛繁,難以駕馭,其實就非常像當代藝術所呈現的面貌。它可以讓你在裡邊去挖掘出無數分叉的岔路,而不是說只有一條路讓你去跟著走,它不是要成為經典的那種文學作品,相反它是有很多種解釋的出口的文學作品。
我想起我寫過的一小篇關於電影《帕特森》的影評。寫那篇影評的時候,我還沒有看過《帕特森》這部長詩的全貌,只是看了一些片段。當時很多影評都著重在:這是拍一個巴士司機去寫詩,他的詩是放在飯盒裡面的之類。當然這些都特別像威廉斯的短詩裡邊的場景,他的短詩很多是廚房意象:電冰箱上貼的便條、我吃了你的早餐等等這些東西。所以當時我跟大家一樣只是意識到:導演賈木許把這種文字上的東西移植到一個具體的人身上,這種巧思就像賈木許很多電影一樣。
但是現在讀完這篇長詩以後,才發現原來還有更深度的兩個地方在裡面。首先很重要的一個是這部電影的主角,他的名字也叫帕特森。這不是一個噱頭,而是導演真是深刻地領會了《帕特森》這首長詩尤其是第一章,才做出來的一個決定。《帕特森》的第一章就是把帕特森整個地區進行一個人格化,甚至還用了古希腊神話裡的巨人族意象作為潛文本。
威廉斯要做的是,要讓美國的諸神如何著地,如何成立。美國是一個沒有史詩沒有神話的國度,在所謂的主流歐洲文學的角度去看的話,會覺得美國是這樣的一個地方——但威廉斯把帕特森人格化,甚至神格化之後,它就逆襲了。
在電影裡面呢,這個人格化然後神格化的過程,就變得更加具體。《帕特森》最後有一個轉折是,司機帕特森跟他妻子去看電影的時候,他的小狗把他那本寫詩的筆記本撕成粉碎——我當時的影評是這樣說的:
「當他的鬥牛犬把這本秘密筆記本撕成粉碎,他們傷心地收拾殘渣的時候,我意識到一個詩人將浴火重生。就是過去的你被撕碎之後,你才可能成為一個好詩人,你才獲得了成為好詩人的機會……其實無須電影結尾那個神祇一般的日本詩人出來遞給佩特森一本新的筆記本,這本新的筆記本早已藏在他開的公車的每個座位上,他妻子做的每個成功或者不成功的蛋糕和甘藍派裡,在酒吧和洗衣店裡。而佩特森要做的,是把它們解放出來,變成新的江河湖海。」
其實在寫那篇文章的時候我完全預料不到,我今天在《帕特森》第三卷裡看到了類似的句子——「你會飛過什麼空氣 / 跨越大陸 / 讓詞語以任何方式落下吧 / 他們可以歪斜地擊打岸。」接著威廉斯繼續去展示他對一種未來的詩的想像。他說:「果肉是否需要進一步浸漬?」——他用了一個以前經常出現在他短詩裡的意象。你經常可以看到他寫那個冰箱裡的李子,「它太好吃,那麼甜,那麼冰」,還有他寫一個貧窮的老太婆走過街角,她在吃著一個李子:
「味道真好,對於她
味道真好,它們吃起來
味道真好」
在這裡有一個暗示,這些詩句是呼應的,果肉需要進一步浸漬,是指語言是怎樣進一步發酵、怎樣變成一種新的語言的過程。接著他說,語言將不得不被重置,就是推反了那個廢墟一般的歐美文明。在二戰之後,語言怎樣重建起來,其實這也是龐德和策蘭所關心的東西。威廉斯提出了自己的方式,最後一段,他再拉到了瀑布上面去講述這個願景:「而過去在上面 / 未來在下方 / 現在傾瀉而下 / 公民,現在的公民 / 一種言辭 / 必然是我唯一關切之物」。
他說語言像瀑布般瀉入不可見之物,超越在它之中,瀑布是可見的部分。這裡他一方面是向未來推進,但同時他又一次回溯,回溯到意象主義詩歌的出發點,也是威廉斯一直很強調的,龐德也很強調的,就是:我們不要去書寫理念,我們要用最具體可見的事物去言說。所以在第三卷裡面,他的語言觀,他的詩歌觀來了一個循環。在電影裡面,我也意外地看到了這種打碎重建的可能性。
受這種語言觀影響的,除了剛才提到的黑山派詩人奧爾森,還有黑山派的其他幾個詩人,如羅伯特·克里利(Robert Creeley),也是有跳躍的節奏和對爵士樂的呼應在裡面。但這次讀《帕特森》我還有一個意外的發現,其實他對垮掉派詩人的影響,並沒有體現在艾倫·金斯堡上面。艾倫·金斯堡雖然也是在帕特森出生的,但是艾倫·金斯堡的個性跟他太不一樣了。金斯堡是一個相對浮華一些的詩人,但威廉斯其實有非常刻苦和樸素的一面,而這一面我反而是意外地在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身上看到了。
連接點是威廉斯在《帕特森》裡邊大量談論聯邦的稅務,談論經濟情況——表面上跟龐德很像,龐德很喜歡談論經濟,但龐德的著重點是高利貸,高屋建瓴地打擊猶太人帶來的經濟危機等等這些理論東西。《帕特森》裡的經濟就非常龜毛、非常細致到令人難受的程度,尤其他談論稅收的時候。但是這一切東西,我又曾經在加里·斯奈德的詩裡面看到。
斯奈德寫過好幾首這樣的詩,比如說《深夜與州長談未來預算》,還有計較怎樣去買一輛拖拉機可以省錢,他寫道「反正大錢亂花,小錢精打細算」。這些非常細膩的東西,是美國的非常務實的精神所帶出來的。從私人的角度來說,我們可以看到,斯奈德跟他的相似之處通俗一點說就是接地氣。這個接地氣不是說用一些口語寫一些瑣碎的生活就可以,而是真真正正可以著手於這些好像是非詩意的東西——這樣他的詩意完全是開拓性的。
最後,斯奈德和威廉斯都體現出他們對印第安文化的關注,而這種關注又不是一種異國情調式的關注,而是實實在在、真的是跟印第安人歷史上的被侵害,以及他們現在在當代美國的社會結構裡的尷尬位置這些東西相關,《帕特森》都有呈現出來。這點非常難得,是一個非常質樸的、願意去觸及和處理問題的詩人才能動手去做的,原來斯奈德有跟他呼應的地方。
這是我讀《帕特森》很意外的發現,頗令人欣慰。但這也是我們當代華語詩普遍缺乏的,這又讓人焦急。以詩重組一個地方、重組一種個別的時代精神的嘗試,於今並未過時,但今人還有這等魄力和執拗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