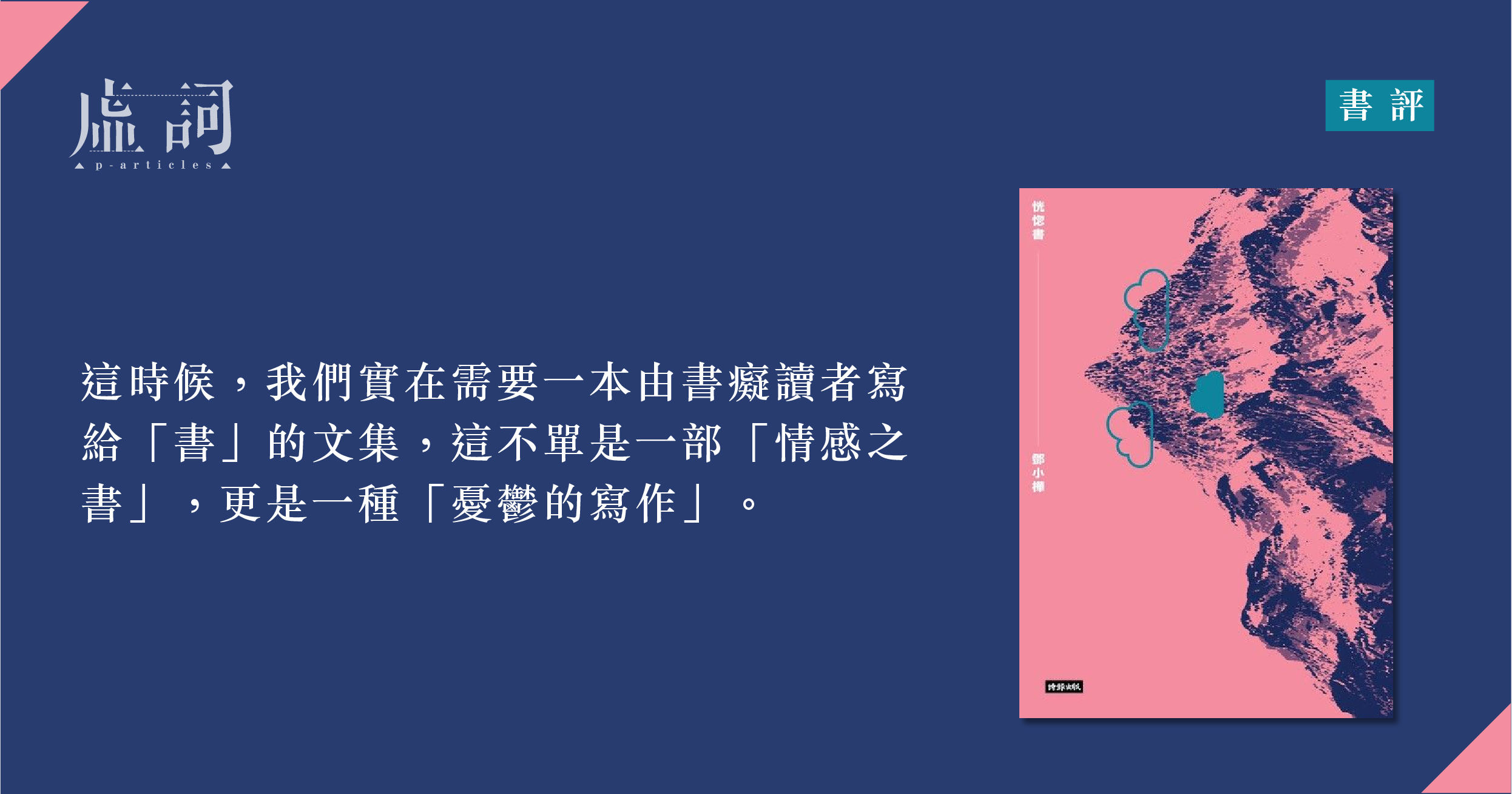關於書的散文或情書——評鄧小樺《恍惚書》
今年盛夏,小樺新作《恍惚書》在台灣時報出版,封面是鮮豔的鮭紅,加上海軍藍的腰封,很是搶眼,也令人忍不住翻開看一看。事情前我沒有刻意去看介紹,根據我對小樺的瞭解,已知道這是一本散文集,台灣作家胡晴舫在推薦語寫道:這是一本「寫給『書』的情書」。印象中,小樺出版上一本散本集《若無其事》,已是多年前的事了,那本散文集的內容還算比較個人化,有穿插於學術和生活之間的思考,有關於現實與想像之間的界限,有成長的回憶,也有一些比較實驗性的散文,語調有時帶有書院氣,有時帶有未經琢磨的少年氣。《恍惚書》則不同,書中所議所談的,全都與書有關,語調也變得沉穩、持重,書中不乏時評或報告式的文章,內容為書展、書業軼聞、略談新舊書藉等,實用性很強,敍事較《若無其事》少。
所以就一本談書的文集而言,我會擔心讀者有未必太大反應,原因不外乎是因為內容有業務或技術成份,或者看來不涉日常的物事。有時我們會看見國內或台灣有人翻譯或撰寫一些關於書店的文集,通常賣點都在於借書店這種場景說故事,不管是自己的抑或他人的故事,總之書店就是一個會產生奇人奇事的空間。我們不應該太執迷於這份迷思,反而應該認真思考一下:看書、賣書,以及種種關於書籍的活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有認識、思考書的產生,我們才能明白一本書,以及其中盛載的文字,為甚麼會變成我們閱讀時的模樣。這就是我覺得為何《恍惚書》值得一讀的理由了。
說來我們之所以喜歡看書,除了宗教經典或涉及實質需要的原因外,就是因為它記載了現實生活的種種,或開拓我們的想像力。想像力不一定要天馬行空,據說近幾年來在香港公共圖書館以讀者借閱量所作的統計排行榜中,旅遊書竟然高踞榜首。我相信,不少香港讀者對遊歷外國的憧憬應比準備旅遊的實質需要更大。這反映出,雖然大部份旅遊書不是文學作品,但在為香港讀者提供心靈慰藉這方面,與文學的作用是差不多的。
香港人經常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人不看書,在香港做出版無法養家,這已經成為一種陳腔濫調了,但還是有人做出版。他們以為,既然這只是片藍海市場,那麼我們只要低端一點,做些內容通俗的、印刷成本低的書籍,薄利多銷,大概也不會虧本吧!殊不知這些以量產、通俗是尚的圖書,亦一樣變成廢紙,加上這行頭本身就很微利,即使有官方資助的大型機構,亦不得不面對高昂的租金、工資,卻苦於微薄的收益,而在生存綫上掙扎。香港書展已久被詬病為一散貨場,然而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香港人對閱讀的需要極其殷切,在日常生活裡甚至離不開書本。
很多時候,我們總是把書本與生活割裂開來,我們聽慣一種論調,說書本裡都是理論,而理論來自日常生活的實踐,而日常生活瞬息萬變,當生活知識被寫成書,知識會脫離變化多端的生活,成為化石。這種說法不能被否定,然而生活也會淘汰一些同樣具價值,卻隨歲月被遺忘的知識。書本的作用,正正就在於保留這份貴重的財產。
不過,有一種人,他們和一般讀者不同,一般讀者只求從書本獲得了知識,或者享受過了閱讀小說、文集的過程,得魚忘筌過後,就把書本拋開了,他們卻把書本當成收藏般小心保存。這種姑名為「書癡」的讀者,與有錢人收藏古本名書以突顯品味是不同的,他們對書本的內容與物質同樣著狂。在香港這裡來說,小樺算是這樣一種讀者,她在自己的文章裡,常訴說自己與一些書籍的緣份,那不僅是對書本作者的見解五體投地,而是每本她所珍重的書與「書主」都曾經歷盡滄桑,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這恐怕是對馬克思說的「商品拜物教」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表現了。這些經驗甚至還包括把一本書買兩次。小樺在書中坦言,買書太多的人,其中一個沮喪是,發現家中有重複的書,這恐怕已是很多書癡的共同經歷了。
書癡與書交往,亦與書店交往,因為書癡與書的關係不止這主體與客體的關係,還有兩者發生「關係」的時空:窗邊一扇陽光,照灑在暗角的書架上,讀者緩緩搜索書脊上若隱若現的書名,在剎那間的驚訝下,書緣就這樣形成,正如蘇格拉底會說的,哲學(愛智)形成於驚異。這瞬間的驚異對於我們這些追逐生活的香港中青年來說,確實就是一種無上的奢侈。然而香港書業之所以艱難,除了一直「文化沙漠化」的經濟因素外,政治箝制恐怕是更重大的原因。自傘運以來,涉及相關題材的書都被封殺,銅鑼灣書店事件,還有以賣政情書作招徠的書店被警告一事,更加說明了,當權者一定會全力封殺這些販賣揭祕式書籍的書業中人。
當然,有人被抓,就有人轉圈子,透過賣食品、手作工藝品來維持書店營業額,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我們都認識的台灣誠品集團,可是誠品也是大集團,小店根本無法仿傚。小樺曾經在誠品工作,她提及「誠品」這種做法說:「書店求存變化,無可厚非,只是心痛……」寥寥數語,恐怕心情遠遠複雜得多。但如果賣書不賺錢的話,那誠品為甚麼在香港仍要賣書呢?大家會說,這是誠品為人所熟悉的一個招牌,這樣說是對的,但不啻於以自己的大招牌,壓迫那些艱苦地只賣書的本地小書店,而在台灣那邊廂,有一位退休董事長以「社會企業」形式開設了「益品書店」,以免費飲料,廿四小時營業作招徠,結果亦招來同行書業的批評。這帶來一個「賺錢不賣書」抑或「賣書不賺書」的問題,在小樺看來,如此提供免費的東西,正是大書店以小書店承擔代價的表現。而在香港,我們所見的書業操作,恐怕是擴展到意識形態方面。我們正面對主權(如聯合書刊物流集團)對個體的箝制,也面對主權所操控的大集團對小店的壓迫。書本,既是生活中的避難所,象牙塔,也是政治打壓和商業壟斷的場所。
小樺也寫道,台灣近年來興起獨立書店這一名堂,標榜不走連鎖式集團經營路線,但接受政府補助:然而在香港,從來只有樓上書店,這當然是因為租金問題,但也是與香港政府素來箝制書刊言論,書店與建制保持一定距離有關。這又關係到存亡與自由的問題,如果有一天,香港政府推出樓上書店資助計劃,只要樓上書店經營艱困,都可以向政府申請資助。那麼樓上書店是否應該接受資助,或千方百計符合政府的門檻,例如賣更多銷暢書,就像當年商場小店舖必須接受領匯的門檻一樣嗎?但如果不接受資助,書店營生會越來越艱難,而且親建制人士可以製作杯葛該書店的文宣。這種兩難困境會否比銅鑼灣書店事件更恐怖?
《恍惚書》是一部評述書業和自身買書、讀書及藏書經歷的文集,在評述書業現象、軼聞的時候,作者似一種旁觀者的客觀角度來評述,談及自身經歷的時候,就顯露她所喜愛的文學作品和理論書籍,不過語氣仍是從容的。有時候,我們都會忽略一個問題:散文語調的定位應該如何?按理說,它是作者最放鬆,最暢所欲言的時刻,所以應該用最個人的語言,但又不用像詩歌一樣去修飾或推敲:但散文又是寫大眾讀者的,必須追求明晰的表述和在地的討論。過去也有其他作家談論書店或買書的經驗,陳智德的《地文誌》裡面有一半是關於他留連二樓書店的經驗,然而在《地文誌》其他講述香港地方的篇幅中,作者都會援引自己的詩作,以表現他在地區生活經驗中的感性體會,在關於書店的篇幅中,卻較少援引詩作(或者陳智德很少以這類題材入詩),而《恍惚書》也是以散文正正經經地討論書和書店的。如果胡晴舫是真的話,那麼情書應該含有不少個人化的語言,就像詩一樣才是的,可是《恍惚書》卻一點也不像情書。
現象學家梅洛—龐蒂晚年寫了一本著作,名為《世界的散文》,當中有一篇名為〈純粹語言的幻象〉,似乎是要戮破現象學創始人胡塞爾對「純粹語言」的執著,借討論「散文」提出他對語言的概念。而在德國那邊,海德格也探討語言,但以詩作為探討語言的對象,而不是散文。梅洛—龐蒂說,語言是以各種含義的符號串連一起的表達,平庸散文與報告一樣,屬於「被言說的語言」,而開創新語言的小說則屬於「言說著的語言」。話雖如此,我們表達的時候,也是在溝通和交流,而散文本身作為一種中介,一種交流手段,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這樣說似乎很吊詭,書是一種傳達知識、訊息、情感、想像力,甚至對語言實施再創造的中介,而散文本身也是一種討論問題的中介,關於書的散文,則無異討論一種中介的中介,正如為關於書的文集寫一篇書評或介紹,亦無異於討論「討論一種中介的中介」的中介。那麼為何必須以一部文集來說書呢?因為關於書的經驗並不純粹,它夾雜了學術知識、個人情感,也有商業行銷和心理分析。關於書店的經驗和體會,都離不開人與人的接觸,因為讀者不是躲在象牙塔內,而是要與店主溝通,也接觸形形色色的讀者,這樣,講述書店經驗的語言就不再純粹,而是豐富、駁雜。
目前我們生活在透過電子媒體傳達資訊的社會,印刷品的價值正在消亡,很難想像報童在大街上派發報紙的情景了,因為大家都用電子媒體接收或分享即時資訊。紙本書之所以並未消亡,是因為在把書本當成消費品和精神食糧的讀者大眾心裡,電子書仍未能完全取代紙本書的地位,我們仍然相信信紙本有某些「實在」的價值,即使只是手稿或油畫的影印本,也能予讀者一種「共在感」。我們也發現,讀者之間對於紙本書的討論,必會比他們對一篇推特短評或連登post的討論更持久,因為紙本的文字往往久經斟酌而成,更耐得住時間的考驗。
所以,如果我們說,紙頁的明亮度,和字行的間隔等因素,會成為今日我們堅持紙本書的一些理由的話,那是捨本逐末的。即使小樺在書中亦嘗斷言,書以後會變成屬於少數人之物,只屬於少數有錢人,而大部份普人則上網亂看資訊,無法避開廣告(這對大多年身無分文的讀書人來說,都是一個極有可能成真的噩夢):然而我們現在更經常碰到的現象是,紙本書很快就落入二手書店成為故紙堆,就像今日看過的報紙在明天已經沒有價值。所以書更應該著重內容的縱深。這時候,我們實在需要一本由書癡讀者寫給「書」的文集,這不單是一部「情感之書」,更是一種「憂鬱的寫作」。這是我對於《恍惚書》之所以被稱作「情書」的一種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