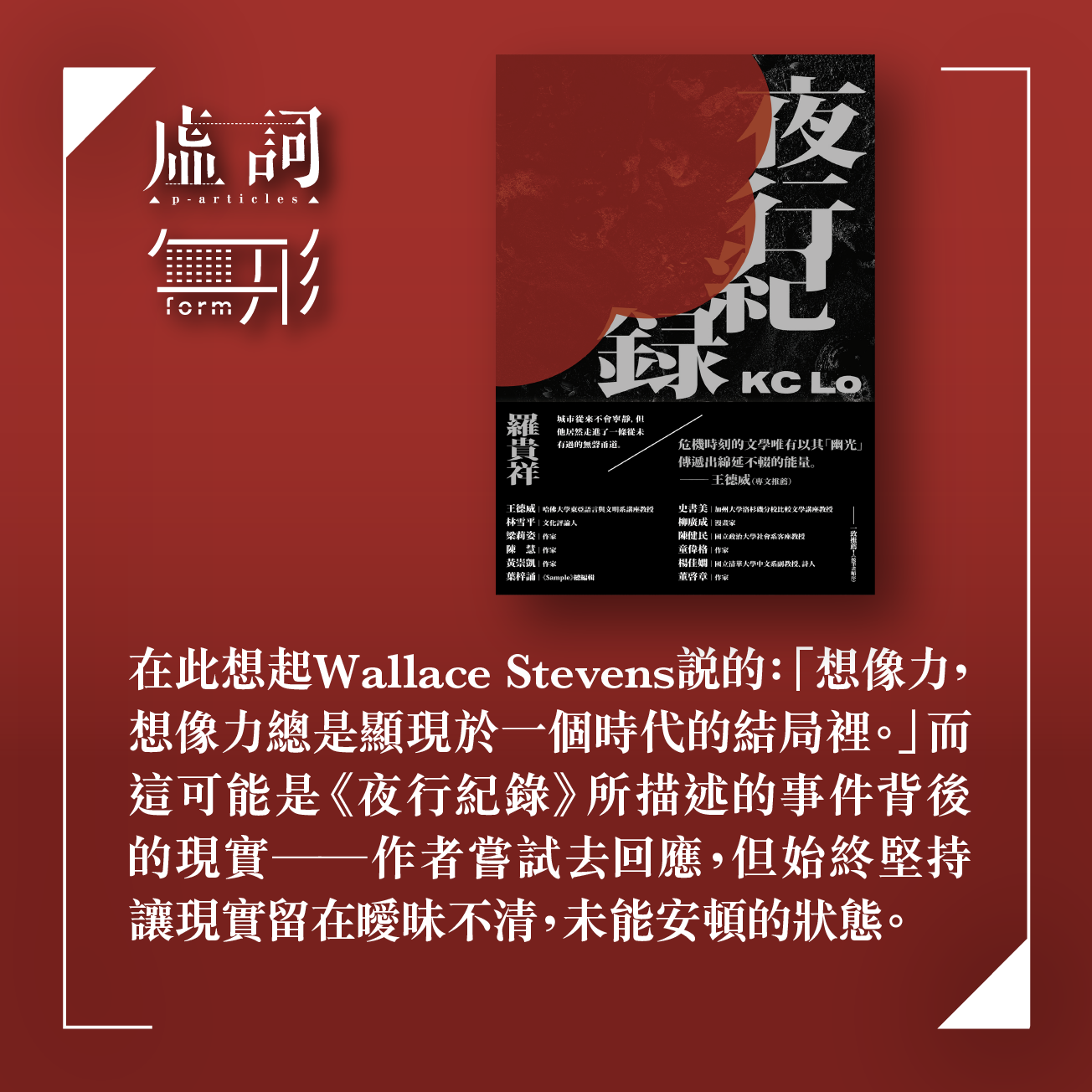【無形・沖繩.虛實之旅】結局的意義──讀羅貴祥的《夜行紀錄》
書評 | by Sabrina Yeung | 2023-08-31
Frank Kermode在《結局的意義》(The Sense of an End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Fiction)中說,一個平鋪直敘、結局明顯的故事似乎更像是神話,而不是小說或戲劇。在小說或戲劇裡,即使是一個結構極為簡單的故事,也有「突轉」這個元素,即行動的發展由一個方向突然轉向另一個方向,或由順境轉向逆境,或相反,由逆境轉向順境。「突轉」是一種能引出和諧的否定。和諧的意思是無論故事的開頭如何,中間又如何,結尾部分總是把之前那些衝突與不安都安頓好,未必是大團圓結局,但就各安其位。而否定是在故事中間部分,有某些事情破壞了我們各種天真的期待與常見的平衡狀態。當然,這種由「突轉」而來的破壞是為了讓我們找出某種藏在事件背後,更指向現實的東西。「突轉」越大膽,我們就覺得作品越尊重我們的現實感。Kermode的說法明顯受了亞里士多德《詩學》的影響,而我為甚麼會突然提起這個觀點呢?其實只是一場偶然,因為我在看羅貴祥先生的《夜行紀錄》時,同時也在看《結局的意義》這本書。可能因為這樣交錯的閱讀,令我加倍關注《夜行紀錄》那些作品的結局。不知道是強行附會還是以意創造,其中數篇作品的結局的確頗有意思,例如〈同舟〉、〈前行〉和〈夜行紀錄〉等,因為那個轉折──如果不能用上古希臘戲劇「突轉」這個術語的話,似乎都是發生在結局。然後我就想,如果轉折是在結局才出現,那它開啟了甚麼意義,呈現出怎樣的藏在事件背後的現實呢?
或者先簡單介紹羅貴祥先生及《夜行紀錄》這本書。KC Lo,即Prof. Lo,既是學者,也是作家。根據鄧小樺引述作者自己的說法,《夜行紀錄》「收錄由2014年至今的十二篇小說創作。第一輯六篇作品覆蓋的年代和範疇較廣,從古代的重塑到當下的虛擬,但都與種種現實產生對話及牽纏;而第二輯是對過去數年本地社會運動的一些思索與回應。也許作品看似各自成篇,在虛構與真實之中,卻有細線把重重複複的生活與生命勾結交織在一起。」的確,我覺得結局頗有意思的幾篇作品中,〈同舟〉是說一場突然而來的海難;〈前行〉是講一個早年涉水偷渡來香港,在香港落地生根四十年,年老時被逼遷的農戶的故事;〈夜行紀錄〉既寫主角的人生也寫新界農地復耕的故事。它們,以及很多結集內的其他作品,皆對應著香港過去十年不同的社會運動及新聞議題。不難想像,讀者可能會從社會議題或社會運動的角度去看這部結集;又或者引用結集裡林雪平的文章〈我的老師是一名海盜〉中的說法,從海洋文化理論的角度去分析這部作品。不過這些角度已被其他評論者提及,所以我也只能分享一些於錯置中得出來的讀後感受。而由於是感受,所以也就簡短而粗淺。
〈同舟〉基本上整篇都以沉穩的筆調去講述主角「他」不同階段的行船生活,每個部分都有一句提示句去表明船與他的關係,例如「船是他唯一的工具」,「船是他掌舵及管理的」、「船是他服務上層階級的工具」。船也是他表達如何看待女兒打扮中性的方法:「船到橋頭自然直……女兒的裝扮問題自自然然會好起來的。他清楚知道船身都是弧線形的,到了橋頭或碼頭,也不會因而變直。直與彎,只是視角的緣由。」不同類型的船是他事業不同發展階段的工具,行船造成了他與妻子感情疏離,但又造就了他與女兒的某種默契。可以說,在這篇故事裡,船不完全是他所聲稱的一個「內部掏空了的工具」,也是他與家人的關係的中介,以及他看待世界的方式。而在故事最後一段之前,所有事情都很淡,就像一艘船在海面上來回搖晃,一種沉下去的情緒。直到最後一段,在描述他開船帶遊客觀看中華白海豚後,船為他的生命及世界迎來一個巨大的轉折:「沒想過眼前的世界會突然崩塌,他被他忽然的無力感逮個正著,說不出話來,肢體又完全不能活動……一切不能飛躍又受制於地心吸力的物體、在空氣中震動著的叫聲,都正在迅速被捲入波浪的漩渦之中,在他面前淹沒。」他和在船上做替工的女兒沉沒了。
強大的不幸在最後一段才出現,這樣看起來有點像偵探小說那種解謎總是在晚餐之後的結構,即突然而來的轉折在結局才出現。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船是他觀照世界的中介,而不幸或死亡也是世界的一部分,那這個轉折算是高潮、結局,還是只是展現他的世界的一部分呢?即生命的起伏,包括快樂與不幸皆是船引導,就像作品中有一句:「自然要毀滅他,或要養育他,也不過出自偶然。」故此,轉折雖然出現在故事最後一段,就結構來說像是一個突厄的結局,但就人物整個生命而言,它是否只是生命與世界的一部分,無所謂結束與不結束,轉折不轉折呢?
〈前行〉和〈夜行紀錄〉的結局是另一種,兩篇作品都在短促的結局之前大篇幅地記錄了人物人生的歷程,讀者以為去到結局部分那些未能安頓的,經過時日和某些看起來像反思的文字後,總算可以安頓下來了吧。但兩篇作品卻在結局部分又再開啟一條未完之路──不是為故事留下一條懸疑的尾巴,而是好像所有東西又回到起點。〈前行〉第一句是「登岸那刻,一個念頭浮起:他的生辰還有三天半。」故事中的「他」在批鬥的年代,靠著幾個膠桶從內地游水偷渡來香港,他說是水引導了他。然後他一步一步在香港建立自己的生活,在粉嶺霸了地建屋、開荒、種植,最後以種富貴竹養活一家。四十年後,官府來到,指他霸佔公地,必須拆去不合法的閘門。這樣的情節很像雜誌中那些人訪會出現的耳熟能詳的新界故事。這位老人家想不遷不拆,與支援的年輕義工前往示威,而故事的最後一句說:「當一道水柱高速射過來時,他糊塗了。水,不知是不是又再一次引導他,前行。」原來他涉水前行的路一直沒有完結。〈夜行紀錄〉也是類似的結構,故事主角她和另外兩個人深夜徙步走進山中,拍農業復耕的紀錄片,行走過程中她不斷回想起自己的生命,包括她與父親的關係,她對好朋友素然和喜歡的人梓南的感覺,她拍紀錄片的意義等。這些回憶不純然是個人的,而是放在更大的時代脈絡中的剪影,例如拍紀錄片,她說「如果沒有了如許的動盪和不安,她不過是在做讓人麻木消費或無關痛癢的製作,一切作為變得可有可無。」故事最後一段,他們一行人穿過築起鐵絲網的土地,穿過行車天橋下的通道,以為要去的地方離鬧市是很近的。但最後一句是:「不,梓南說,那是邊界,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表面上,那是一件深夜入山,然後迷了路的事,但如果跟其他故事並置去看,那又是一場前行,過程中透過敘述仿佛安頓好了一些意義,但去到最後一切好像又回到起點的歷程。
《結局的意義》說《聖經》提供了一個家傳戶曉的歷史模型,《聖經》第一章是 〈創世記〉,最後一章是 〈啟示錄〉,開頭第一句是太初有道,故事的最後是「儘管如此,主耶穌啊,我願您來」。Frank Kermode說這是一種天衣無縫的理想結構,首與尾的關係十分和諧,而人類的故事就是太初有道與主耶穌再來這兩端中間插入,人類也是在兩端的中間死去。同時,因為主耶穌最後的審判,中間過程中那些未能解釋的都會被提供意義,最後都會安頓下來。我不能說《夜行紀錄》的敘事模式與這種經典的敘事模式相反,就小說而言,它還是很大程度做著小說常做的事,例如描述人物、提供背景、協調敘述元素之間的關係、敘述時間上有明顯的連續性等。但它有好幾篇故事的結局,好像又回到開頭,是一個循環或圓形的敘事迷宮嗎?應該不是的。我想,那是作者拒絕在結局部分給予人物一個安頓,拒絕在最後的部分以結局的力量去為中間賦予終極的意義,包括人物人生的意義、事件的意義以及敘述的意義。
在此,不由得想起Wallace Stevens說的一句話:「想像力,想像力總是顯現於一個時代的結局裡。」而這個可能就是《夜行紀錄》當中所描述的事件背後的現實──一個作者嘗試去回應,但始終堅持讓現實留在曖昧不清,未能安頓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