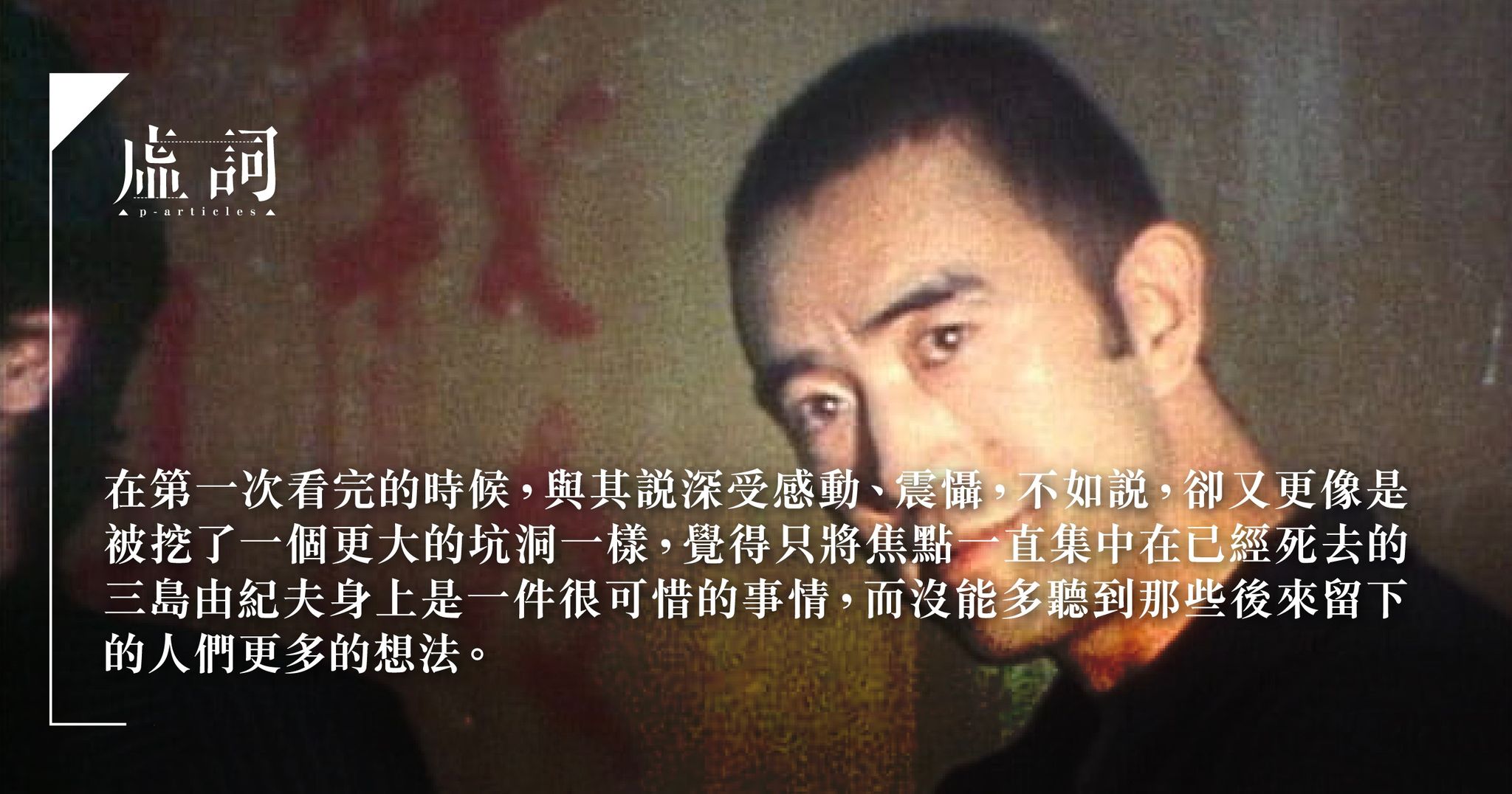《三島由紀夫:最後思辯》——建立關係與面對他人
《三島由紀夫:最後思辯》是一部很精彩的紀錄片,很多地方在觀看的時候讓人很想停下,不一定是思索一段時間,但至少想先讓感受沈澱一下,才繼續看下去整場辯論。然而,在第一次看完的時候,與其說深受感動、震懾,不如說,卻又更像是被挖了一個更大的坑洞一樣,覺得只將焦點一直集中在已經死去的三島由紀夫身上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而沒能多聽到那些後來留下的人們更多的想法。
我想大部分的人之所以會看這部片子,都是因為文豪三島由紀夫的關係吧?但這部片子到頭來讓敝人收穫最多的,可能是認識芥正彥這個人以及他的想法。而這部片最讓人印象的片段,也是芥正彥和三島之間的對話。
在這段對話裡,三島向芥正彥詢問了兩個問題,第一,在不賦予名稱的狀況下,人們如何建立關係?也就是說,有不存在沒有名字的關係嗎?或者應該說,一個關係如果沒有名字,那麼這個關係還能維持自己的持續嗎?第二,人和人之間常常存著各種「利用」,沒有這些「利用」,人與人很難建立所謂的關係,因為這些「利用」是人與人建立關係的「目的」,那麼在這些被建立的關係裡有不存在不含任何「目的論」的「利用」嗎?也就是說,有不存在沒有目的的關係嗎?
這段提問與對話無疑是「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鬪」這場對話真正的核心,也可以視為東大共鬪運動的意義之一,也就是如何重新建立人與人的關係?而非左派右派孰是孰非的爭辯。
對於「如何建立人與人的關係」,三島提出的答案是「天皇」以及「日本人」,因為對他來說,天皇信仰以及「日本人」的國族信念是組織社會不同階層人們的強大工具,哪怕他知道,自己心目中的「天皇」和「日本人」在一般人的想像中是有極大差異的,但為了讓人們支持自己,一起反抗現在的國家制度,「天皇」與「日本人」的民族形象是為了在彼此之間建立關係所產生的必要的「利用」,而他批評東大共鬪的學生應該和自己一樣,運用「天皇」和「日本人」的認同來獲得大眾的支持(哪怕他們心中對於天皇信念和日本國族認同是批評的)。
被譽為「三島由紀夫轉世」的日本作家平野啟一郎認為,三島是在說,到頭來「語言」還是重要的,沒有「語言」,社會是無法改變的,必須用「語言」進行歸類,用語言革新系統,這樣透過「語言」改變的事物才能持續下去,而不會失敗。
芥正彥在這方面上,是直接批評三島的。他詢問「但日本人這種概念,又是存在何處呢?」並且說道:「其實國籍根本不存在,不是嗎?」,三島笑了笑,說著:「那你是個自由的人,而我會尊敬你。」
從這邊其實可以看到,芥正彥並不是在質疑關係的建立是否需要「語言」,或不需要「語言」,而是在質疑那些被語言所形塑的關係是否是人與人之間真正的關係,也就是這些構築「國籍」、「天皇」、「法律」、「族群」等等「事物」的名稱與「關係」。
「這世界是閉上眼睛的,如果我們不睜開眼睛看向他人,我們是無法建立關係的。……如果不先和他人建立關係,我們甚至無法把這玩意(桌子)稱之為桌子。」
對芥正彥來說,是先有關係,才慢慢開始有名字的,而非相反。如果先用名字進行歸類,那麼就是「假裝自己可以單方面和他人建立關係,而無法意識到關係是可以被顛覆的。」得先面對他人,才能真正產生關係,而非先界定關係,才開始安排「會面」。
強調關係是面對他人的在場,可能和芥正彥的戲劇背景有極大的關係。因為一直以來,戲劇和其他藝術最大不同的地方,就在於觀眾是直接看見舞台當下在場發生的呈現,而不像文學、電影是透過剪輯好的文字和畫面來再現自己要呈現的東西。在劇場裡,如果演員當下不小心出錯,不小心跌倒或是背錯台詞,不像電影,他是無法刪減、彌補、重剪的,而是只能接著這個錯誤繼續演下去。也就是說,戲劇是在這樣一種直接面對,無法被重新剪輯的語言與狀態中,去和他人的存在建立關係的藝術與對話。
這也使得相較於重視文字、影像、照片形象的三島,比起建立關係,芥正彥更強調面對他人的重要性。因為建立關係雖然固然重要,但重點不是在於這個「關係」能否一直穩定地固定下去,而是在於這個被建立的關係有沒有重新被打開、重構的機會?而非被「語言」一直固定。對他來說,如果就如三島的「天皇」一樣,是沿用從前就用來穩定自身統治的「語言」來建立現在新的關係,那麼還不如乾脆不要建立所謂的「關係」,而是維持關係的斷裂逼迫人們持續面對彼此。
三島與芥正彥所思考的「持續」因此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對三島來說,所謂的「持續」,是將某樣被改變的東西在改變發生後,仍夠維持它的持續留存的狀態。平野啟一郎對三島文學的評論說地很好,他說綜觀三島的文學,三島在追逐與表現的其實一直都是一種「剎那的狂喜」。換言之,三島所思考的「持續」,其實是一種「剎那的永恆」,是對某個片刻成就的永恆回歸(這兒的「永恆回歸」不是尼采的意思,尼采的「永恆回歸」或許更接近下文芥正彥所思考的「持續」)。
然而,對芥正彥來說,真正要思考的「持續」,不是事物的持續,而是「改變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就是他口中所說的「時間」的可能性,要思考的不是持續,而是在建立關係的同時仍讓關係的能持續發生變動的「可能性」,這也才是革命真正的意思。
電影的最後,年老的芥正彥在影片中,對那個時代發出了一段感慨,他說:
「那是語言作為人與人之間的媒介最後還能展現力量的時代。」
將這段話和電影中另一作家平野啟一郎的想法並列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同時也是很矛盾的,因為平野認為改變終究需要依靠「語言」,然而根據芥正彥的感嘆,語言在這時代卻是已經失去力量的媒介。
為何會這樣呢?答案很簡單,雖然兩人口中說的都是「語言」,但芥正彥說的「語言」並非平野啟一郎所說的「語言」。因為芥正彥所說的「語言」,其實是更像那種人與人面對彼此,真實發生在場的語言、對話,而不是被再現的語言、文字、符號,而他的感嘆揭示了我們現代的困境,也就是我們如何在一個語言總是被再現、剪輯的時代中,去持續進行新的「語言」的鬥爭與真實地面對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