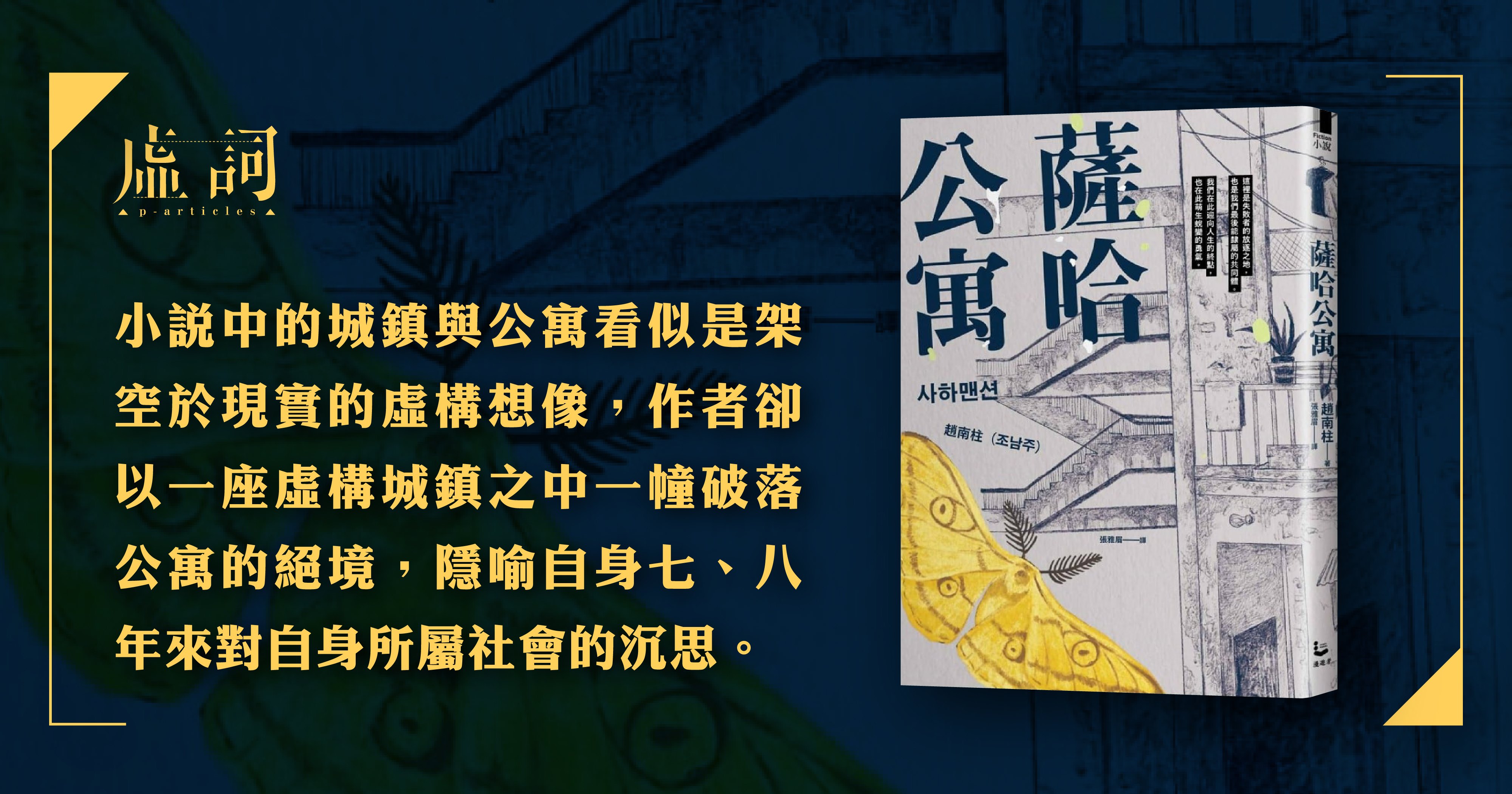飛蛾撲火終成蝶——讀趙南柱《薩哈公寓》
書評 | by 林兆軒 | 2021-01-11
趙南柱這個名字,華文讀者可能不太熟悉,但若然提及她的成名作《82年生的金智英》,相信大家一定不會陌生。假若《82年生的金智英》為韓國女性在嚴重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環境下所遭遇的壓迫與剝削作一側寫,自二〇一二年起開始創作,其間多次修改,最終於二〇一九年才完成的《薩哈公寓》似乎展現了作者更大的野心,切意將自身對韓國近十年來發生的社會問題所作的考察,轉化成為一則惡托邦(Dystopia)寓言。
惡托邦作為一種敍事方法,投射了一個與我們現實生存情境密切相關卻又更等而下之的世界。在惡托邦式的世界觀裡,人類社會看似紀律井然,背後其實深受極權根深蒂固的制約與規訓所支配,人民漸逐陷沒於如流沙的極權之中,動彈不能。藉由文學想像終極之惡的降世,似乎成為了人類反思既有制度成規的缺口之一。《薩哈公寓》中奉行特殊體制的國家「城鎮」,以及作為失敗者的流放之地的「薩哈公寓」,正好構成典型的惡托邦圖景。
城鎮是「一個不知是大企業還是國家的怪異城市國」,遵行七人總理團制度。總理團以徹底保密的協商過程組成,總理團名單是城鎮至為重大的秘密,整個城鎮從來無人得知誰是總理;一切國家政策的發布,皆由總理團代言人代勞。為了杜絕動亂的一切可能性,坐擁絕對權力的總理借「特別法」制定一連串臨時法案:「電視和電臺頻道單一化,新聞媒體也遭合併,還廢除特定的大學科系,瞬間使諸多大量教授、研究員和學生失業。有些商店和公司因為位置、業種、公司代表的履歷等問題突然關門,卻沒辦法抗議。假日有三名以上的成人集會時,必須事先取得許可。宗教團體也是一樣,有些字不能說、不能寫,也不能印刷出來。無論前後脈絡為何,一旦使用就會受罰。有些人不能見、有些歌不能唱、有些書不能讀、有些路不能走。」城鎮的戶籍分為L和L2兩種。L是永久居住權,也代稱擁有居住權的人,全是經濟能力相對優越,又擁有城鎮所需的專業知識或技術的精英份子。至於L2,他們只有為期兩年的短暫居留權。L2大多只能於工地、物流倉庫、清潔公司等地方工作。至於小說的一眾主要人物,既不是L,也不是L2,而是城鎮的最底層「薩哈」。顧名思義,薩哈公寓是薩哈們的主要據地,薩哈甚麼都不是,他們甚至不被視為人(正如小說明言:「在『城鎮』中,只有L和L2兩種人。」)他們只是維持「城鎮」運轉的工具零件,在「城鎮」的默許下代替L和L2完成一切低賤的工作。
《薩哈公寓》採用片段式敍事,大部分章節將敍事焦點集中於一名薩哈,記錄她們遷入公寓的原因及定居後的生活:既有出身自育幼院,矢志成為幼兒教師,卻因L2身份而只能成為合約員工,最後在城鎮育幼院爆發新型傳染病時被指派照顧病童而丟了性命的恩辰;也有天生獨眼而只能在酒吧工作的莎拉及其長期遭受家暴侵害的母親蓮花;以及獨一無二的傳染病倖存者友美——小說曾交代新型傳染病的特性是百分百的流產率,友美卻是在母親染疫卻成功康復的情況下出生的唯一嬰兒。友美的特異體質成為城鎮覬覷的資產,他們以放任薩哈公寓為代價,將友美私有化為城鎮科研工程的實驗品。以上提及的小說人物全是女性,小說續用慣常的女性視角,反映作者對女性處境的關注未有停歇,但她未止步於性別議題的單一探討,反而藉階級、性別、殘疾、樣貌等多重社會身份的交叉複疊,模塑更複雜卻更準確、宏大的社會弱勢處境。
恰如作者自言:「這本書就像是,當我覺得我所屬的共同體和韓國社會好像答錯問題時,改用我自己的方法去解問題的那過程,所以這就像是本記錄答錯題目的筆記本。」小說中的城鎮與公寓看似是架空於現實的虛構想像,作者卻以一座虛構城鎮之中一幢破落公寓的絕境,隱喻自身七、八年來對自身所屬社會的沉思。如此一來,作為城鎮正規編制以外的一個孤絕的空間,薩哈公寓隱喻一個被邊緣化的共同體,隱示作者對南韓社會結構嚴重失衡的猛烈批判。小說描述的船難(及其觸發的革命)、新型傳染病,甚或薩哈們因身份「原罪」而無法於社會向上流動的元素,實際上亦不難在近十年的韓國社會中找到對應。
作為惡托邦小說,《薩哈公寓》的情節展現人民嘗試與極權對抗的典型模式。這段情節以珍京及道暻這對姊弟作為主角。小說開篇即以一宗謀殺案佈下全書的懸疑基調:死者是城鎮的L——秀,她是一名兒科醫生,不時挪用醫院資源為公寓的小孩診症,因而與道暻結緣、交往,更遷入公寓與道暻同居。當秀的死亡引發全城鎮的關注後,二人的關係加上道暻的薩哈身份,令他在輿論的審判中成為兇手,為此道暻只好四處潛逃。秀的死亡不是整部小說的主要關懷,死亡的真相於小說中段和盤托出後,情節推進的動力轉移到珍京身上。珍京是個怯懦怕事的人。軟弱的她決定挑戰極權,與其說是受到自由與正義等宏大使命所感召,毋寧說是出於對道暻、友美的愛,對總理團的恨,以及對被警察追捕的恐懼與絕望。「信念本身沒有力量,讓人行動的是直接且具體的情緒。」在了解到道暻以及友美所遭受的折磨後,她別無退路,只好選擇直面恐懼。為了營救下落不明的道暻和友美,她選擇直探城鎮的核心,到總理府除掉總理團。
正當讀者期待一場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的人民與極權正面對抗時,小說終章迎來最大的衝擊。珍京遇到的只是總理團秘書長,他對珍京持槍闖入不以為然,他不但屏退守衛,更邀請珍京親手推開總理團所在的會議室大門。珍京鼓起勇氣,用盡全身的力氣將大門推開,卻沒想到「她的眼前一片空。那裡沒有會議室」,遑論總理團。小說堆疊已久的張力瞬間化為烏有,珍京直指總理團的仇恨亦頓時撲空。失去發洩對象的暴怒,剎那間萎縮成莫大的虛脫感,徒留珍京(以及讀者)的無所適從。透過抹煞「總理團」,令其成為從不存在的存在,作者似乎刻意在關鍵時刻掏空極權的本質,以無法填補的遽然落空逼使自己(以及讀者)反思極權的意蘊。當慣常指涉「極權」的國家政治制度突然消失(又或從不存在),「極權」到底是甚麼?
傅柯對全景監獄(Panopticon)作為現代社會權力機制的詮釋,似乎可以為我們帶來一點啟示。在《監視與懲罰》一書中,傅柯認為全景監獄的特點在於「將一種對於可見性有所意識及持續性的狀態導引到受拘留者身上」,以確保權力的自行運作。全景監獄以一個圓形大廳組成,警衛(監視者)處於圓心的高塔而囚犯(被監視者)被安置於圓周的囚室;囚室之間可以互相探視,卻沒法感知來自高塔的監視者目光。每位被監視者因彼此注視而意識到自己是永遠被互相監視的對象。他們也無法感知來自監視者的監視,為了安全感,他們只好永遠警戒、規範自己的行為,因而陷入自己正被永久地監視的假想。久而久之,被監視者自身成了自己的監視者,構成一種強而有力的自發規訓。傅柯視全景監獄為紀律社會權力機制的隱喻,藉由瓦解「看與被看」的關係,權力得以自動化及個人化,常態性的壓力在一切失序的行為出現前已經發揮作用,令權力的規訓作用趨近完美。在全景式的權力機制之中,不再需要規訓的執行者,權力的自動化將規訓銘刻於社會制度之中,自行運轉。「真實的臣服乃機制性地產生在一個虛構的關係中。」
回到《薩哈公寓》,城鎮的社會模式正是全景式監視的權力機制運行到極致的狀態。當秘書長向珍京揭露真相後,他要求珍京回到公寓,當作什麼事也沒有發生。秘書長毫不畏懼珍京將「真相」帶走,這種高度自信,正是秘書長對城鎮居民在全景式監視的壓制下絕對無意造反的確信。即使總理團(高塔中的監視者)從不存在,城鎮的人民(被監視者)已自動臣服於總理團的神話之下,受全景式監視(被監視者的相互注視)所支配:L受既得利益馴化,是不會反抗的「收成期」順民;與修正扭曲的制度相比,L2樂意追逐的,亦只有成為L的榮譽。擁有「真相」的,是無法撼動體制分毫的「薩哈」。城鎮杜絕社會階層流動、連結的任何可能性,藉階級差異的偏見構築高效的監視系統,一切巔覆勢力在其萌芽前已經注定銷亡。小說藉薩哈公寓這片化外之地,安置被城鎮排拒、失去能動性的弱勢份子;將住客們的生命故事凝聚成一個被邊緣化的共同體,意在反射深植於整個城鎮社會結構的冷漠與不作為。城鎮的運作體制代表着資本主義社會的高度異化,城鎮中佔據精英位階的L事不關己地冷待沉澱於社會結構深層的一切逼迫、剝削及壓榨,這種層階式的疏遠與隔絕形成規限社會連結,加劇社會中人民個體化的孤絕狀態。人民的冷漠促成個體之間的排擠,從而育成另一種摧毁社會的「極權」,一道不用政制推動卻足以令人民匐伏跪拜的「特別法令」。如此看來,小說對極權的想像似乎有別於一系列惡托邦的經典作;作者想像的極權稍為背離了政治學的標準定義,她不只抨擊暴烈的極權政制,而進一步將批判的目光投射至滋養極權的異化與腐朽的人心。
珍京不是唯一掌握真相的人,原來幫助自己潛入總理館的公寓管理員老頭和就業輔導所所長也曾經來到這裡,並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接觸到盒中剩下的唯一「希望」。小說的最後一幕,是珍京無法忍受秘書長字裡行間的輕蔑和誘降,糾纏之間,她如野獸般將秘書長的肩膊咬得鮮血淋漓,更搶回手槍指向他。小說沒有以俗套的槍聲作結,反而將最後一個鏡頭放在一隻從窗口飛入的蝴蝶:「有一隻蝴蝶飛過來,打開翅膀停在掉落的葉子上。那是隻亮黃色的蝴蝶。在牠展開的翅膀上,有像瞳孔那樣圓圓的,旋渦狀的黑色紋路。牠頭上的觸角張開呈寬扁貌,越接近尾端,觸角的形狀越尖銳,看起來彷彿在頭上插滿了兩根小鳥的羽毛。」
蝴蝶是小說中的一個重要意象。正如上文提及,城鎮曾經發生一場船難,消失的是一艘載有大量希望逃離城鎮的難民的貨船,總理團以沒有出航記錄為由拒絕承認事件,受害者家屬為此張貼單張抗議,卻被總理團以「特別法」判處死刑。城鎮居民意識到「特別法」的權限過大,事件延燒成一場「蝴蝶革命」,這是城鎮中難能可貴的覺醒時刻,卻在警方暴虐的鎮壓下胎死腹中。自此,「人們在說明極端混亂、不安及恐懼時,都會用蝴蝶革命作為比喻。沒有人知道為何偏偏選了『蝴蝶』這種昆蟲。有人說因為在火焰中飄散的灰燼很像蝴蝶,也有人說因為在那天,蝴蝶翅膀的拍動,為城鎮和城鎮外的其他國家招來了颱風。」有趣的是,珍京看到的根本不是蝴蝶,而是蛾。(在小說初段,珍京曾經看到一隻黃色「蝴蝶」,但友美指正那只是一隻蛾。辨認蛾與蝴蝶的關鍵性差異,在於兩者在靜止狀態時,蝴蝶的翅膀會收起而蛾的翅膀會張開。)珍京未有斟酌兩物種的生物性差異,在她選擇性的認知下,趨光撲火的飛蛾再一次經歷蛻變,幻化成拍翅可能造成颱風的蝴蝶。珍京以不可逆轉的弱勢處境與總理團對抗,就像飛蛾撲火一般自尋死路,但在小說最後一刻她深信自己的舉動誓必帶來改變,於是她再次看到「蝴蝶」。在旁人眼中脆弱的飛蛾,卻在珍京的眼中蛻變成蝶,這一種誤認的盲目,似乎亦隱喻了作者對社會弱勢終能改寫命運的期許。
作者曾經透露,薩哈公寓這個特殊處所的構思,其中一個靈感來源是香港的九龍城寨。曾幾何時,九龍城寨被認為是罪惡的溫床,是「香港政府不敢管、英國政府不想管、中國政府不能管」的「三不管地帶」。作者對九龍城寨的理解,卻是「被遺棄的人們聚在一起,形成一個自治的生活共同體。」作者希望指出,公寓並不是城鎮市民眼中罪惡的淵藪,而是弱者暫時得以喘息的庇護所;她關懷的,終究是犧牲於階級、貧窮及暴力之下的孤絕個體。薩哈公寓的巧思得力於舊日的香港,城鎮的異化卻又巧合地與香港目下的境況遙相呼應,這相信是作者始料不及的,在筆者看來卻不勝唏噓。《薩哈公寓》的珍京尚算幸運,她能夠接觸到城鎮的真相,浴火重生。她得著一份將飛蛾認為蝴蝶的蠻勁,雖則兒戲,但不失為一點希望。更重要的是,她擁有一起分享真相並繼續堅持下去的公寓同伴。不知道其他活在城鎮之中的薩哈們,又能在何處領受這份奢侈的幸運?又有多少薩哈有勇氣相信,終有一日,飛蛾也能蛻變成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