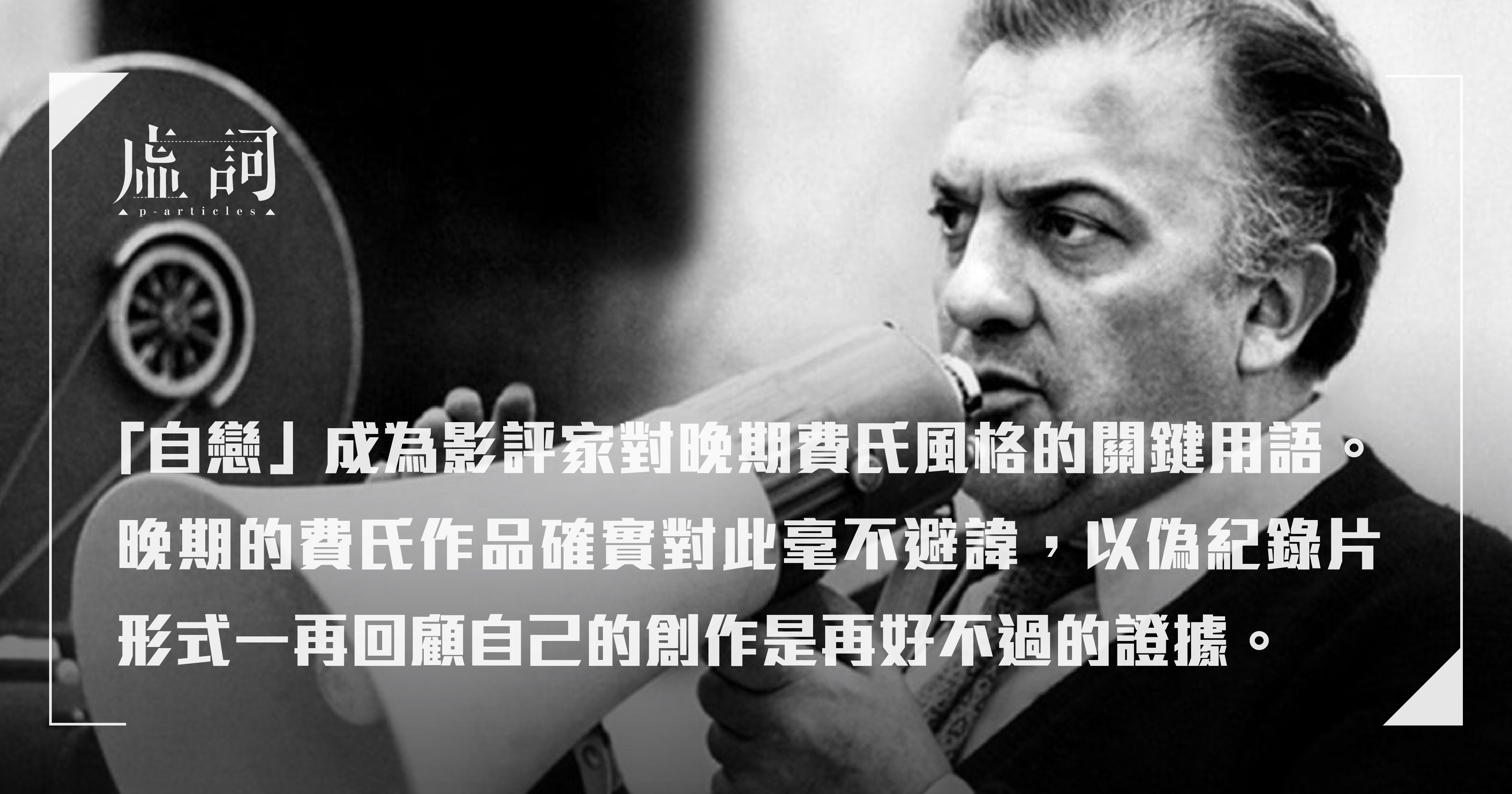我是說謊者:雜談費里尼的電影風格
「生活像是一場夢,但有時夢卻也是個無底洞」
《白酋長》(The White Sheik)
從幻象之間的跳躍尋獲救贖與恩赦,到遊戲夢境本身的虛幻馬戲團,最後反思內省的後設電影,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大概是意大利新寫實主義一代中,風格最多樣的導演之一。適逢今年是費氏百年誕辰,電影節發燒友一口氣放映其全部作品,讓影迷無間斷體驗一部部經典。
「騙子與聖女」是早期費氏風格的基礎,當中《白》是費首次個人執導的通俗劇,卻已盡現其掌控命題的匠心獨運。故事以一對新婚夫婦渡蜜月開展,天真不經世事的少婦和保守、被家族名聲綁住的年輕丈夫,在羅馬一日的歷險中各自陷進了幻像與破滅。少婦誤打誤撞進入了製造幻象的劇組後,她無法從虛幻的愛情投射裏抽身,幻滅後不得不面臨崩潰,最後重投夫君的懷抱。與此同時,丈夫被困於家族聲望和宗教教條的夢魘,唯有遇上兩名流鸞才感覺到真實的安慰,最後迫不得以與背叛自己的妻子步進教堂。理應代表幸福的大教堂,如今卻成為了暪騙幸福的墳墓。由此可見,《白》大抵總括了早期費氏風格的要點:鏡頭跟隨被騙者進入某種如夢如幻的空間,人物的虛空感總是讓他們自進騙局,幻起幻滅始終未為他們帶來真正的關懷或愛,最後唯有死亡或虛空終老。
由此延宕,早期的費氏偏好描寫處於艱難的環境和命運的人物,即使性格設定不盡相同,但作品均帶有創作者對於幻想與現實之間的純真探索。《大路》(La Strada)、《騙子》(Il Bidone)、《花街春夢》(Nights of the Cabiria)這三部同期作品,既是體現到日後風格的雛型,也是費的不同實驗。相較於《大》和《花》中馬仙娜飾演的善良女孩,《騙》裝扮成傳教士的騙子屢屢行騙得手,雖然主角有其苦衷,可是他卻不由自主的過着騙徒的生活。故此,觀眾看到這個無賴,反而呈現了某種自作自受的暢快感。縱使主角彷彿被跛腿少女感召而救贖,終究他還是為了自己的女兒,選擇騙掉他的同伴、跛腿少女、自己(和觀眾)。看似是一段成長軋跡,即使內心的掙扎全炅真實的,事實上一切的反省均為虛假的,唯有謊言本身是永遠的,而謊言帶來的,只有死亡。如此一來,費氏已經為「電影作為謊言」一席話留下了註解,揚棄「新寫實主義」強調的現實依據,費選擇擁抱電影的虛幻本質,不再強求故事的道德教訓,並且沉溺於箇中的浪漫。
走過新寫實主義的各種嘗試後,顯然這樣的形式已經容不下費的想像力。耶穌像降臨現代娥摩拉城,《露滴牡丹開》(La Dolce Vita)成為了費氏風格的一大轉折點。有趣的是,原以為批判絕美之城的上流社會,卻反而為費帶來康城金棕櫚獎,甚至捧其至國際影人的地位,為他帶來更多的美酒佳人。行雲流水的長鏡頭捕捉流麗奢靡的羅馬晝夜,一眾名流與狗仔隊上演一場場的攻防戰。身為專欄作家的主角總是受女人寵愛,一方面他對聲色犬馬的生活感到厭煩,另一方面他卻脫不開慾望的枷鎖,可悲又可笑。強烈的費洛蒙彌漫於鏡頭內外,美艷卻冷浚的鏡頭沒有提供深刻的情感共鳴,反而將一眾場口回歸至它們的原型:無止盡的片段章回式的生活剪影,卻亦可視為標準的三幕劇處理。正如費自言《露》好比顛倒的《神曲》(天堂—煉獄—地獄),一開始神從天上俯視眾生,馬切羅希望自己能在紙醉金迷的生活中,保存作家的清澈心靈。可是愈走下去,卻愈是沉淪。最後腐敗的氣息充斥於畫面中,唯獨的渺小救贖則在於一段悄悄耳語。人生本無預設的救贖和希望,所謂的「甜蜜」必須憑自己的理解拼湊出來,如同觀眾亦必須自行編織片段的脈絡。即使眾人解讀不一,但電影收結於男人和少女被海水分隔在兩岸對望,看來兩者都不像是出路。
有趣的是,費氏以作品赤裸呈現自己的情慾和生活實況的形象,實在太深入民心。除了《露》馬切羅的形象,加上當時《想當年》(Amarcord)甫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導致稅務局開始懷疑他有暪稅之嫌而展開調查,最後使他失去了一橦房子,繼而迫於無奈拍出《美男子》(Fellini’s Casanova)。
正如費自言沉溺創作「無數磨人、不斷改變的迷宮組成的人生」,陷入絕望的精神狀態下,《八部半》(8½)彷如湼磐般橫空出世。《八》基本上延續了《甜》自傳式的剖析與自我對話,以電影作為媒介探紂自己還能拍甚麼,還想拍甚麼。正如片名已開宗名義的以自己的作品數量起題,《八》既有總括過去作品,亦有開辟另域的企圖。以一位不知要甚麼的導演,指涉當刻自身拍攝經歷的後設電影,《八》的劇情源自於主角無法構想劇情的掙扎和零碎幻想,即使主角無法完成他的作品,觀眾卻已看畢一部電影。風格上如此誇張的改變,費自言此乃源自榮格的精神分析理論的影響,因而展開長期的夢境紀錄寫作,逐漸使他意識到電影—夢境(潛意識)的邏輯關係。如此一來,除了總結過往自己對於幻象—現實的思考,《八》自揭童年記憶、對女性的幻想與焦慮、擺明車馬的身分代言、概念後設等元素亦可視為後期作品的原型。
走到晚期,詩意而靡爛的意象可謂充斥於費氏作品。《想當年》(Amarcord)回顧法西斯統治的童年往事,籍由自身記憶重塑影響深遠的三個女性形象:聖母、烈女和妓女。極為荒誕的開場(火燒女巫的祭典)已經呈現記憶的凌亂和慾望。鏡頭遊離於三十年代的法西斯年代,漫天紛飛的塵菌中有信,費首次「直接」呈現自身的成長經驗,純情男孩對自瀆的性幻想對象揮之不去,暗戀對象被班上的小胖子娶走,家中永無寧日⋯⋯即使取材自真實的童年經驗,但費氏的處理卻是後設和超脫邏輯的,而摒棄一貫的觀影習慣後,費意圖以個人的世界觀合理自己的創作。如此一來,作為被譽為費氏最後一部大師之作,《想》正好統合了其晚期風格的體現。歷經所謂的全盛時期後,一方面費氏的想像力馳騁至遠方,極為華麗的敍事鋪張逐漸偏離影評人對他的既有理解;另一方面,不斷老調重彈的命題亦使人覺得煩厭,導致批評聲浪此起彼落。《愛情神話》(Fellini’s Satyricon)中男體女體橫陳的奇觀,大量文學和劇場的指涉使人目不暇給,是遙遠古老的超現實、物慾橫流的世界;即使內容的參考近乎無從稽查,對應的虛妄生活看起來與當今狀況無異;《羅馬風情畫》(Fellini’s Roma)中「羅馬」作為電影中的後設意象,將真實重新虛構、扭曲。鏡頭的不存在感也着實是費氏的獨特敏鋭呈現;如同《羅》的「羅馬」,《小丑》(The Clowns)的「小丑」亦是後設的容器,其象徵的既是電影的虛實,亦是似瘋或傻、大喜大悲的精神狀態。徹底陷入自戀與自省的二元之間,無疑使觀眾反應兩極,卻成就了更極致的敍事實驗。
另一邊廂,費一向摒棄知識份子的冷峻解構,透過徹底無視邏輯的敍事趕走一眾猶如《安妮霍爾》(Annie Hall)中那個偽知識份子的影評人,毫無根據的想像串連成為詩篇的續句。如此一來,「自戀」便成為影評家對晚期費氏風格的關鍵用語。事實上,晚期的費氏作品確實對此毫不避諱,以偽紀錄片形式一再回顧自己的創作是再好不過的證據。《追訪費里尼》(Intervista)的魔法變出銀幕,重溫過往作品的真摯反應,除了大玩後設關係的華麗技巧,也是坦承自戀後的自省;《珍姐與佛烈》(Ginger & Fred)關掉表演的燈光,兩位費氏產出的傳奇相互傾吐作為演員心聲,成就一場真情動人的對話戲,也是費思考為何而拍的告白。
郵輪停在碼頭上,乘風捲浪泊岸,鏡頭捕捉各個登船的人,無聲的鬧市走進默片時代的記憶。旅程終究完成了,電影卻歸返最初。一切的鬧劇,不過是一場浪漫的虛幻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