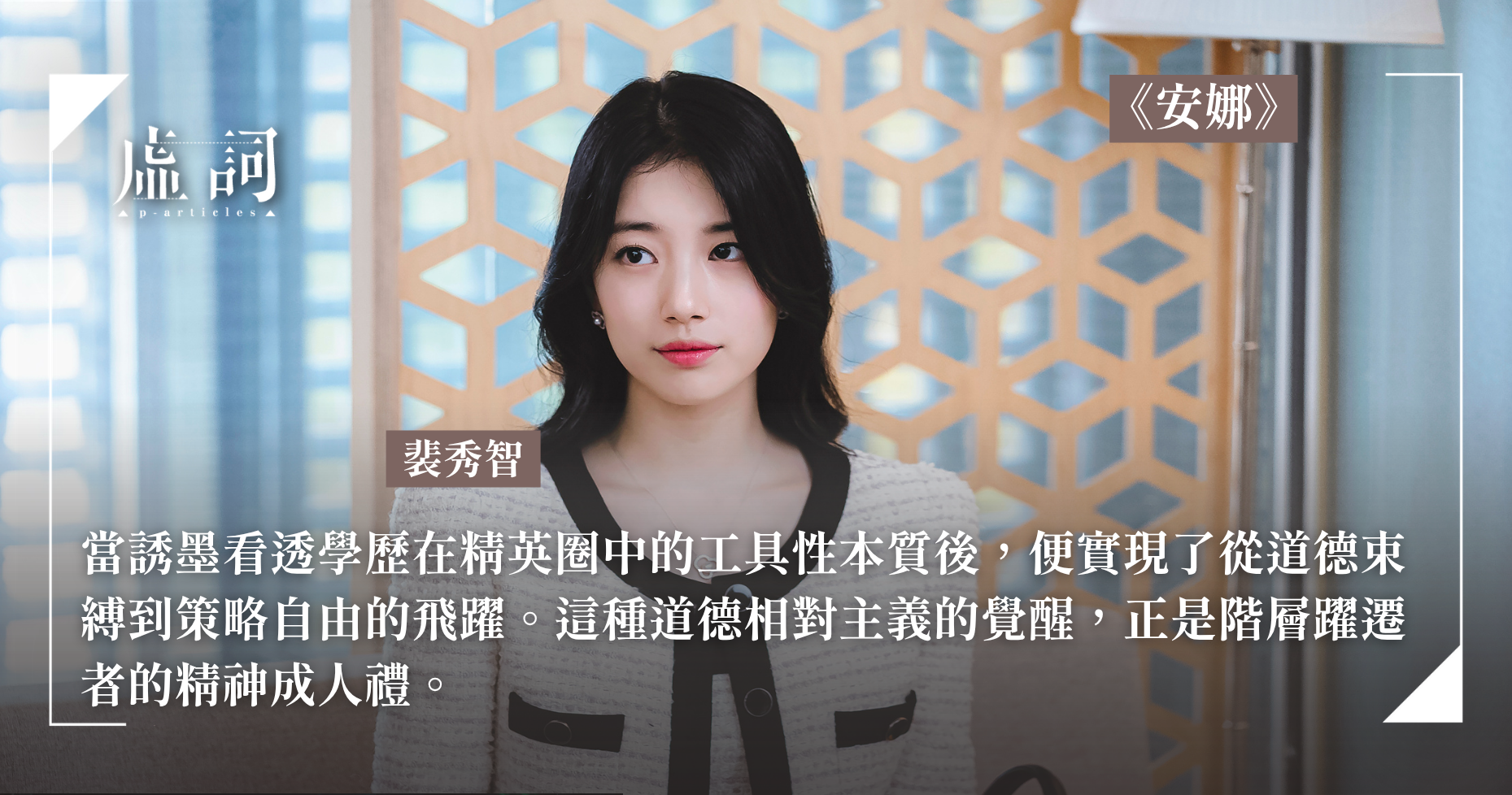惡毒、真實、密教:關於辛波絲卡與文學通訊
書評 | by 雨曦 | 2025-06-11
雨曦讀畢《辛波絲卡談寫作》,指出辛波絲卡在這本書以幽默犀利的筆鋒,戳破創作者的自我陶醉與抄襲迷霧,並以「脆弱的植物」或「餐廳菜單」等生動比喻,回應年輕作者的迷惘。從《辛》中可看到辛波絲卡對文學本質的深刻洞察,用幽默與智慧解構創作困境,強調天賦與耐心並重,並鼓勵創作者以謙遜和自我批判的態度,擁抱生活的真實面貌,創作出有血有肉的作品。 (閱讀更多)
建築師看電影《粗獷派建築師》:一場美麗的誤會?
影評 | by 梁顥維, 陳偉信 | 2025-06-05
梁顥維與陳偉信觀畢《粗獷派建築師》,指出電影將粗獷主義建築與主角身份定位為劇情道具,卻未準確反映其理念,建築設計缺乏邏輯,甚至與主角最終成為國際大師的結局顯得脫節。他們作為建築計設師,藉此為大家簡論粗獷主義,強調結構清晰、功能優先與材料「如實」呈現,讓讀者在享受電影的同時,釐清電影中關於建築學的一些爭議與誤解。 (閱讀更多)
在「自由通行」之間的短暫假期:評《監獄中的哲學課:探索自由、羞愧與救贖的生命對話》
書評 | by 王奕蘋 | 2025-06-03
王奕蘋讀畢《監獄中的哲學課:探索自由、羞愧與救贖的生命對話》,指出作者維斯特在英國監獄教授哲學的經歷為核心,交織個人創傷與受刑人的故事。維斯特在獄中向囚犯教授哲學,帶領他們探討自由、善惡與命運等議題,在一個受限環境中尋求心靈救贖的過程。書中亦提及社會對惡的定義與污名化,亦令王奕蘋與讀者不禁探問「裡面的人生」與「外面的我們」之間的聯繫,重新思考自由與善惡的界線。 (閱讀更多)
誰說這算是情愫——談張婉雯的《有心人》
梁璇筠讀畢張婉雯的《有心人》,認為書中的 「有心人」相對日常狀態的「沒心人」,在城市壓力下滋生複雜欲望,既審視他人又壓抑自我,甚至不自覺讓「有心人」寄託著/實踐著自己的欲望。令梁璇筠不楚憶起昔日香港文藝及影視作中大多都有著活色生香的生命力,而現在只剩下看似一本正經、健康至上,強調安全,實則是把情慾貶低、壓抑,甚至到了自我欺騙的地步。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