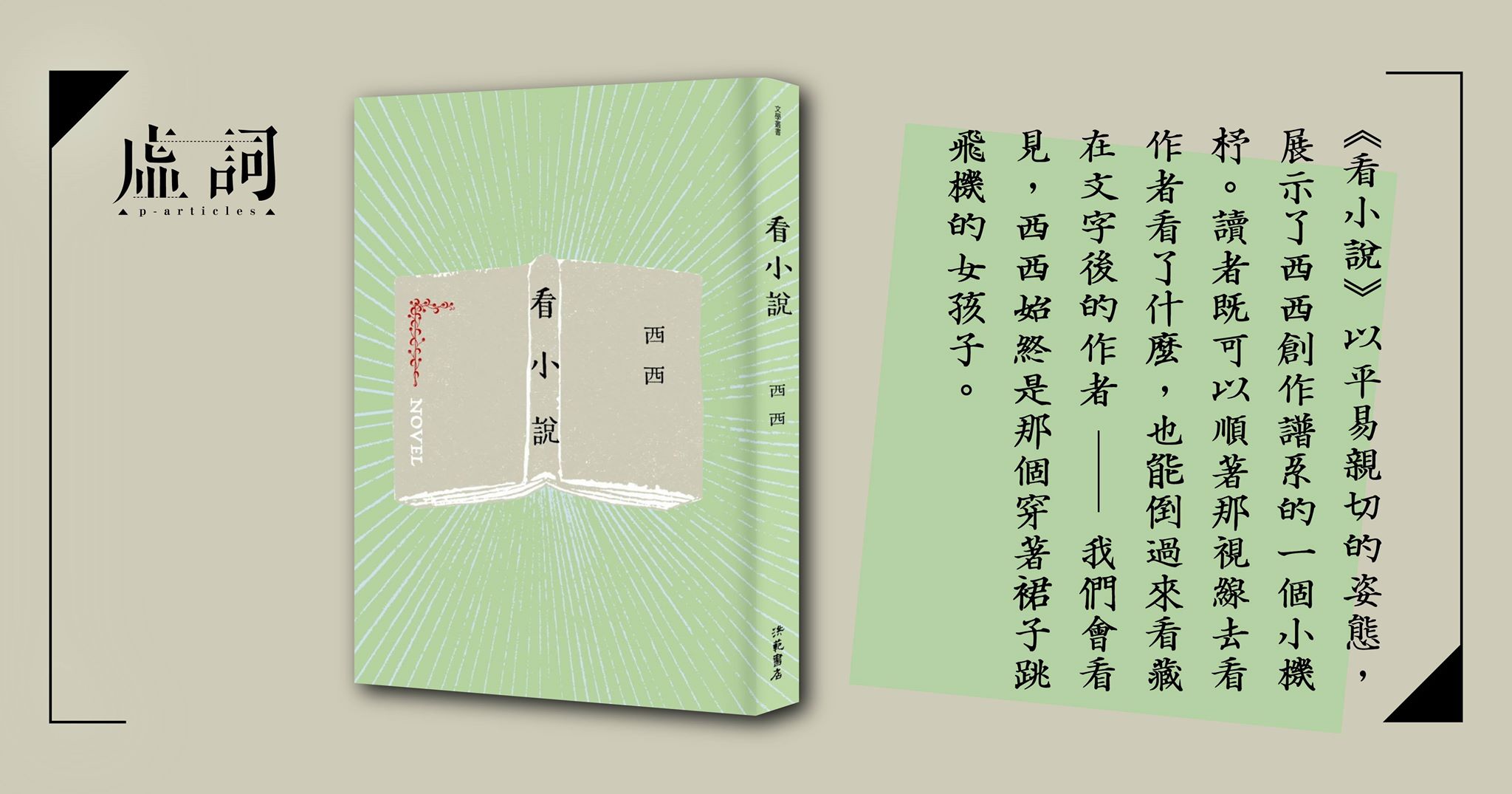大師與學生——看西西看小說
名字簡潔得刪無可刪,西西的新書就叫《看小說》。書中收錄西西幾年前的專欄短文,都是她看完小說後的筆記。「看」可以說西西近年寫作的一種方法,目光追尋的對象從《看房子》和《我的喬治亞》的建築、《縫熊志》借以「演義」的擬人毛熊、《猿猴志》的猿猴到《我的玩具》的玩具,眼神專注於某一物類,用耐性整理來歷和光譜,用細心勾勒特徵和深意。
當作者把這樣的觀察寫成文章,便提供了代讀者而讀的便利。這樣說顯得像一種濃縮湯粒的銷售概念,把寫作的生產性定位為完全向外,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作者本身就是一個讀者。有人說一個好作家要麼完全不讀書,要麼狂讀書。前者想像某種石頭爆出來的曠世奇人,無需參考,單憑一己天才便能創造新氣象;而西西是後者,更是後者的典範。我們說西西的小說有創意、有視野,那無疑來自她閱讀經驗的深刻沉澱,才能隨手拉出那麼斑斕紛陳的知識與技藝。對此最誠實的展示,是她過往出版的兩本閱讀筆記,1986年的《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和1995年的《傳聲筒》。在《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的序中,西西敘說其心愛作家卡爾維諾的《看不見的城市》的情節——當「說故事」本身已是故事,西西對此的重述,早已透露這一系列閱讀筆記的書寫驅力:「就像這一個讀者向另一個讀者講他喜歡的一本書」。
看什麼
那麼西西喜歡看什麼小說呢?從《看小說》,我們能再次窺見西西閱讀範圍的廣泛,書中提及的小說來自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葡萄牙、美國、加拿大、波蘭、土耳其、芬蘭、墨西哥、阿根廷、秘魯、尼加拉瓜⋯⋯用西西的話說,「閱讀可以開闊我們的視野,讓我們認識別的國家」。當然,以國籍去分類作家和作品、把語言對應民族國家的做法,往往會關限了虛構的能動和認同的複雜性。《看小說》的書單中便涵括一些體現文化流動與反思的作品,例如美國作家瑪夏.漢彌頓(Masha Hamilton)的《駱駝移動圖書館》,寫一個美國人前往肯亞一個叫米迪迪亞的貧窮村落,營運移動圖書館以提高當地識字率。西西敏銳地總結出小說背後的問題意識:「就算處於良好動機,是否就有義務以至權利,教育以至主宰滯後者?」殖民歷史下文明與野蠻的衝突,是現代文學的一大母題,佼佼者是西西在《傳聲筒》和本書都寫過的庫切。
《看小說》從中段起揀選了一些第三世界的作品,當中西西對兩本印度小說評價頗高。這兩本小說都充滿苦難,亞拉文.雅迪嘉(Aravind Adiga)的《白老虎》的悲劇源自種姓制度,英德拉.辛哈(Indra Sinha)的《據說,我曾經是人類》則取材史上最嚴重工業事故的1984年博帕爾毒氣泄漏災難(Bhopal disaster)。西方人對第三世界的凝視時常內置了獵奇或觀光的心態,相較之下,西西更欣賞印度人寫印度的內部視角,更肯定魯西迪以外的印度大作家是可期的。(但也值得補充,這種「自我書寫」被承認的現代性條件:這兩位移居西方的印度作家都用英文寫作,由此獲得布克獎的入場券。這也許是邊緣(非歐美語言)小文學從理論跌入現實體制的命運。)
怎樣看
但是否第三世界文學本身就等於是好的?作為同行的西西,除了重視小說的思想文化,也時刻注意技藝問題。西西也讀了十分普及的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的《燦爛千陽》,讚嘆於素材細節之豐盈,亦為敘事節奏感到遺憾,她借用福樓拜的比喻(珍珠作為內容、線作為技巧)說「那條把珍珠穿起來的線卻時緊時鬆」。對阿爾及利亞作家雅斯米納.卡黛哈(Yasmina Khadra)寫中東戰亂的《巴格達警報》的評點,則把話說得更白:「作者提出警報,用心良苦,但小說畢竟還有一個美學的道理」。
以上說的是寫實技巧的不圓滿,但從她把恣肆狂想的魯西迪作為大作家的一個標竿,便知道西西眼中的美學價值,仍是那麼「老土」如一地側重創新。我們記得,西西是八十年代把中國小說介紹出來的先行者。中國大陸文壇在改革開放後進入新時期,如今一些世界知名的中國作家在當時急遽冒起。西西當時參與編選洪範出版的「八十年代中國大陸小說選」,卷一以莫言〈紅高粱〉命名與壓軸。莫言師承自馬奎斯的對中國小說寫實傳統的突破已是共識,而西西也是拉美文學爆炸的忠實擁躉。雖然沒有專文討論,但馬奎斯和波赫斯還是在《看小說》裡神出鬼沒,「做我們胡亂闖蕩之後重返的原鄉」。
但那黃金時代畢竟已經逝去,西西慨嘆似乎再沒有出現能令人激動的大師。在《看小說》的後段,西西集中閱讀了一批充滿巧思、刻意偏離規範的作品,探視當代小說的新可能。同樣以此為目標的金匠獎(Goldsmiths Prize)即吸引了西西去讀原文,例如愛爾蘭作家Eimear McBride的得獎作A Girl Is a Half-Formed Thing(西西譯作《女孩是半形成體》)通篇是一個受盡傷害的少女的內心獨白,迂深的情感不經理性中介而體現為錯亂語法。在這種「呈現真實」的方向上,西西發現的另一位前衛小說家B. S. Johnson走得更遠,他視故事或虛構為說謊,其小說被稱為「非虛構小說」,附錄的何福仁文章更將之比作現象學。
種種實驗有其冒險的價值,即便可能差錯腳;而在光譜另一端,穩打穩紮「好好講故事」的代表可數強納森.法蘭岑(Jonathan Franzen)。這位迅速獲正典化的美國作家大概每十年出一本大部頭長篇,西西讚賞《修正》和《自由》「回歸常態的人情,回歸細水流深的筆法」,寫出了普世性的情感內核。看來各家各派浮華潮流的新嘗試,對西西來說還是不盡人意:「現代小說一大毛病是,許多都不好看」。
誰在看
西西說《看小說》不是文學評論:「真正的文評,我不會寫」,這是謙遜之言,亦是對文體的誠實自覺。專欄寫作有其先天侷限,文章在大眾傳媒刊登,始終一定地要求通俗性——當然通俗性與深度絕非兩立,更確切的界限在物理性:寫不長。對原書情節的轉述,佔據了這批文章的最主要篇幅,其餘已沒有很多展開的空間。事實上,從《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開始,西西索性發展出一種模式,一開篇即直入正文概述情節,到最後一段方現身說明書名和作者。從另一個角度看,用千字收納長篇小說的規模,那要求十分精準的取捨,才能使被壓縮的來龍去脈不淪為木乃伊式的梗概,極考驗作者功底。
西西把這系列的寫作比喻為「學生做的讀書報告」,她也的確像那些仍願意坦誠表達情感的學生,在文章中完全不見評論的嚴肅架子,反倒不時流露「不合時宜的」真心話,絕妙爆笑,直如彩蛋。在書評書介與廣告越趨混合難分的環境下,表露自己的不喜歡是少見的,但西西就這樣做了。比如〈野兔、烏鴉和小熊〉寫到芬蘭作家亞托.帕西里(Arto Paasilinna)兩部有關動物的小說,愛動物的西西不滿作者的殘忍,看到《遇到野兔的那一年》中懲罰偷食烏鴉的血腥橋段毫無憐憫,「這本書,我扔掉了」;《牧師的小熊僕人》則奴役熊來雜耍賺錢和服侍人類生活,「哦,嗯,這本書又不用看了」。又像《魔山》的男主角愛上一張X光肺片,西西以此聯繫自身經驗,她曾患肺炎而照出一張傷痕累累的X光片:「難道有人會愛上這樣的肺片?小說家真愛開玩笑。」拆同行也拆自己的台,不留半點情面。令我心頭一暖的片段,出自寫科塔薩爾的〈美西螈〉。科塔薩爾終生沒能過上好日子,而近年阿根廷首都為年過六十的作家提供退休金,西西知道了這個消息,多希望科塔薩爾有這樣的機會,養好身體,「可以每天去看他喜歡的美西螈,以及其他,看著看著就寫出更多出色的作品」。
西西把寫人物的小說家分為兩種,一種是天馬行空、遊戲態度的「皮影戲」,另一種是具體而微、質感實在的「麵粉公仔」。事實上,西西的寫作本身就兼具兩種特質,心性純真,技巧爛漫。一方面,我們從《飛氈》等作都見識過西西想像的飛揚,另一方面,西西筆下人情之溫柔敦厚至近作《織巢》仍綿延不減。《看小說》以平易親切的姿態,展示了西西創作譜系的一個小機杼。讀者既可以順著那視線去看作者看了什麼,也能倒過來看藏在文字後的作者——我們會看見,西西始終是那個穿著裙子跳飛機的女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