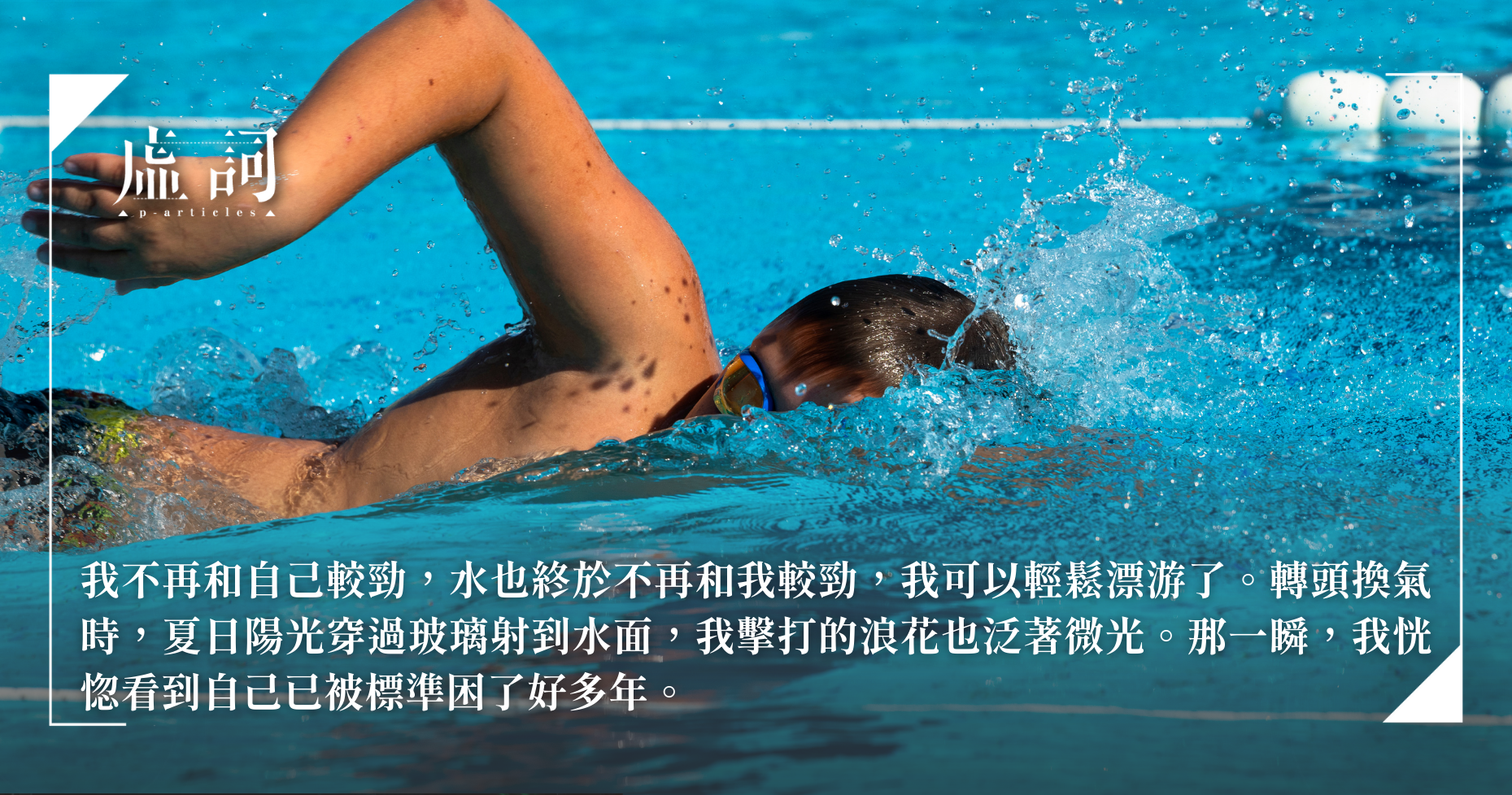蛇美文蛇美人
今年正值蛇年,令惟得想起吳煦斌的〈獵人〉的蛇,其攝人心魄的雙重本質——既令人著迷,又暗藏殺機。此蛇的意象不僅停留於自然,更延伸至藝術領域,特別是荷里活黑白電影中的蛇(蠍)美人形象,《殺夫報》的菲莉絲嬌媚外表掩蓋致命野心,又到《墮落天使》的史蒂拉至《舊恨新歡》的凱西等等,她們雖命運不同,卻同樣有蛇的冷酷與魅力。 (閱讀更多)
悶
散文 | by 俞宙 | 2025-07-04
俞宙傳來散文,他總是提醒自己別買太多人偶,要不然之後搬家真的很麻煩,但總是一而再再三地敗下陣來。他認為躺在盒子裡的人偶是最完美的,四肢以鐵絲細細綁縛,規矩地固定在瓦楞紙盒裡;頭髮壓得服服帖帖,盒子一側塑封著精緻的衣服和飾件。把娃娃取出來,就像解救一個被封印的沉睡精靈。替人偶梳妝打扮是一樁很神聖的儀式,也是俞宙生活中少數能掌握的安定。 (閱讀更多)
科幻小說
散文 | by 無鋒 | 2025-06-20
無峰傳來散文,書寫一個單性生殖的文明中,小棕人帶著好奇與渴望,嚮往加入外太空探索的熱潮。然而,母親分享 「纖維人」 的故事希望打消小棕人參與外太空探索。「纖維人」作息規律,且十分崇拜一個會發光的矩形物體。有的纖維人隨意浪費資源,有的則相聚嚴肅討論節省資源來拯救他們的星球,他們的一舉一動都相當神秘詭異。 (閱讀更多)
回憶的內在意識
散文 | by 黎喜 | 2025-06-18
黎喜傳來散文,認為「現象學」是傷心哲學,為解構回憶的存續。他指出回憶是無可避免,記憶即便被過去埋藏,還是會被現在觸發,但經歷都引發不一樣的體會。忘卻過去或許是解脫回憶的出路,但正如過去無法抹滅,回憶亦難以忘記。而回憶的誕生來源於人對事物產生認知,命名即是認知的開端,從而留下逝去而又無法擺脫的回憶。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