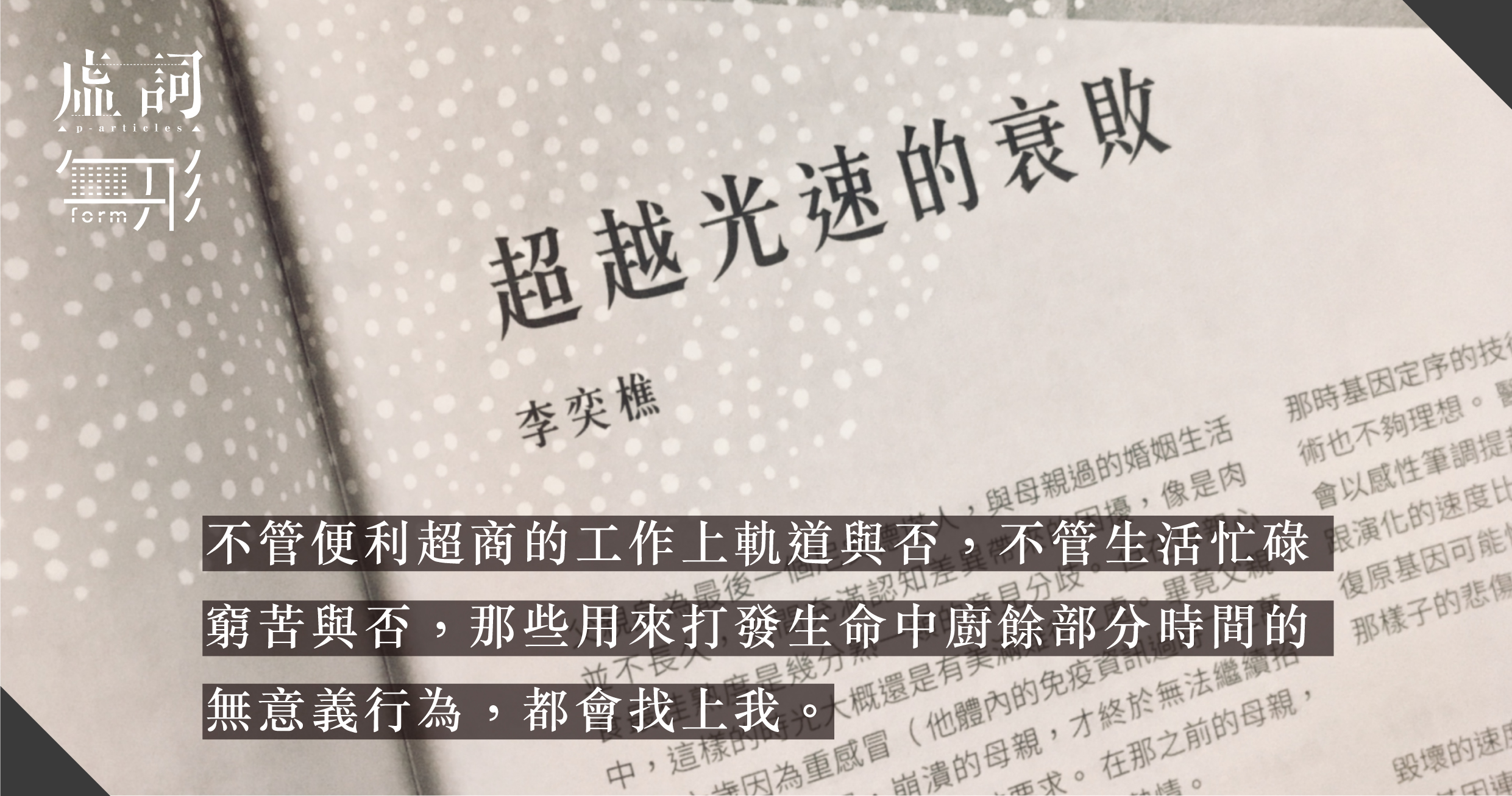【無形.寒】超越光速的衰敗
小說 | by 李奕樵 | 2018-10-19
父親身為最後一個尼安德塔人,與母親過的婚姻生活並不長久,期間充滿認知差異帶來的困擾,像是肉食最佳熟度是幾分熟一類的意見分歧。但在母親心中,這樣的時光大概還是有美滿難得之處。畢竟父親二十六歲因為重感冒(他體內的免疫資訊過時了三萬年)過世的時候,崩潰的母親,才終於無法繼續招架探索頻道拍攝小組的採訪要求。在那之前的母親,如冰河般排拒一切,無視各種穿鑿或熱情。
聞訊趕來,幫我檢查的醫師也不忍心雪上加霜,通知母親我是個性無能的事實,當然另一個事實是,醫師自己也不願意接受。
「其實並不意外。就跟馬跟驢產下的騾,或老虎跟獅子製造出來的彪一樣,尼安得塔人跟一名健康現代黃種婦女的愛之結晶也沒辦法製造正常的精子。」醫師說。
「這樣想起來還滿理所當然的。」八歲的我對醫師說。
但醫師根本沒鳥我,自己喃喃述說這件事有多麼多麼的合理,解釋解釋著就抽抽搭搭地哭了起來。
送我回家的正妹研究員傳醫師的口信告誡我,如果我母親沒有提起就別告訴她事實,如果她開始希望抱孫子,就交個女朋友敷衍她沒關係。
「博士認為你母親也會跟他一樣難過。」研究員說。
但聰明的母親當晚在餐桌上就識破我簡陋過時的演技。
她知道無論如何這個世界還是會讓我活下去,放心地剃度出家了。
那時基因定序的技術還不夠發達。低溫保存細胞的技術也不夠理想。醫師一直跟我保持通信聯絡,每次都會以感性筆調提起,低溫福馬林裡基因毀壞的半衰期跟演化的速度比起來是多麼短暫,並且不斷修正預測復原基因可能性期限的計算式,不然連他自己都覺得那樣子的悲傷很抽象。
毀壞的速度會隨著時間趨緩,前面十年可能會有10%的基因連結斷裂,但隨著巨大複雜的基因愈來愈少,剩下那些較短的片段也沒那麼容易壞。但到那時候,要把拼圖般的基因碎片拼回去,已經非常困難了。
我們可以參照著現代人類的基因拼回去,反正人類與尼安德塔人的血緣本來就如此接近,但也因為如此接近,兩者之間的重要細微差異難以不被忽略,或是早已無法辨識、斷裂而流失。雖然整件工程還是比「給猴子一台打字機跟無限的時間,便能打出全套的莎士比亞」容易些,但也只是容易一些而已。父親才剛死,離猴子、打字機、無限時間的境地都還很遠,但會隨著時間亂度趨向「莎士比亞-猴子打字機」的速度,可是指數形式。
「一開始很緩慢,但後來會連光都被拋在後頭。」但醫師連預測那個不可挽回的日子都顯得吃力。
「所以我還無法在時間軸上分配我悲傷的強度。」醫師在信中如是說。
母親離開十年後,我找到了瑪莉安,把她帶到科博館,父親低溫福馬林標本的展示廳。「爸,這是我女友瑪莉安。瑪莉安,這是我爸,雖然不高但是很強壯。」我為他們兩人做個簡單的介紹,平扁的額頭(事實上髮線跟眉毛幾乎沒有距離)下,老爸雙眼圓睜。
「如果我們能有小孩,也許他懂事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比你爸老了。」
瑪莉安在說夢話。也許我應該先甩了瑪莉安。
探索頻道拍攝小組跟已經成年獨立的我關係也還算不錯,隔幾年見面一次時,還會刻意找話題聊幾句。而我每天騎腳踏車去便利商店值班,偶爾還是會繞路去科博館跟老爸打招呼。抬頭跟他隔著玻璃容器玩大眼瞪小眼的遊戲。
當來找我的正妹研究員按下公寓門口電鈴的時候,其實也是我內在生命的另一次重要分水嶺。我赫然發現我正在陽台敲製我的舊石器時代小玩意兒。拿一塊石頭敲著另一塊石頭。
我知道這樣的行為遲早會到來。不管便利超商的工作上軌道與否,不管生活忙碌窮苦與否,那些用來打發生命中廚餘部分時間的無意義行為,都會找上我。我曾試圖主動去左右它們的出現,但我所能想的方案遠比我所預期的還要有限,這令我茫然且自卑。我好奇父親會如何解決這項議題(在印象中他似乎不為此掙扎),於是翻出當年博士隸屬的研究單位對父親的觀察紀錄,試圖從其中獲取靈感,運氣好的話還可以考慮直接沿用。但博士那群人似乎對這方面較不感興趣,而母親當年如冰山的抵抗,也讓探索頻道拍攝小組沒能留下有意義的成果。我只好試圖延續我的茫然,以對抗那些令我自卑的、毫無想像力行為的到來。直到這一天下午,茫然之中,我居然開始依據小學課堂中得到的印象敲製切肉用的小石片,抵抗行為才算是徹底失敗。
「博士終於把足夠可靠的時間點算出來了。」當年的正妹研究員說,無視我滿身的汗與手上畸形的石片。
我對研究員的出現不算太訝異,因為醫師的信已經中斷三個月了。
「那是因為博士算出時間點之後就在耍自閉。別理他。」研究員為我解釋:「他嚷嚷著要把自己冰凍起來,好停留在絕望的臨界點之前。這個世界才不會因為這種軟弱的廢物停止轉動呢。」
我們在客廳邊吃烤肉邊談,為了將我手上的不規則石片合理化,我把它拿來切生豬肉,說真的並不好用,肉的邊緣碎碎的,而且都只能切得很大塊。研究員花了很長一段時間等我將肉烤好並灑上鹽,她沒有帶任何東西過來,在等待的時間沒說話也沒作任何事,只是盯著客廳的小桌桌面等我端出肉。
我實在不知該對她帶來的消息作何感想,醫師已經悲傷許多年,更強烈的悲傷對我來說也太抽象了。
「感覺主事者都這副德性,研究室也該關閉了。」研究員說:「博士算出的時間點是三天後的凌晨四點四十三分五十七秒,我們幾個研究生想在這個時候辦一個歡送趴。有興趣嗎?」
歡送誰?
「在認真考慮把自己冰凍起來的博士?或者是我們的青春?」研究員說:「怎樣都好,只是想找個藉口,跟朋友們好好慶祝新生活的到來。」
「原來是慶祝啊。」
研究員說:「就在實驗室的辦公區吧,順便隔窗監看博士的奇葩言行。你喜歡烤肉?我們有人工培養的猛瑪象肌肉組織,口感不怎麼樣,也沒有油脂,但梅納反應總是可以創造味覺奇蹟。」
我沒答腔。研究員說派對開始時間是三天後的午夜,我可以隨自己的意願出席。
「重現滅絕物種是很浪漫,但要真能做到,人類對現存的瀕危物種會有多冷酷啊。」她說:「現在這樣子比較好。」
她看起來真的不太沮喪。
那個時刻也算是父親種族歷史的另一個終點。但我看不出來這場派對有要我到場的必要性。
在研究員來拜訪我之後的第三天。我以準備慶典的專注程度,花了一整個上午四處採集各式現成食物,然後背著塞滿食物的背包進入科博館四處遊走。趁展示時間結束人群散去、而清潔人員尚未到達之際,翻身躲至尼安德塔專題廳裡的某一塊佈景背後。直到空調關閉,燈光熄滅。在佈景後,我用家中帶來的小掃帚自灰塵中清出一小塊空間讓自己舒適窩藏。
睡了一覺,醒來時吃掉帶來的波羅麵包跟蘋果,對照跟格林威治時間校準過的手錶,時間已經是凌晨兩點。
四點四十三分時,我坐在父親的容器前,打開肉醬罐頭,把肉醬塗在土司上。容器低溫維持裝置嗡嗡地運轉著,除此以外一切都很安靜,我邊嚼著碎肉跟麵粉,邊注意父親的臉,直到五十七秒的到來。
然後五十七秒過去。
一片寂靜,甚麼都沒有發生。也許研究員在許多個小時之前過去公寓找過我了,也許我的手機此刻有一兩通未接來電。也許派對很成功。也許她此刻已經遵循醫師的指示將醫師與他巨大的悲傷成功地冰凍了。如果是這樣,也許日後會被移來此處與父親一同展出吧?我盯著父親的臉,確信沒有任何變化,不論是過去幾年來,或是四十三分五十七秒那一剎那的前後,都沒有任何的徵兆與變化。
我繼續製造一份份的肉醬夾心吐司,一份份的把它們吃完,在這之間我一直瞪著其實我一無所知的父親。毫無選擇餘地,裸體的父親也只能瞪著吃肉醬夾心土司的我,因為我就坐在這個位置上,而父親的眼珠無法轉動。然後我拿出裝滿沸水的保溫瓶、鐵碗,開始泡泡麵。
長久以來被預言的、那些不可挽回的甚麼超越光速的那一瞬間,就這樣被我與父親渡過。
接下來,我大概會喝些雞尾酒,另一個保溫瓶裡有冰塊。再接下來,我應該會試著打電話給研究生或是母親或是瑪莉安。
再接下來,我應該會回家。為城市遙遠彼端市,無力傷害一切的巨大悲痛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