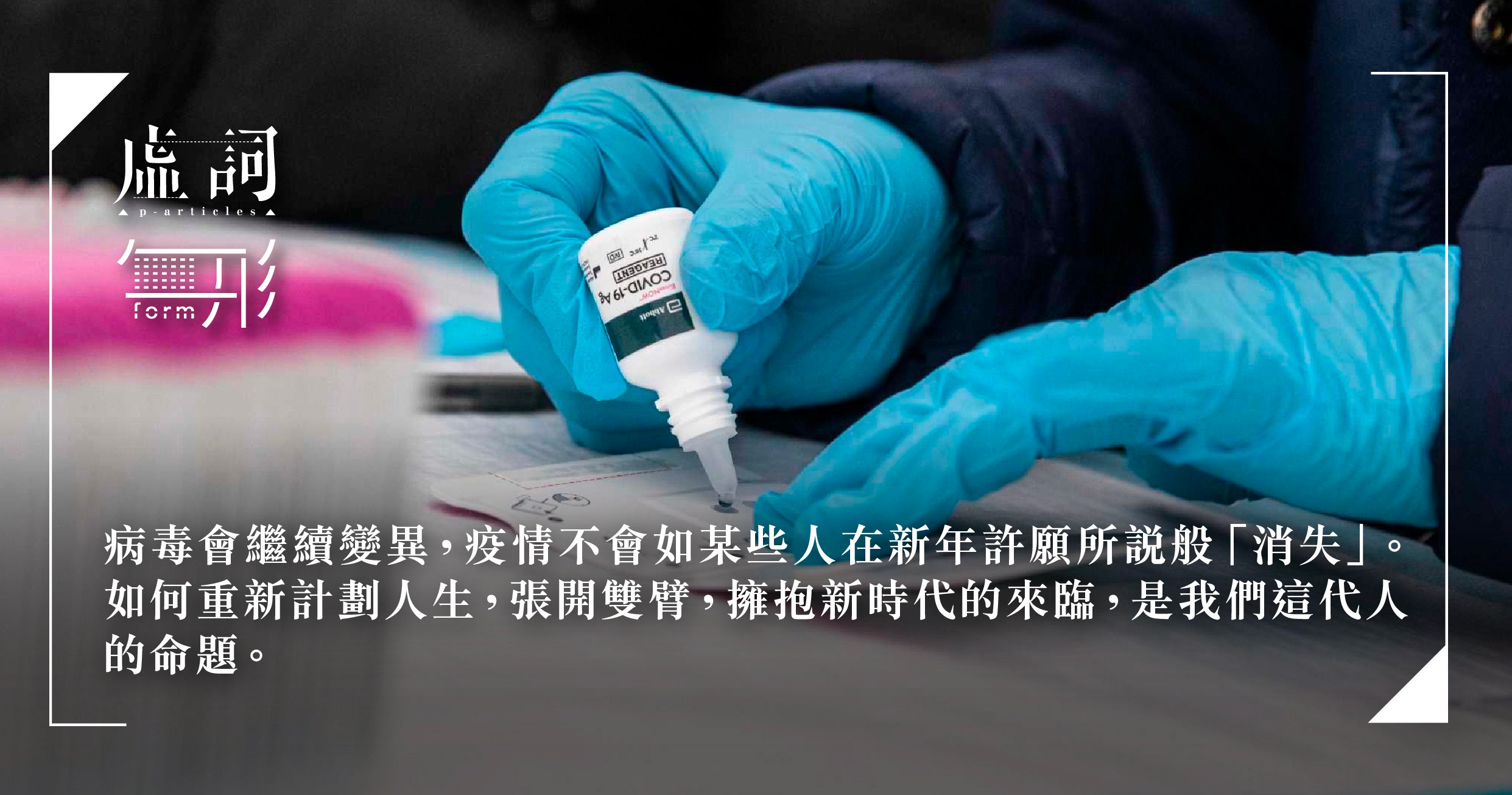【無形.中過又如何】從焦慮到釋放
我會分為四個時期去描寫我和家人確診前後的身心狀況。
「忍一忍」的時期:2020年1月至2021年4月
2020年1月,COVID19病毒首次傳入香港,造成零星的社區傳播。隨著防疫措施的推出,首當其衝的是我這一屆的文憑試考生。課堂突然中止,無法回校補課,甚至不知道考試能否如期舉行。在溫習計劃被打亂和焦慮不安的心情下,最後以不如預期的成績告終。
更無奈的是沒有了畢業禮和最後上課日。考公開試前最後一次回校,就是和同學取回模擬試卷。那天我們連回到已經空無一人的課室拍照留念,也被校工以防疫為由諸多阻撓。我一向著重事情要有始有終,十二年的中小學生涯,在這光景下突然完結,實在難以接受。有些朋友更是未來得及道別就飛走了。
進入大學後情況並無改善,感覺就像是中學的延續,繼續上網課,獨自在家中溫習筆記,然後預備考試。我連一個新朋友也識不到,放假時約出來見面的都是中學同學。每次跟朋友談天,也只能拿出中學的回憶來「炒冷飯」。
幸好疫情在四月慢慢減退,生活有望可以重回正軌。我告訴自己,失去了一年的人生,就當是乘機讓自己專注在學業上,令自己在「疫情消失」時有更多發展空間。
希望及曙光期:2021年5月至2021年12月
這段時間本地幾乎沒有確診個案,疫苗接種率也不斷提升,生活終於可以回到2019年前的模樣。在整個城市再次活躍起來之際,更強的變種病毒正在歐美多國急速傳播,而我們欠缺的是群體免疫力。
惡夢時期:2022年1月至2022年3月
2021年12月30日,我跟多個親人在打邊爐的時候,臉書不斷瘋傳一則新聞:望月樓群組一名非同枱食客初步確診。當大家在興高采烈地享受節日氣氛的時候,我已預知一場災難的來臨,放下筷子,胃部肌肉繃緊起來。
2022年1月5日,我剛教完補習,在即時新聞報道上看到:特首宣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食肆晚上六時後禁止堂食。我當時還自我安慰説:「若忍一忍十四天,換來大家的安全,沒所謂吧。」但我心裡知道這次疫情並不簡單。車外的陽光暖和,但我手腳冰冷,連午餐吃過甚麼也忘記了。巴士上的乘客分別佩戴著五顏六色的口罩,但也掩藏不住一種不能言喻的壓力。
2022的新年,一向幼稚的我首次不因為貪圖利事而期待拜年。坐在親戚密閉的私家車上,焦慮之感油然而生。疫情自葵涌邨一事之後迅速爆發,身邊的人隨時也會成為確診者。想到也許會被送到那些寒冷、簡陋、與外界隔絕的白色房子,不禁渾身不自在。我的腦海甚麼也沒有,只希望四時半的記者會上,台上的人不會説出一些驚人的數字。
隨著疫情海嘯式爆發,二月的春季學期在網上展開。我在大學朋友已不多,若再花上一個學期獨處,我快變成社恐了。我度過了人生最漫長的二月。看到大清早便要漫無目的地排隧檢測的隊伍,看到急症室外那些抵禦着凜烈寒風的病人,我在想:那怕我怎努力,也無法改變世界。疫情前的難關,難的是事物本身(例如一場難以勝出的比賽);疫情後的難關,難的是我沒有動力去做,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事情做來還有甚麼意義。只要疫情重臨,它可以壓倒一切,所有事也會靜止,你努力做過的事,很可能也會是徒然的。
我開始發現跟之前四波不一樣,疫情影響的不再是我們的生活習慣,而是我們本身。三月,疫情終於傳入我家,先後次序值得深究。首先於二月底,我發了一場前所未見、伴隨發冷和骨痛的腸胃炎,但我當時的快測為陰性。一星期後,跟我吃過飯的朋友和我的母親相繼確診。我不停在想:會不會是我把病毒傳給她的呢?答案永遠不會知道,因為原來我用了一枝2021年的過期快測棒。嘿。
不過,(疑似)確診對我來說反而如䆁重負,兩年來的窒息感忽然完全沒有了。疫情於三月中開始減退,隨着群體免疫屏障建立起來,我們不經不覺進入了「後疫情時代」。
後疫情時代:2022年4月至……希望直到永遠啦
後疫情時代不等於一切回復正常,而是我們經過疫情的洗禮後,變得更具適應力。
若要了解不同地方的價值觀,從不同國家的抗疫方式來找答案就最適合不過。要看一個地方是否宜居,不只看它國泰民安的時候,也要看它面對困境的時候。如何在公共衛生危機出現時既保持市民自由,同時保障市民健康,是全球每個政府的考題。
我從疫情中得到的啟悟是,自己一直待在這個城市,對世界其他地方所知甚少。我決定畢業後到香港以外的地方闖闖。疫情教會了我,有些事不做,可能一輩子也沒有機會做了。我們不會知道,多少個月丶多少個年頭或者世紀後,又會出現一次席捲全球的疫情大流行。
結語:我們終會是COVID確診者
迎接後疫情時代,COVID 的走向仍然有待觀察,但我們的心理狀態肯定有所不同。我們重新了解世界,我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我們看透了宿命的現實。事情有時會來個大洗牌,一些以經濟發展為傲的人口大國,卻會因為人口密度過高而爆發疫情。
病毒會繼續變異,疫情不會如某些人在新年許願所說般「消失」。如何重新計劃人生,張開雙臂,擁抱新時代的來臨,是我們這代人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