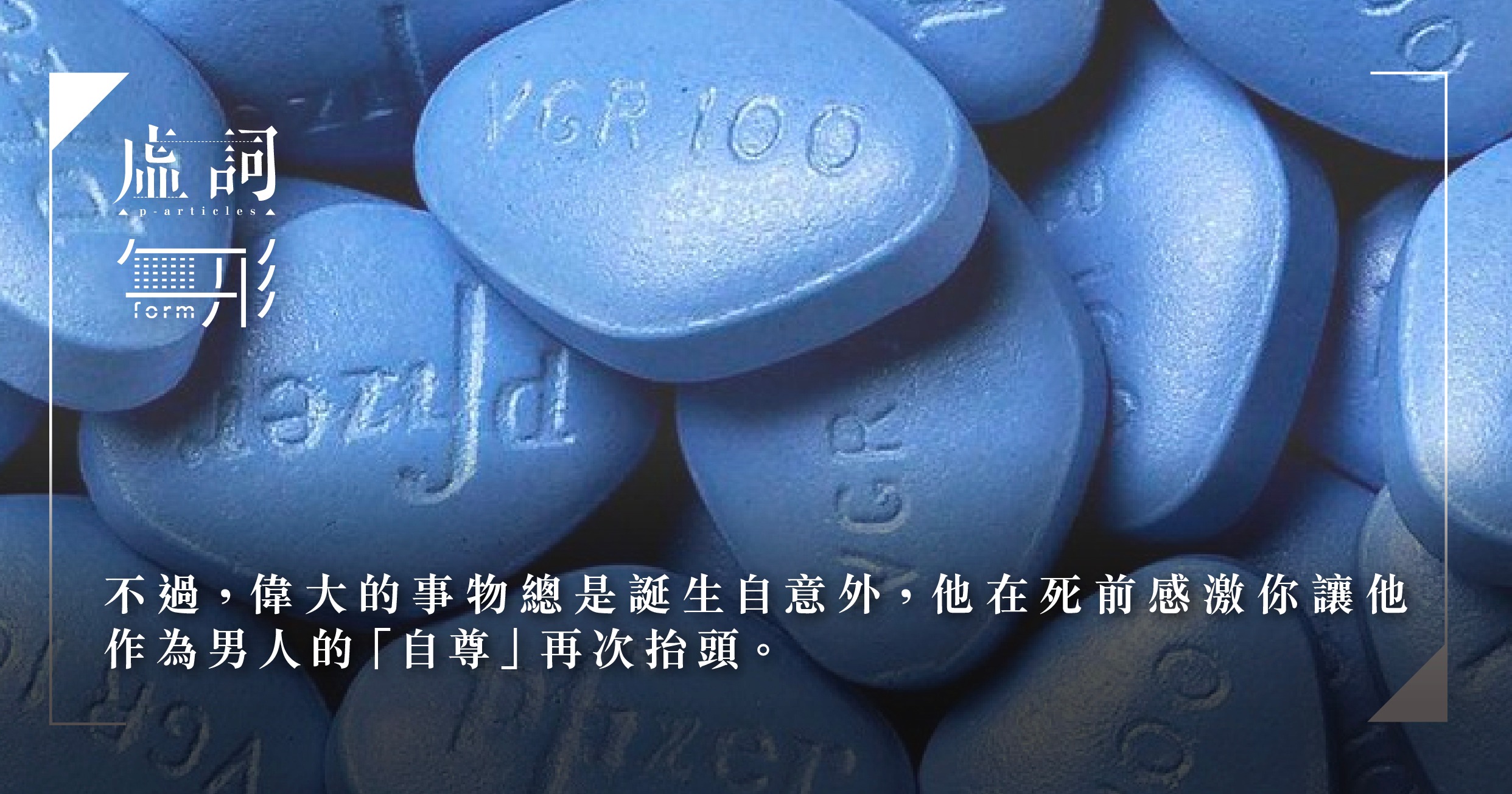【無形.夠鐘食藥】偉哥,以及其顏色的隱喻
他感到頭上的白光燈變亮,在這間白色的房子裡,他有一刻,誤以為自己來到了天堂。也對,創造你,確實是為了對抗死亡。但隨著身體的反應與眼前事物的模糊,他又認為找到了愛情的感覺,連手中的小紙杯也活潑如一隻小貓。這也對,你原本寄望作用於的地方是心臟,活著與愛情正是心臟所掌控的事情。如果一切順利,你將會延長這個老人的生命,可惜,他還是死了。不過,偉大的事物總是誕生自意外,他在死前感激你讓他作為男人的「自尊」再次抬頭。
你已無法確定有關於「你」的歷史的真偽,你只知道自己現在是棱形與「藍」色的。為什麼是「藍」?在油畫中,「藍」代表著高貴與神性,路易十四與聖母都身披著這種顏色,這也許與天空有關,而天空色彩的顏料,在自然界中卻難以獲得,這為這種原本就高高在上的顏色,添加了更無可替代的性質。在人類最早的文明,蘇美爾人建立的烏爾城中,宮殿、神廟、皇室用品都大量使用了「藍」,蘇美爾人認為這種從阿富汗的青金石碾磨出的「藍」(群青),代表月神(烏爾的保護神,太陽神的父親)為黑暗的天空帶來光明,是權力與信仰的象徵。
「Royal Blue」。
不過,正如你其中的一個副作用―對「藍」色的識別異常,在「科技」與「科學」所帶來的物質豐盛下,你的「藍」是積極的「藍」,是「文明進步」的「藍」。確實啊,《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的頭巾、梵高的《星空》、《神奈川沖浪裏》的大海,也是「藍」。只是它們的「藍」不是來自石頭的「藍」,而是人工合成的「普魯士藍」。聽說,這種「藍」的誕生也是一場意外。雖然這種「藍」的名字與軍隊有關,卻拓展了藝術的可能性,就像你雖然無掌握心臟,但,你掌握了性。而性的目的,是延續生命,也就是,對抗死亡。從這個角度來說,你最初被創造的目的,經過迂迴一點的路徑,最終在生育、繁衍後代層面上,還是達成了那麼些許。
然而,《星空》的「藍」與瑪利亞的「藍」,雖然都是「藍」,但兩者在波長(本質?)上有著兩位數nm(納米)的差異,如早上、中午,與傍晚六點的天空的分別。天空的顏色是流動的,「藍」也是流動的。在古漢語中形容天空為「青天」,而在當時,「青」既可以是藍,又可以是綠,甚至也可解作黑。而「藍」字在上古只是植物之名,而將「藍」引義為一種固定的色相(物理學),也許是在中古,大唐的杜甫就把天空形容為「藍」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台。)。在古希臘情況也類似,他們的語言中沒有一個純粹表示「藍」的詞,他們眼中的顏色是隨著環境流動的,並不依附於色相。在荷馬的口中,你的顏色在屋內可能是「κυάνεος」,而在陽光底下則可能是「γλαυκός」。就如「青」一樣,這兩個詞都能用來形容其他顏色,而且也可以是綠與黑。這兩個詞的使用的分別,在於事物在當前的環境中所呈現的亮度、飽和度與光澤等。上古時候的人對色相的理解,也許更近於佛教意義上的「色相」。
這讓我想起那件在網絡上曾引起幾百萬人熱烈討論到底是「白金」還是「藍黑」的長裙。顏色,猶其是你的顏色,總讓人類困惑,因為我們有一種對確定性、簡化與絕對的追求。在強盛的唐朝,天空的顏色被定性,在牛頓拿出三棱鏡後,「藍」的可能性被消弭。物理學上有了色相,就像那隻處於生與死重疊的貓的命運終於塵埃落定。而我們的歷史給予這些色相作用於每一個人心中的內涵,這,就是現代社會權力結構的一柱根基。所以,你被賦予了這一身「藍」。
Yves Klein稱「藍是宇宙中最本質的顏色」,我想,「藍」是人類傳統社會秩序的色彩,因此,《Matrix》中的那顆留在虛擬世界的藥丸是「藍色」的,跟你一樣。只是你更強大。你逆轉了男性性能力的衰退,逆轉了時間,讓被自然規律奪走了滿足永恆不變的欲望的能力再展雄風。你打敗了自然中的必然性,重現了魔法與神話中的奇蹟。你的勝利就像陽具般嵌入我們的潛意識,讓我們,或者更準確地說,讓既得利益者認為「人定勝天」同樣適用於應對人性與社會的訴求,古老的、傳統的、封建的價值觀也能透過現代科技對抗自然規律,甚至是對抗時間,讓「人」回溯為附庸與物。來源自科學的力量成為了人類心底最原始的欲望——「性即是權力」的招魂幡。於是,某些我們曾以為必然的社會發展趨勢因為你的出現而戛然而止,車開始倒退,所有人的處境開始變「藍」,或者說,在充斥著「化學」、「核武」、「代孕」、「AI」的空氣中漸漸「氧化還原」為「藍」。畢竟,「偉哥」是你的名字,「偉大的老大哥」。
但偉大的「藍」的你雖然能在「傳宗接代」的意義上對抗「死亡」,但其實,這並不是我們吞下你的目的,你的出現,並沒有改變出生率的每况愈下,你的出現,你的能力,實際上加速了使用者的死亡。你會導致那些服用你的年邁男人有更大的機會死於心血管疾病,死於你最初你被創造出來時,想要治療的疾病。你,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就如同現在我們知道藍色因為更渺小(波長更短)而更容易發生瑞利散射,所以天空是它的顏色一樣。只不過,男人與權力最不介意的就是矛盾,因為他們「做鬼也風流」,因為他們「只在乎曾經擁有」。只有在援引自你的高潮過後,他們才會靈光一閃地喃喃自語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隨即又拋諸腦後。
然而,我想如今提起藍色,跟你同一代的人首先想到的更多是梵高與畢加索,而非聖母,更多是NASA 與「高達」,而非路易十四。這當中固然有科技與藝術在理解與使用過程式中產生的遮掩性,但同時,這也是一種張力。也許,在這顆「藍色」的星球上,我們服贋於這樣一條規則:生於意外的事物與孕育它的環境之間無可避免地存在著張力,而這種張力,就是萬物生生不息的力量。如你,如藍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