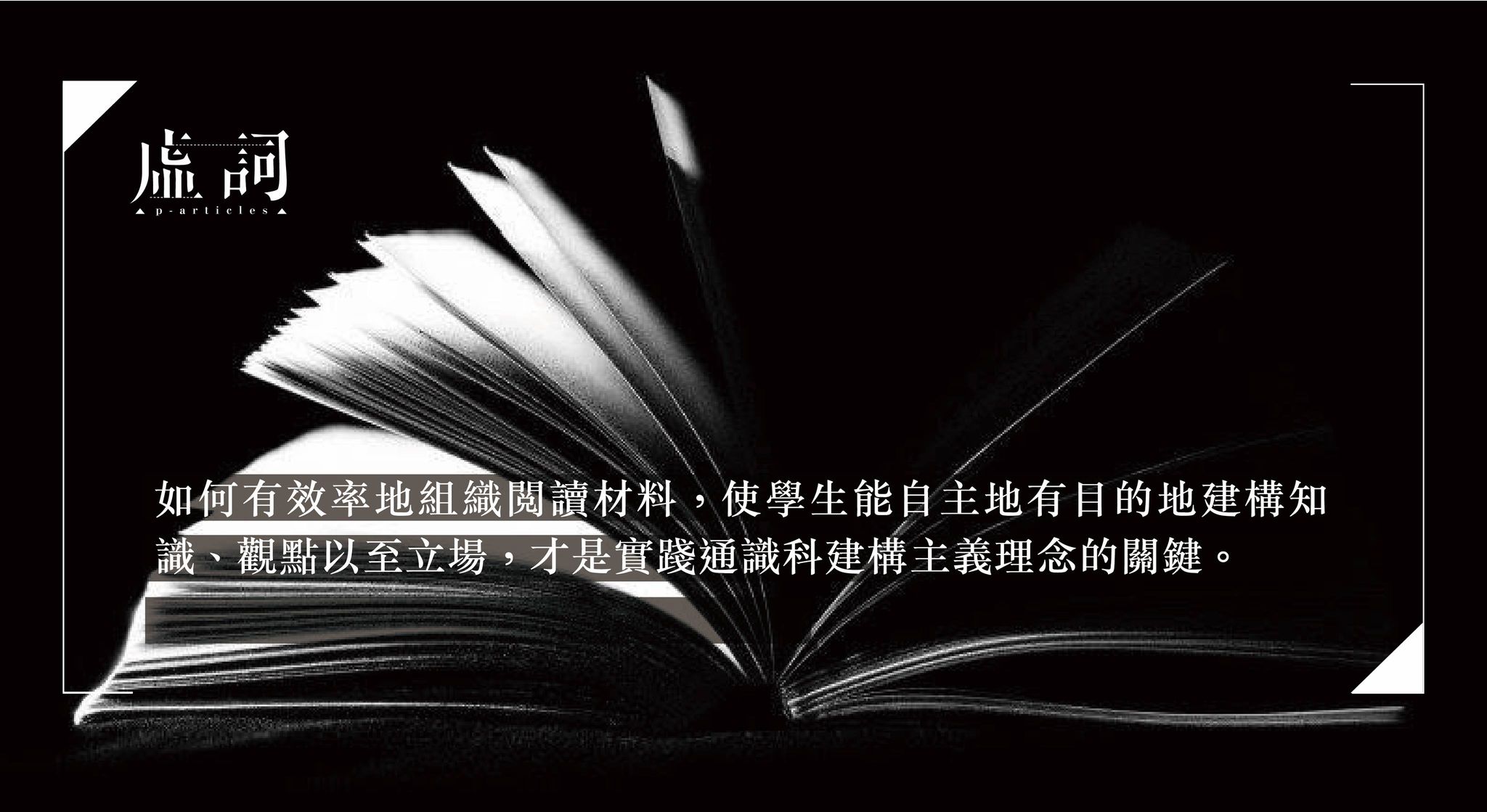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書、通識與教科書
教育侏羅紀 | by 陳曦彤 | 2020-09-21
通識書送審受社會各界關注,有傳媒把修訂剪輯成影片,甚至連初中社會及生活科的課本也一併報導,讓社會鉅細無遺地認識到政權如何審查教育界。為此,筆者衷心向各傳媒行家致謝。但亦由於大篇幅報導,社會甚至業界也出現恐慌情緒,在筆者看來,部分實屬不必而過度的反應;其實在通識的課程指引中,仍然明確指出不應倚重教科書:「鑑於高中通識教育科所研習的當前持續討論的議題仍處於不斷發展和轉變的過程中,因此,相關的學與教資源不應只源自教科書。這些議題各具爭議性,學生須自行探索不同的資料,研習時才不致被少數視角所局限。」(109頁)在立法會答辯中,教育局甚至明言「傳統課本的方式處理通識科的學與教並非最佳的選擇」。當然,由教育局推出自願送審服務開始,業界便應該做好課程指引原則被推翻的準備,以至有一天「使用送審書教學」會變為最佳選擇。在筆者的前線經驗看來,通識相關書籍其實用得不少,但「教科書」則屬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究竟為何會有此結論,希望借《虛詞》這平台跟各愛書人分享一下。
教科書的更新頻率追不上議題變化
通識科與一般科目的最大不同,在於教學是議題為本;相對於傳統的科目由一個個固定課題結合成教學大綱(syllabus),通識科容讓教師透過選取不同議題作探究去滿足課程目標。所謂議題,課程指引的定義為「探究與自身、社會、國家、人類世界及物質環境有影響的當代議題」。以考評局的試題為例,2020年的議題便包括網絡成癮、國際移民、新聞自由、粵劇文化、中國民企及智慧城市等等。這些議題的更新速度是以年計,例如香港的新聞自由指數在2019年便大幅下降,網絡成癮中的遊戲障礙更是在2018年才進入國際疾病分類,智慧城市的科技例子更是日新月異。如果出版社須遵守教育局對教科書「五年不改版」的規定,則學生在2020學年所讀的便可能是2015年的資料。這在其他科目或者問題不大,但按通識科的標準而言,則是難以接受。即使出版商以參考書名義避過規定,因為修訂印刷甚至如今加入審批等程序,其更新速度絕對不足以支援前線教學需要。
教科書未能滿足通識科的閱讀目標
在當年教育改革中,通識科其實擔當重要角色。其中一個期望透過通識達致的目標,便是「從閱讀中學習」,用趙志成教授的說法,就是探究性閱讀:「 學生閱讀大量不同種類、性質和立場的資料,促進他們對閱讀內容作更深入的思考,瞭解文字背後的語意及所體現的意識形態,分析、綜合及評鑑有關內容,得出個人對該課題的見解。」教科書的優點,正正與上述目標大相逕庭;當作者只受限於兩三位,用字文法都以容易理解為主,在審書後甚至連部分立場都被刪去,學生在閱讀「教科書」時,根本不用作甚麼深入思考,更談不上甚麼個人見解;在教科書的運作邏輯中,每個課題都是重點,參考觀點就是雞精秘笈,所有問題亦有建議答案。這種閱讀,不單不能稱為探究,甚至連策略性閱讀都不是,極其量只是很淺層的有目的地閱讀,完全不符通識科原意。
教科書撰寫方式不符建構主義教學
上述兩項要求,不過是通識教學的入門。即使教師能定期更新教材以讓學生探究學習,如何有效率地組織閱讀材料,使學生能自主地有目的地建構知識、觀點以至立場,才是實踐通識科建構主義理念的關鍵。在課程指引中,「建構」一詞共出現了50次,當中絕大多數與「知識」搭配。在學理上,建構知識的概念源自建構主義,是種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及批評傳統被動接收教學的理論。這套理論在近年獲學界以至官方高度認可,通識科就被視為在教育界推動建構主義教學的試腳點。即使在本文未能深入解釋,相信各讀者亦不難明白教科書與建構主義不相容之處;傳統使用教科書的方式就是被動接收、以教師或書本內容為中心。所謂自主權甚至握在作者之手,不要說建構知識,學生連掌握知識也受限於教科書內容。狠一點說,如果建構主義是教學大趨勢,教科書的存在,根本就是開倒車。
教科書以單元為本不符考評局方針
一份能滿足建構主義、探究性閱讀及當代議題為本要求的通識教材,當然已是不可多得,但在香港讀書,最為重要還是能夠有效結合考評。這一點,也是教科書無可避免的短柄;即使近年各出版商已積極模仿公開試卷更新練習題,他們仍未能擺脫傳統教科書出版的知識為本模式;以六大單元知識作為分工,每本教科書內容只針對個別單元。但有趣的是,考評局自2012年起便是跨單元議題為本出題。若學生習慣以單元知識作分析框架,未能打破單元壁壘,融通不同單元概念作分析,將難以在考評中獲取高分。按單元出書的結構性問題,絕不可能透過一兩個跨單元練習或補充就可以解決。試想像,當學生在課堂教學中習慣知識為本的主題教學,然後做題目時就回歸議題為本,以分析資料或運用跨單元知識作分析,相信只會感到無所適從,具資質者甚至早早看穿教科書根本無用,影響課堂的投入度。
倚重教科書的通識雖然會百病叢生,但通識卻不能脫離閱讀,不可脫離書本。在筆者備課或製作教材時,政府機關、公民社會及各大媒體的文章及報導,依然是重要的取材來源。若政權要審查媒體及互聯網,對通識的傷害將遠遠比審書大得多。可是,筆者也必須坦言,雖然身後的書櫃放滿近百本通識相關書籍,但大多都是用作豐富個人知識,以及判斷不同議題及討論的重要性及優次,直接用於教學的則寥寥可數。箇中原因,除了是書籍的文字始終太多而學生難以吸收,技術上要搜尋書本內容並轉載於教材,亦屬一大難題。教筆者無奈的是,當網上閱覧報刊已成主流之際,本地中文電子書卻仍處於萌芽階段,不少筆者期待的2020年新書,還是只有印刷版。即使前線教師還是可以透過參考書目及圖書館推介書單等途徑,鼓勵學生閱讀實體書,但最直接影響學生的,還是如教科書般能直接用於課堂的讀物。
各位作者及出版商應該可以想像,如果有一天,書籍可透過如Netflix般的系統,以學校名義訂閱及讓師生自由閱覽及抽取內容,出版界的生態及師生的閱讀風氣,或許就不再一樣。那個時候,所謂教科書,也會正式成為如幻燈片般的歷史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