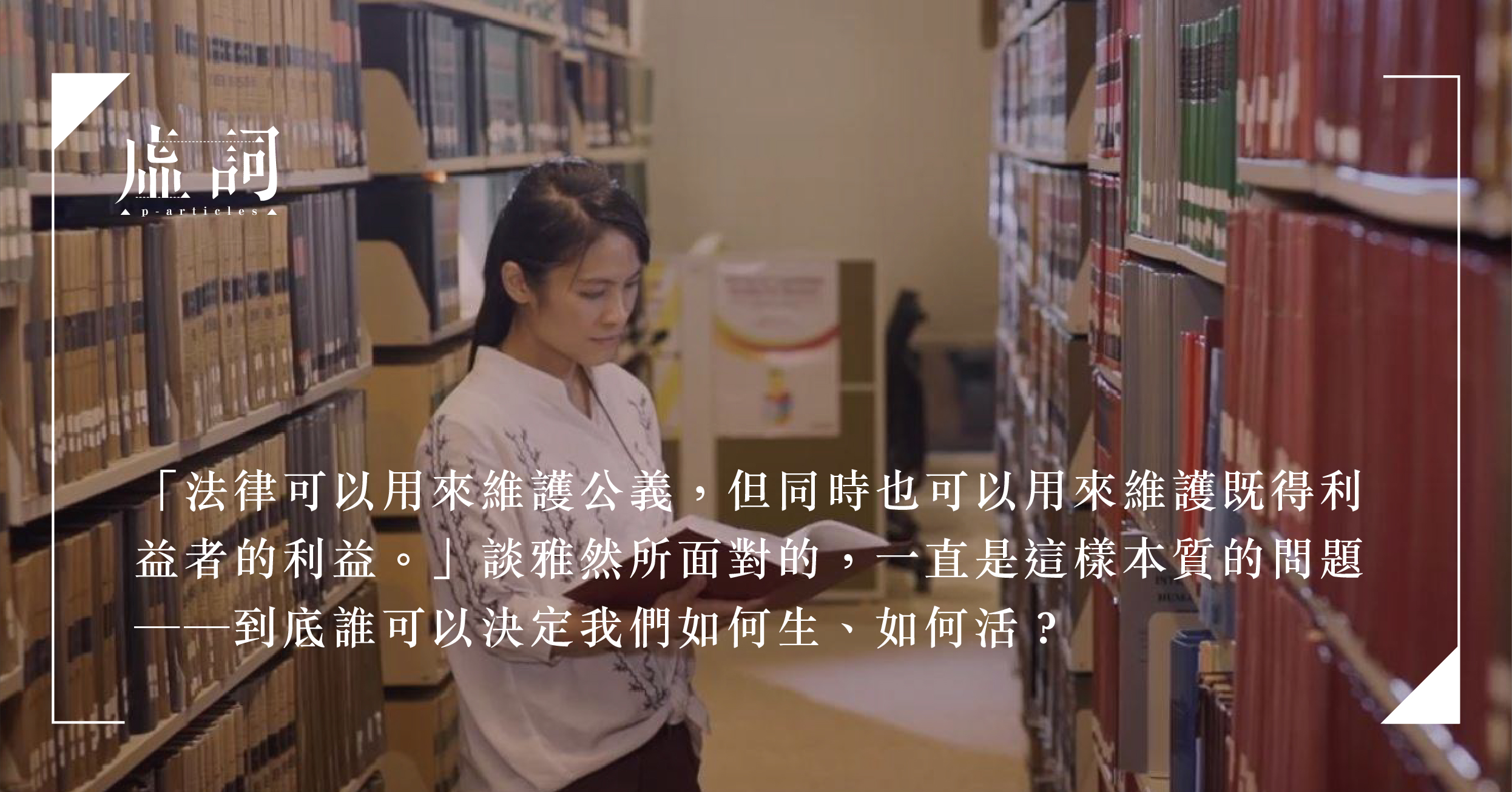【現身說法】踏上這無盡旅途:居港權抗爭廿年
現身說法 | by 虛詞編輯部 | 2019-04-05
還記得談雅然嗎?2001年7月20日,這位生於大陸而遭遺棄、最後被港人領養的孩子,得到終審法院一紙敗訴,面臨遭遣返內地、與家人分離的絕望處境。當時談雅然不僅面對入境處的遣返警告,更受媒體與公眾輿論的猛烈追擊,連自己是養女的事實,她都是從《明報》記者口中才得知的。成年人尚且未必能承受這樣的壓力,何況當年談雅然只是個十二三歲的中學少女,箇中滋味是難以想象。
轉眼二十年過去了,如今談雅然已從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畢業,著力於動物法律研究,又前往英國進修政治哲學。命運在她身上急轉彎好幾次,年少時的波折經歷,也讓她對法律和命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這幾年的法律學習,令我深深體會到法律的限制,雖然它是一個很強大的工具,可以用來維護公義,但它同時也可以用來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她所面對的,一直是這樣本質的問題——到底是誰可以決定我們如何生、如何活?
生活是,一啖砂糖一啖屎
1999年1月29日,「吳嘉玲案」[1] 宣判,香港終審法院指出「所有香港永久居民在中國內地所生子女,不論有否單程證,不論婚生或非婚生,不論出生時父或母是否已經成為香港居民,均擁有居港權」,不少分隔兩地的家庭都重燃希望 。然而不久後,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表示,這樣的政策估計導致十年內有一百六十七萬人內地人士移居香港,為社會帶來沉重人口壓力。這個說法引起了巨大的社會爭議,之後更出現了第一次人大釋法,居港權政策緊縮,大量家庭團聚幻夢破滅。
悲劇,就是把美好的事情毀滅給你看。在李維怡的短篇小說〈一啖砂糖〉中,安琦一家不正是面對類似的遭遇?故事中還在讀小學的安琦隨父母來港生活,但因政策之故,親生哥哥卻要隻身留在大陸,逢大時大節才能短暫來港,多數時間還都在居港權運動現場抗爭。政府的見利忘義,使得原本得以安生的家庭,如今卻要像坐過山車般,乞討一家團聚的權利。李維怡說「一啖砂糖」,之後還未說破的,不就是政府繼而給出的、「一啖屎」那樣的騙局麼?
於個人而言,時代的創傷更是難以抹去。小說中的哥哥安國長大後不嗜甜,可能就是因早年與家人分開的時候「被五姨拉著,在月台上飲泣,表姐阿霞為安慰他,把一塊糖餅乾放在他嘴巴前面,大哥不肯吃,表姐便把糖餅乾弄成一小塊一小塊,一口一口地餵他。安國的嘴巴便塞滿了口水眼淚鼻涕和餅乾碎。」甜,於他而言就是痛苦的滋味。而現實中,那張因敗訴而痛哭的相片裡,談雅然與父母絕望的神情,我們至今還記得。
(2001年談雅然居港權案敗訴後。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居住魔咒:不存在的香港人
2019年,居港權抗爭進入第二十個年頭。1月13日,一直關注弱勢群體的甘浩望神父再次於政府總部外絕食抗議,因的還是港人子女的居留問題,卻已鮮有媒體報導。其實早在九年前,甘神父就因此事進行一次絕食行動,當時政府承諾於2011年容許合資格「超齡子女」(即其親生父母於獲身份證時,該子女未達十四歲)申請單程證,然而這麼多年過去了,這些家庭內部可能已發生很大變化,但面前那道政策的鐵閘,還依然堅固不破地豎在那裡。雪上加霜的是,因著日益累積的中港矛盾、更多政治事件爆發,這群無法歸家的人,已從媒體視線中淡出,真正成了不存在的隱形人。
在居港權的問題中,有太多限制、太多荒謬,不能盡數。廖偉棠的詩〈荃灣,石圍角村〉,寫的是無法留在香港的母親(未獲得單程證期間,丈夫去世了,而根據政策她不能申請來港照顧年幼無依的兒子),充滿辛酸:
「石圍角村寂靜至極,老人們點頭說笑依舊,
不存在的女人鼓起了空氣,空氣粗糲
足以傷害一切——首先傷害自身。
現在是丈夫的幽靈仍然為她向空氣申請……
申請一把火、一片好柴、一張舊報上
滿載的升平……」
唯一能幫助那位無助母親的,只有她不存在的丈夫,而他仍得透過不斷地申請、申請、申請,仿佛生和死都得在居住權的魔咒中循環往復,讀起來都是字字錐心。
如此看來,談雅然雖然不幸,但也是幸運的。在居港權爭議風口浪尖時爆發,她的個案受到矚目(儘管中間也因此經歷了被人誤解、上訴失敗),但最終還是得到了居港身份,如當年李白在被流放的路上突然得悉獲釋,回頭看則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但還有多少死別生離還在發生?沒有忘記,不能忘記,看不見的他們仍在邊緣掙扎時發出的呼喊聲。
[1] 吳嘉玲於1997年7月初來港,其來港方式在法律修訂前並非違反偷渡罪行,但在經修訂後,她的行為被後來的法律追溯成為犯罪。
(香港電台及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聯合製作的電視節目《現身說法》,將於3月24日起,逢星期日晚上8:30在港台電視31及31A播映;於3月27日起,逢星期三晚上6:00在無綫電視翡翠台播映;港台網站tv.rthk.hk及流動程式RTHK Screen視像直播及提供節目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