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完結了嗎?——「六四:小說與大說,香港與中國」座談會紀錄
報導 | by 賴展堂 | 2021-06-24
1989年,香港首次發生人數過百萬的遊行,聲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六四事件的三十週年,過百萬人上街的景象再度出現——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綿延百日未見止息。適逢中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在九月舉辦「六四:小說與大說,香港與中國」座談會,邀請了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黃念欣以及歷史系副教授何曉清,分享她們各自從文學和歷史、香港和中國出發的六四研究。活動開始之際,主持人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特意解釋,這次座談會早在一年半前已構思,而非因應當下運動而來;但在當下多角度地回顧六四,不僅是對事件本身的分析,更有助我們思考香港的局勢。
六四歷史內外
何曉清是六四的同代人,當年還是個廣州的中學生,參與了省港澳大遊行。後來她到加拿大升學,到哈佛大學任教,一直在他方進行六四的歷史研究與教學。發言一開始,她表示這次的座談會對她說具有特殊意義,因為這是她二十年來,第一次可以在靠近中國大陸的地方談論這個話題。
何曉清首先敘述了鎮壓當夜的兩個片段。6月3日晚,軍隊逐漸逼近,廣場上已有覺悟犧牲性命的學生齊聲宣誓:「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只有一個人。」血腥清場隨即發生。另一片段,是劉曉波折斷廣場外運來的槍械。面對軍隊開火,一些憤怒的工人極力說服學生武力抗爭,劉曉波最後仍堅持和平的立場。「我認為這是一個象徵性的時刻。很多人後來質問劉曉波為什麼要這樣做⋯⋯如果學生開了一槍,中共便會立刻把學生標籤為『暴徒』,來合理化那些坐擁AK-47和坦克的20萬戒嚴部隊的行為。這是劉曉波在1989年的決定。我們知道這最後沒有起作用,但仍很值得我們思考。」
她列舉當年學生的七項訴求,釐清運動的性質。4月22日,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臺階上,高舉請願信,可見天安門事件並不是意在推翻政權的「革命」,而是儒家傳統下的體制改良,祈求統治者聆聽意見。而運動的升級有三個節點。4月19日,學生在新華門前聚集要求對話,最終被警察毆打流血。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引發學生以至廣泛民眾的怨情,翌日便發生「四二七大遊行」,給予學生擴大規模的信心。第三個轉捩點是5月13日 ,學生開始絕食,感召全民參與。運動的主體不僅是學生和知識份子,亦包括大量上街保護年輕人的平民百姓。
運動中有力量的團結,也有令人遺憾的爭議。5月23日,天安門城樓上的毛澤東像被潑墨,余志堅、喻東岳、魯德成的這個行動沒能得到學生的信任。何曉清形容三人為1989年版本不獲諒解的「勇武」,最終被學生「捉鬼」送交公安。三人的下半生從此摧毀。何曉清後來聯絡上出獄後輾轉偷渡美國的余志堅和喻東岳。喻東岳服刑16年備受折磨,精神失常,出獄後只懂喃喃自語「不要打我」,但當何曉清問他最想在哪裏生活,他清楚回答「我想回大陸」。一直照顧喻東岳的余志堅在去年過世,何曉清說,「這是我第一次看見一副紙棺材……只是因為當年的一個舉動,他們的人生便要落得如此下場。」
何曉清指出中國政府透過操控傳媒和教育,製造謠言混淆真相。六四鎮壓當晚,央視主播杜憲與薛飛報導時身穿黑衣,神色悲傷,隨即遭到封殺。中國政府剝奪新聞自主權,以此創造另一版本的六四敘事,例如官方英文周刊Beijing Review當年九月刊出社論“Rumours and the Truth”,指控西方、香港、台灣的媒體共同「發明」了天安門事件。「愛國主義教育」也是中國政府在六四後設立的意識形態宣傳政策。
今年是何曉清第一年到中文大學任教,迎頭遇上反修例運動。眼見局勢緊張,在她來香港前,很多人都問她為何還作如此決定。她回顧了反右、文革、六四中知識分子的慘痛經驗,「作為一個研究現當代中國的歷史學家,我不會天真到以為一切都會迎刃而解……但香港人令我感覺有希望。」在發言中,她特意分享了李蘭菊的倖存故事。李蘭菊是當年前往北京支援學運的香港學聯成員,六四當夜親眼目睹嚴重死傷,北京人堅持要她先上救護車,一名女醫生握著她的手哭著說:「孩子,我們要你平安回到香港,告訴全世界我們的政府對我們做了什麼。」她又透露了其書Tiananmen Exiles: Voices of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的製作過程:由於學術出版預算有限,這本書原本並無封面設計,但一個香港記者免費提供了照片給她,也就是現在我們在書上看到的維園燭光晚會。香港反修例運動與天安門事件亦有相似象徵:連儂牆讓她想起西單民主牆等地的大字報;中大的民主女神像,當年在天安門也有一尊。她回憶在血腥鎮壓翌日,她戴著黑臂紗上學,最終被老師勸說脱了下來;現在換她成為大人,再度遇上一場運動,她會是支持學生的那個人。「天安門事件不但關於鎮壓,更是關於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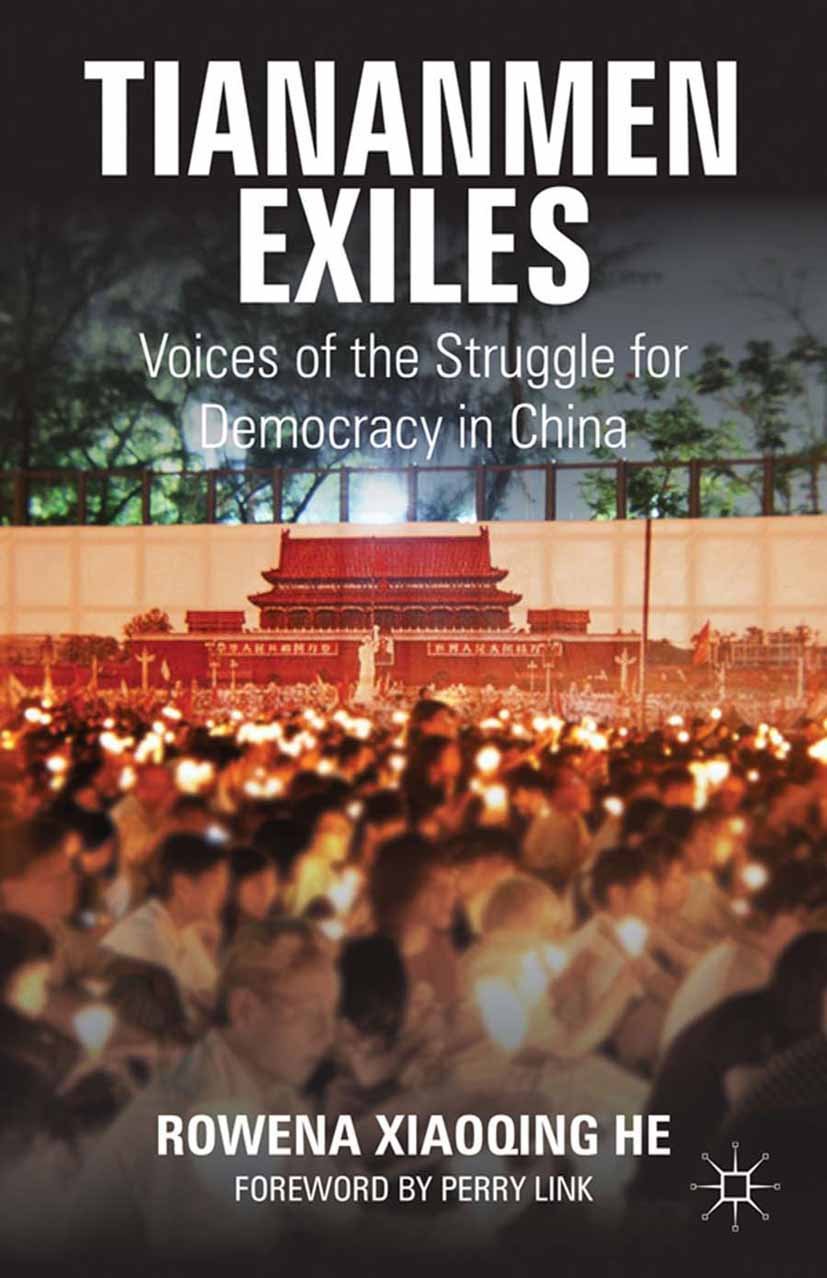
未說完的六四故事
黃念欣自言,她的開場白也許並不恰當。她引用了齊澤克(Slavoj
Žižek)《歡迎光臨真實荒漠》(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中一則共產時代的笑話:
一個東德人在西伯利亞找到工作,他知道從當地寫信回國必定會遭到審查,於是告訴朋友:「我們來制訂一套密碼:如果我的信是以藍墨水寫的,信裡寫的便是真的;如果是用紅墨水寫的,信裡寫的便是假的。」一個月後,朋友收到他的第一封來信,用的是藍墨水:「這裡的一切都好極了:店裡貨品充足,房子又大又暖,電影院放映的都是西片,還有很多漂亮女孩等著你――唯一找不到的是紅墨水。」
齊澤克分析,「沒有紅墨水」這一聲稱所揭露的,不僅是極權主義的審查,更可以是更完善的自由主義審查:我們擁有各種「自由」,唯獨欠缺了「紅墨水」——那表達「不自由」(unfreedom)的語言。黃念欣把這種狀況類比為香港在六四上的文學生產,嚴肅悲情的「藍墨水」塑造了對六四的正統視角,例如香港作家協會編的《作家的吶喊:一九八九中國學運文選》中的哀悼與控訴。但如果我們追求更深入的理解,便有需要去發掘、審視那些未必符合上述論述型態的「紅墨水」。
她正在修訂的書稿《六四印象:香港文學的七種自由想像》涉及過百篇提及六四的香港文學作品,整理出七種關於「自由」的經驗與想像。不同於立場清晰的主流論述,這些文學作品不少是虛構的、個人化的,甚至帶有道德瑕疵。它們未必像歷史寫作般負擔起事實與真相的責任,但正是其含混複雜,能夠引領我們更全面地認識天安門事件的記憶與情感。
她的第一個個案是李碧華在1990年1月出版、快速回應了六四的《天安門舊魄新魂》。書中收錄的短篇小說〈失物在長安街〉裏,在六四死去的「新魂」遇上在1976年四五運動中死去的「舊魄」,六四「新魂」最終在長安街上找回自己的腦漿。李碧華大膽運用靈異此一「虛假」的文類,以因果報應的迷信觀念,影射當代中國的殘酷歷史。
第二個個案是陳寶珣的《發給每個閉塞腦袋幾顆理性子彈》(1990)。香港文學的六四論述,包含了一種未曾真正在場的局外人式的遺憾,但當時在北京擔任記者的陳寶珣在小說中採用了北京當權者的角度,以幹部之子為主角。他在天安門事件時身處巴黎,極遺憾無法親歷「那些能牽動一個嚴格要求純粹情感的心靈的,生死之間的種種激昂事蹟」,當中不無諷刺,卻也投射了香港人想成為「局內人」的慾望。
第三個個案是黃碧雲的〈中國之戀〉(1990)。這篇小說在六四剛發生不久寫對中國的情結,顯然是非主流的。故事中,香港女大學生葉丹傾慕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于光華,並投身社會運動。今天可能仍有人會藉浪漫與愛情質疑革命的純粹性,其實即使不引用「革命加戀愛」這個長久以來的公式,戀愛不僅不構成革命的雜質,更時有超越與昇華革命的可能。
第四個個案是陳冠中《什麼都沒有發生》(1999)。主角張得志致力不讓情緒打擾生活,他對六四的漠不關心甚至激怒了英國老闆托圖,並說自己最受不了「酸的饅頭」(sentimental)。他的反傷感主義,引發我們重思香港人面對六四的理智與感情。另一個案是辛其氏的《紅格子酒舖》(1994)。小說裏中年女性角色追憶青春,例如曾是保釣份子的葉萍在六四大遊行遇上一貫政治消極的舊友立梅,在歷史大事的背景下鋪開心結,為六四經驗提供了更為個人化、日常的抒情視角。
最後兩個案例來自大眾文學,亦舒《傷城記》(1990)和林燕妮《為我而生》(1990)。《傷城記》中的愛情帶有物質主義色彩,女主角苦惱應否應否賣掉港島區三層大屋然後嫁到外國,反映了六四後香港移民潮裏上層階級的心理掙扎。林燕妮的《為愛而生》用更戲劇化的方式來寫六四:香港年輕女首富與候選美國總統的情人,聯手從北京營救學運領袖。小說結局王丹成功逃到美國,在CNN上澄清自己的真實身分,指「獄中的王丹並不是我,共產黨專政政府濫捕無辜。我們要求放人」。現實中,王丹1989年被捕後反覆進出監獄,直到1998年才流亡美國。
《為我而生》情節安排的爭議,與上述靈異、諷刺、迷戀、犬儒、個人化的文本同是「紅墨水」,忽視它們的存在會導致文學自由(literary freedom)的匱乏。黃念欣同意,文學並非進入事實的最好方法,然而,小說儘管是虛構的,當中蘊含的情緒卻十分真實。作為知名作家的亦舒和林燕妮的這兩部作品,甚少在六四的脈絡下被討論,也許因為它們帶出了某種「不願面對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亦舒工於現實計算的感情觀念、林燕妮的天真理想,都難容於六四的主流論述。當香港享有這麼多自由去討論六四,相關的文學論述可惜未見多元。在香港,儘管史實已經清晰可及,但對六四的情緒仍未得到完整抒發,當中的複雜層次,仍有待我們進一步梳理。

(左起)何曉清、彭麗君、黃念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