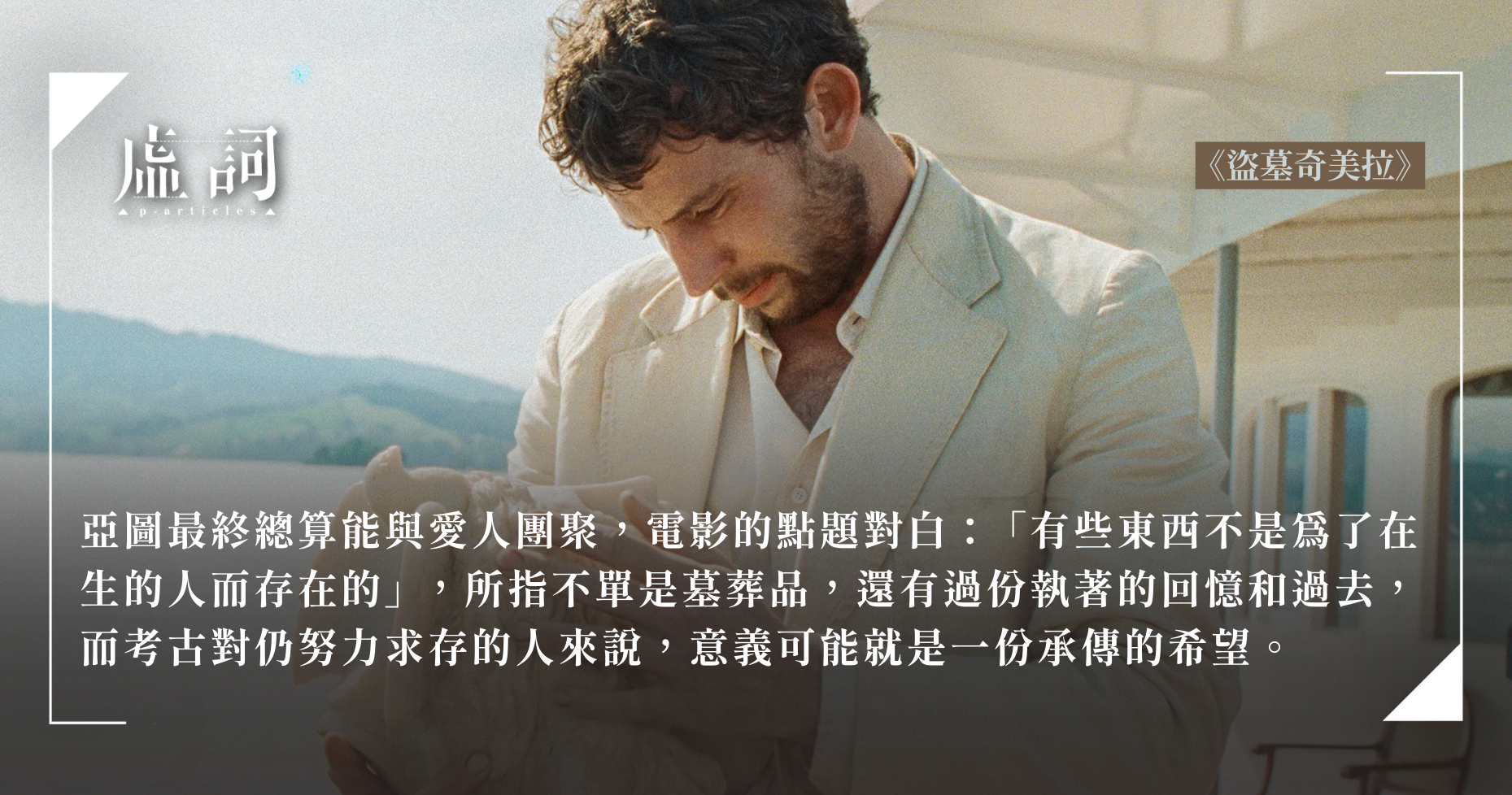去年全球首映的《盜墓奇美拉》入選金棕櫚獎主競賽單元,首映場獲得全場9分鐘起立致敬。藝術家黃嘉瀛有見香港坊間影評多論述電影中的虛實、生死意象或拍攝手法,鮮有談及貫穿整條故事線的伊特魯里亞(Etruscan)古文明及其象徵意義,故撰此文,深入分析導演置放的劇情設計的用心,以及介紹一些歷史文物如萬獸女神像、躺臥餐廳墓的壁畫、伊特魯里亞銅鏡等等。 (閱讀更多)
《汪汪夢裡人》:你是我想像的假幻
影評 | by 吳騫桐 | 2024-08-14
吳騫桐從《汪汪夢裡人》的原著漫畫作對讀,發現電影導演帕布貝加(Pablo Berger)和原著作者莎拉華倫(Sara Varon)皆從片段的個人經歷中想像紐約街頭和大都會景觀。媒介一定影響改編,填塞電影佈景的過千名配角供讀者自由穿過、想像,拓墾了主線籬外的敘述空間,而吳騫桐認為動畫的疤痕深了許多,導演把或友情或愛情的「關係」扻爛得徹徹底底。相比繪本,夢與現實的界線在動畫中更顯模糊,吳騫桐覺得「夢」作為內在世界的某種真實,或就是「人與人關係」的終極呈現,你是我想像的假幻,所以那些逝去的是否真的存在、回憶是否虛構、September的承諾有無兌現,也罷,現實不留痕。 (閱讀更多)
《Robot Dreams》:一再被時間所欺,但我們還將毫無保留地到來。
嚴瑋擇看《汪汪夢裡人》,想起狹義相對論中的雙生悖論,以及愛恩斯坦給貝索家人的哀悼信,當中寫著:「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的分別,不過是持久而頑固的幻覺。」機械人和狗先生都想著回去過去的時間,最後無法再聚,因為他們其實不曾共享過同一個時間,他們對時間的體感經驗不過是事件的接續發生,是物體的運動,這一切只是意識帶來的錯覺。然而,他指出過去與現在與未來並無區別,不過是我們為人的限制無法越過時間,但我們所經歷或未經歷的一切歷史與感受,早已超越我們,一切從未流逝。此世可遇見,往後日子可偶爾想起,已是萬幸。 (閱讀更多)
在聒噪的城市裡重覓內心──談《無聲絕境外傳:首襲日》的壓抑與反抗
影評 | by 浮海 | 2024-08-05
獨立電影出身的Michael Sarnoski執導的末日幻想恐怖片《無聲絕境外傳:首襲日》早前上映,浮海認為戲裡戲外的寂靜無聲是一面鏡子,教人掂量著聲音與沉默的重量。他從精神分析理論說起,作為「他者」的怪物,可視為壓抑之物的反撲,而電影探討了聲音如何是個人與世界的橋樑,形成傷痛的共同體。同時, 他也指出聲音的力量不僅在於發聲,也在於靜謐,即使面對著把人「滅聲」的外星威權,人們尚能找到各種契機釋放自身的傷痛。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