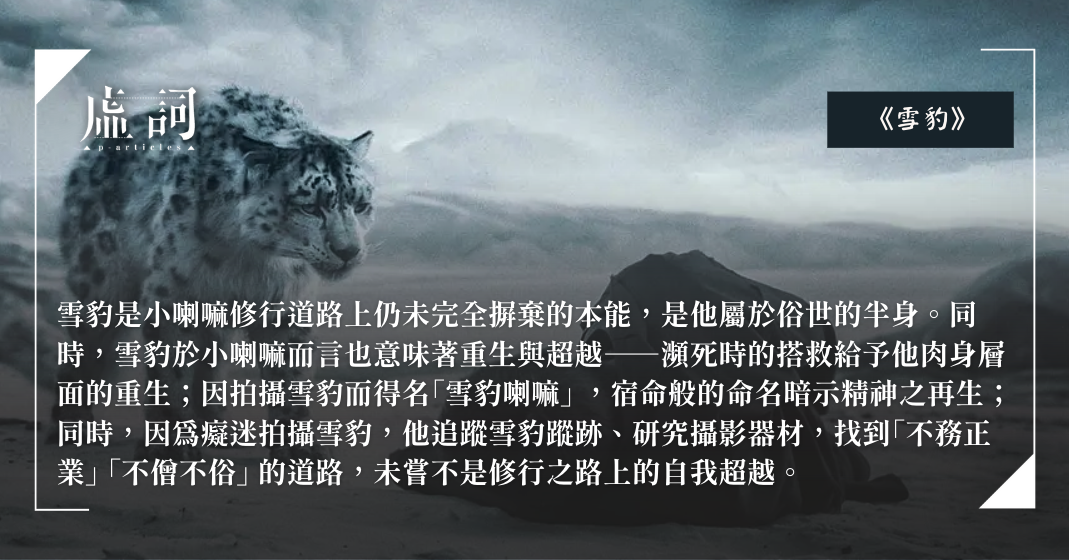在豹眼中相逢:觀萬瑪才旦《雪豹》
影評 | by 小煬 | 2024-04-10
都道「管中窺豹,可見一斑」,萬瑪才旦遺作《雪豹》反其道而行,以豹眼窺人,以動物視點揭開人類社會的假面,照見人無法自視的盲點。在國際版海報中,「雪豹喇嘛」位於畫面左下角,於羊圈中抬頭仰望巨大雪豹。 中心與角落、巨大與微小之對比,已暗示誰才是電影的「主角」。大陸版海報折射出人物與動物的關係:側身的喇嘛於雪豹身體留下剪影,雪豹的臉亦有一半被另一男性側影遮擋。 人與雪豹之間究竟是遮擋、阻礙,還是重疊、共生?人臉讓位給雪豹——它凝神直視所有觀眾——當你看我時,我也看著你。

(圖1 國際版海報 圖源「豆瓣電影」)

(圖2 中國大陸版海報 圖源「豆瓣電影」)
《雪豹》的情節並不複雜:雪豹闖入牧民金巴的羊圈,咬死了九只羯羊。青海州立電視台得知消息後,派出工作人員前往金巴家中採訪。金巴的弟弟「雪豹喇嘛」跟隨電視台一行回家。父親和弟弟想要放走雪豹,而金巴不肯。由於雪豹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和森林公安隨之介入此事。爭執過後,金巴不得不放走雪豹。
萬瑪才旦出生於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下轄的村子,該村的生產方式是半農半牧,人跟動物的關係十分密切。生長環境使然,他的作品中從不乏動物意象。(註3)《老狗》(2011)以藏獒喻藏文化的當代處境;羊在《塔洛》(2015)中是牧羊人的陪伴與寄託,在《撞死了一只羊》(2018)中則意味著救贖與慈悲;《氣球》(2019)以母羊映照女性人物卓嘎的生育困境。《雪豹》無疑延續了導演的動物書寫,但指涉更加複雜。
《雪豹》的故事由雪豹與小喇嘛的三次相遇串連。雪豹跳入羊圈捕食,被抓住倒吊鞭打。弟弟支開眾人,放走了雪豹。他對雪豹說:「我就要出家了。我放你自由,走吧。」弟弟仿佛是在提前扮演喇嘛,向雪豹施以慈悲。他放走雪豹,與之相望的時刻,是神聖的——令雪豹得以重生的善意,也是他修行之路的起始。再次相遇時,「雪豹喇嘛」於茫茫雪山間迷路瀕死,他決心效仿佛祖以身伺豹,完成自己在世上最後的施捨。然而,雪豹卻記得並認出了他,俯下身子把他馱下山,報答了救命之恩。第三次相遇不再只關乎人與動物,動物保護制度及其所代表的系統介入,擾動了深植於當地的兩種邏輯——弱肉強食(自然法則)和因果業報(宗教倫理)。三次相遇中,雪豹展現出不同樣貌——兇獸、「神使」、困獸、一級保護動物。然而,雪豹始終是同一頭雪豹,不過是因為與人的關係有所變化,便被定義為不同角色。變了的是人,是時代,而非雪豹。
無人注意時,小喇嘛進入羊圈,與雪豹對望。二者分位畫面左右,中間是倒地的死羊。圖像隱喻了生與死、獸性與神性的對立轉化。之後一組特寫鏡頭震人心魄,由小喇嘛的眼球(他眼中映照出雪豹)切換至雪豹的眼球(它眼中是小喇嘛的身影)——原來,我們看向動物時,動物也看向我們;而我們所凝視的,終究是自己。約翰·伯格(John Berger)曾如此評論動物的眼神:「只有人類才能在動物的眼神中體會到這種熟悉感。其他的動物會被這樣的眼神所震懾,人類則在回應這眼神時體認到了自身的存在。」(註4)那麼,「雪豹」到底指向什麼?或者說,我們通過雪豹之眼看到了怎樣的自己?鞏傑認為,萬瑪才旦作品中的動物「呼應著人性中獸性和神性的兩極紛爭,以及靈與肉、理想與現實的衝突。」(註5)這一點在《雪豹》中仍然有跡可循。
雪豹是本能與人慾的化身。小喇嘛一家同電視台一行圍坐觀看雪豹紀錄片。雪豹於懸崖峭壁間追逐岩羊,展露捕食者天性。鏡頭搖過,小喇嘛的眼神隨著雪豹跳躍而激動興奮,洩漏出與年紀相符的天真。當岩羊逃脫時,小喇嘛復歸平靜。固然,那種平靜可以是慈悲,可也像是期待落空後的興味索然。第二段紀錄片講述雪豹如何發情求偶,小喇嘛的眼神隨之閃爍。可以說,雪豹是小喇嘛修行道路上仍未完全摒棄的本能,是他屬於俗世的半身。同時,雪豹於小喇嘛而言也意味著重生與超越——瀕死時的搭救給予他肉身層面的重生;因拍攝雪豹而得名「雪豹喇嘛」,宿命般的命名暗示精神之再生;同時,因為癡迷拍攝雪豹,他追蹤雪豹蹤跡、研究攝影器材,找到「不務正業」「不僧不俗」 的道路,未嘗不是修行之路上的自我超越。
雪豹同樣也是金巴的投影。金巴暴躁易怒,面對採訪鏡頭從不收斂,仿佛隨時可能失控,與雪豹帶來的威脅相似。他的行為依循著樸素乃至粗暴的自然邏輯——弱肉強食沒錯,那麼他報復雪豹也沒錯。如果要放生雪豹,必須先賠償他的損失。慈悲無法說服他,制度也難以嚇退他,倔強不馴如雪豹。最終,他被摁倒在地,處境一如被鐵絲圍困的雪豹。如果說雪豹於小喇嘛而言,意味著神性與人性的對立轉化;那麼,金巴便是雪豹野獸之心的具現。
就雪豹、小喇嘛、金巴三者而言,很難說誰是誰的隱喻,誰是誰的鏡像。他們兩兩之間各有因果(金巴和雪豹有仇,小喇嘛和雪豹有恩),各有相似的特質或處境,在一次次相逢中對立、交疊、轉化。當我們把鏡頭拉遠,雪豹又成為藏人及藏地文化的轉喻:在深植於此地的自然法則與宗教文化之外,又有了現代價值與制度介入。於是,事情變得複雜起來,雪豹也無法只是雪豹。
萬瑪才旦作為「藏地新浪潮」旗手,總是情迷藏地。他坦言:「之前看一些藏族題材的電影,我會覺得很假,於是就想自己拍一部。」(註6)藏族影人大多不滿於藏族題材影片中長期存在的僵化、失真、神秘化等問題。(註7)萬瑪才旦擯棄宏大敘事,聚焦個體命運,(註8)以「自己人」的經驗扭轉他者視角。《雪豹》當然滿載萬瑪才旦對於藏地的深情厚愛,雪山、雪豹、宗教氛圍,都為電影打下地方烙印。然而,《雪豹》同時也抹去了地方——這個故事是藏地的故事,但也可以是其他地方的故事,可以讓藏文化圈以外的觀眾瞭解接受。從《雪豹》看藏人,會發現他們和我們一樣,「一樣經受著時代衝擊,一樣帶著焦灼與期待。」 (註9)
最後,讓我們把鏡頭推近,回到小喇嘛和雪豹對望的場景。在彼此眼中,人與豹跨過物種與生死的界線,一次次相逢。於是可以相信,那如雪豹般遠去的萬瑪才旦,也終會在某雙眼或某次對望中與我們重逢。
註:
見「豆瓣電影」,網址:https://movie.douban.com/photos/photo/2900144976/,訪問日期2024年4月2日。
見「豆瓣電影」,網址:https://movie.douban.com/photos/photo/2905869907/,訪問日期2024年4月2日。
萬瑪才旦、白睿文:〈像一陣風,留下絕唱〉,《讀書》,2023年第8期,頁42-43。
約翰・伯格著,劉惠媛譯:《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4。
鞏傑:〈解讀「藏地密碼」:當下藏地電影空間文化審美共同體建構闡釋〉,《當代電影》,2019年第11期,頁8。
萬瑪才旦、徐楓:〈萬瑪才旦:藏文化與現代化並非二元對立〉,《當代電影》,2017年第1期,頁43。
李一君、達娃卓瑪:〈「少數」的言說:中國安多地區藏族青年的電影生產與文化表述〉,《新聞學研究》,總第155期,2023年4月,頁132-133。
蔣東升:〈新世紀以來中國藏族題材電影敘事範式變奏〉,《電影文學》,2018年第12期,頁18。
王海洲、嚴文軍:〈民族身份與文化蹤跡:百年影史中的萬瑪才旦〉,《電影新作》,2023年第4期,頁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