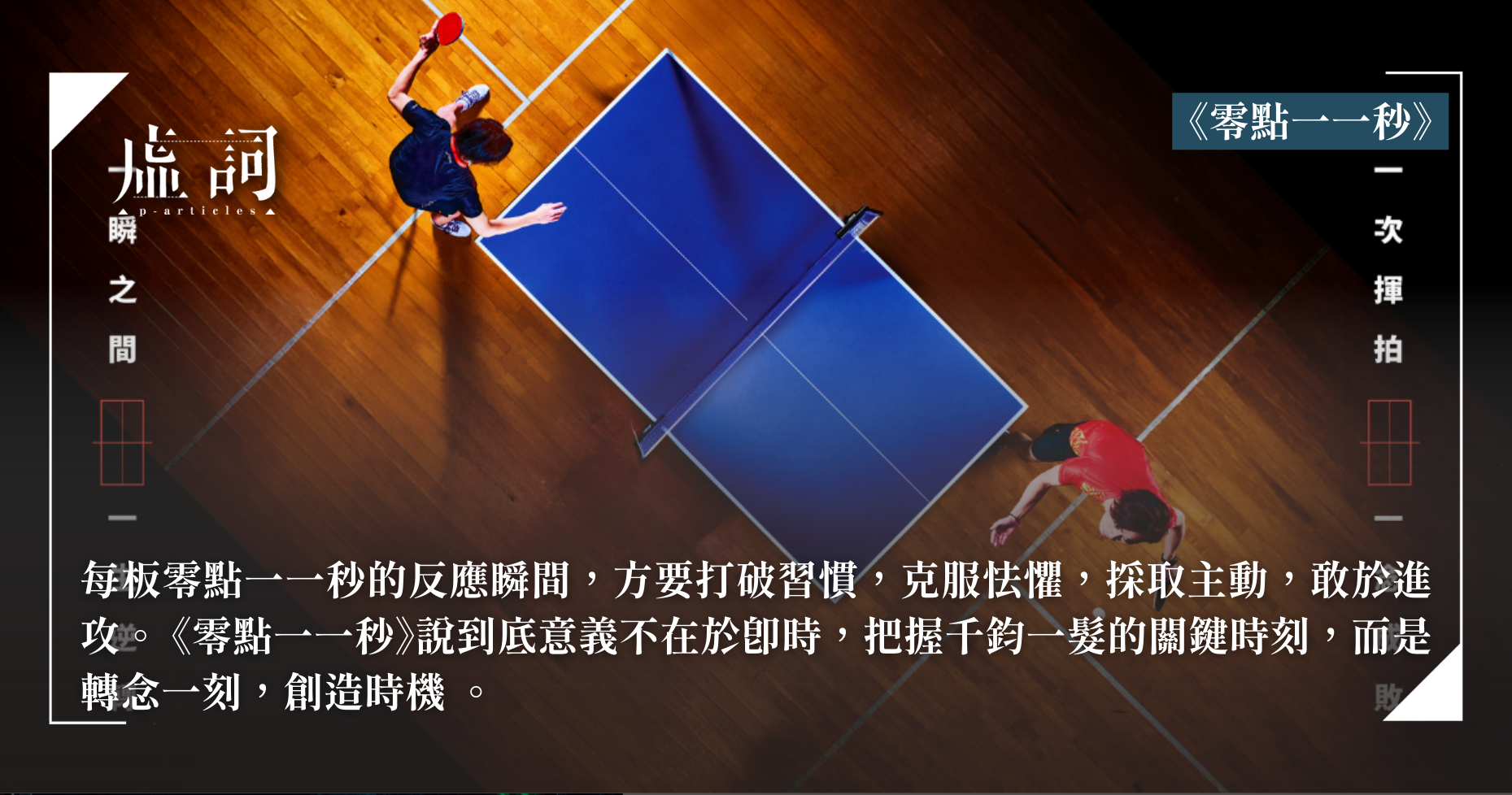《都是她的錯》:到底是誰的錯?
劇評 | by 葉紫婷 | 2026-01-16
葉紫婷傳來《都是她的錯》(All Her Fault)劇評,指其作為2025年年度黑馬的神劇,劇本對角色性格刻畫相當細膩,探討犯案動機、家庭羈絆及愛恨交織,尤其從女性視角剖析社會壓力與責任推卸。葉紫婷認為劇名中的「她」所指涉的既是主角Marissa面對丈夫Peter以理性包裝的責難,又是保姆Carrie悲劇的身世,劇集赤裸裸展現出女性在母職、婚姻與自我間的掙扎。 (閱讀更多)
走或等待並非被動的選擇——評鄧樹榮《等待果陀》舞台劇
劇評 | by 譚嘉琪 | 2026-01-15
在2025年末時,譚嘉琪觀賞了鄧樹榮執導《等待果陀》舞台劇,讚揚此作忠實翻譯原作結構,亦融入本土流行用語與俗語等,既拉近港人與Samuel Beckett的距離,也營造專屬香港的表演形式。譚嘉琪指出「等待」作為劇作的核心,戈戈與狄狄在走與等之間看似有,又沒有選擇權,但其實出選擇的前提是自己如何看待「果陀」的價值,全憑觀眾去定義和解讀。 (閱讀更多)
粵劇《夢斷香銷四十年》:簡單就是美
劇評 | by 何曉旻 | 2026-01-14
何曉旻傳來慶昇平粵劇團主辦、梁振文與王潔清主演的《夢斷香銷四十年》版本,指出演員演繹細膩,唱做俱佳,更將陸游與唐琬的淒美愛情展現得淋漓盡致。全劇雖僅有五場戲,但其劇情簡潔直接,聚焦愛情遺憾,呈現「簡單就是美」的美學。同時,劇組透過獨特的幕後伴唱和音樂設計,營造出沉浸式的聽覺盛宴。劇目只有三小時,劇中人物卻歷盡四十年的悲歡離合,亦喚起何曉旻對自身往事與時代變遷的感慨。 (閱讀更多)
疫後的靜止與流動——舞台劇《我在隔離房⋯⋯》
劇評 | by 吳沚盈 | 2025-12-18
吳沚盈傳來舞台劇《我在隔離房⋯⋯》劇評,指出劇作雖以荒誕喜劇包裝,實則是一部刻畫都市孤獨與生存掙扎的悲喜劇。劇中兩位主角阿俊與廚娘陳三妹,透過投訴信與一碗白粥,在物理隔絕下建立起心靈連結,互相救贖彼此的「三十歲危機」。吳沚盈回望劇名「隔離」在粵語中既指「分離」亦指「隔壁」的雙重隱喻,呼應著疫後的靜止與流動。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