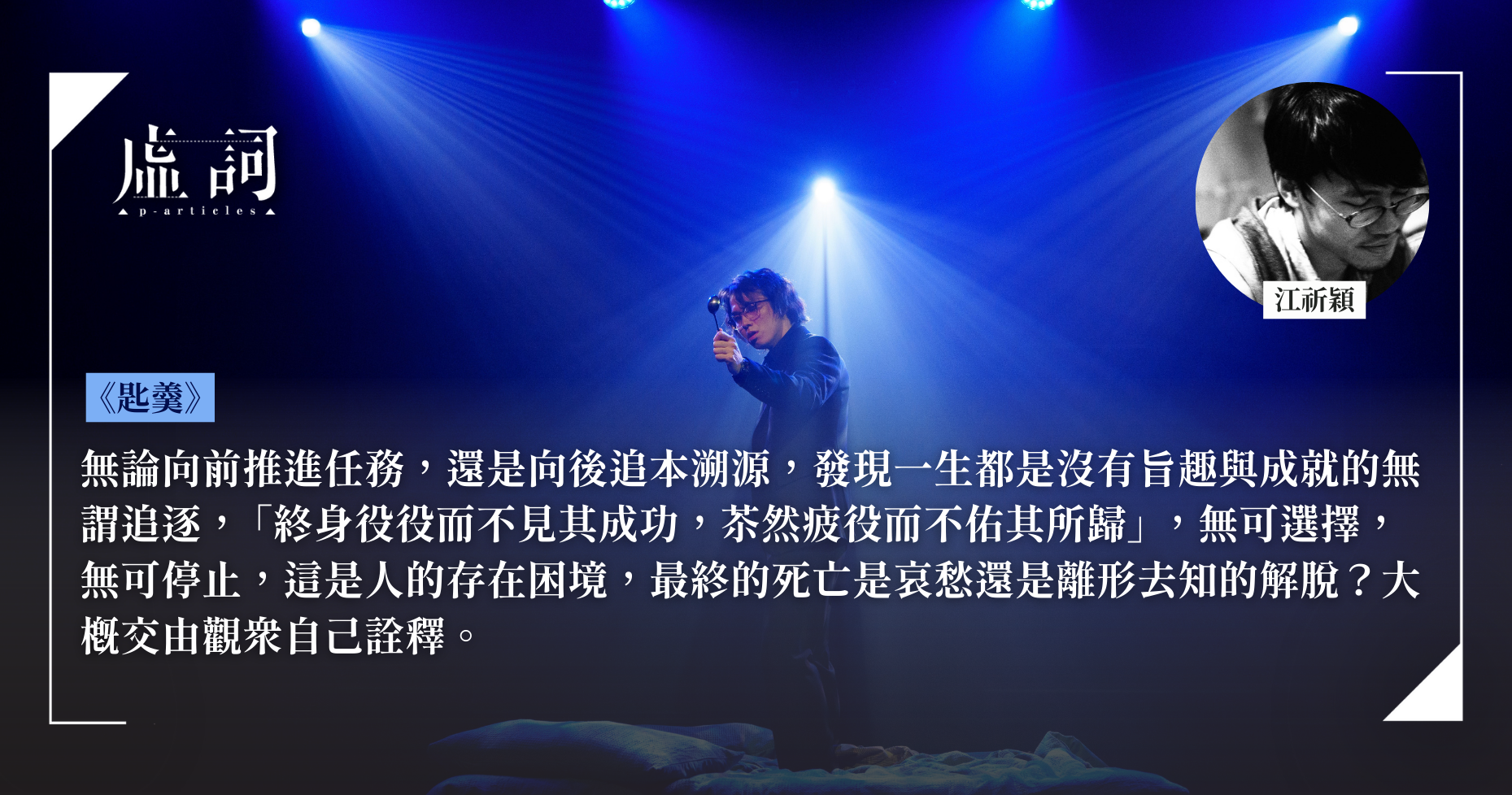江祈穎觀香港話劇團主辦的「新戲匠」系列劇作《匙羹》,想起多年以前取笑電影《湯匙殺人魔》劇情荒謬。多年以後重看,發現原來這就是生活活,人活著又無法不受折磨,存在即苦難。《匙羹》同樣走荒誕戲路,但越後來越發現,這是寫實的,而寫實的盡頭絕是更荒誕,比些悲喜劇更為折磨苦難,與《湯匙殺人魔》不同的是,劇裡提供了一個疑似出路:逃離苦難的快捷方法,莫過於找個比你更痛苦更低沉的人,在他面前故作成功,找藉口把苦難轉移到他身上,一層一層尋找下線,最終在最低層找到一個無力發聲的替罪羔羊,無聲承擔一切。他認為編劇梁澤宇投入相當大的人生體驗,以平面設計師作底層人生為引子,種種可笑無意義而生的苦難,具體化成戲劇障礙,看到劇中人物儘力對抗,身為城巿人的觀眾更容易代入其中。他想起莊子《齊物論》指出,真宰不能在形軀生命及經驗世界中覓得,而人們都受形所限,在生存中與物相刃相靡磨耗生命,無窮追逐永不止息,陷落就成為必然的結局。若發現一生都是沒有旨趣與成就的無謂追逐,「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佑其所歸」,面對人的存在困境,最後面對的態度大概都需交由觀眾自己詮釋。面對細節豐富的文本,導演邱廷輝活用黑盒劇場的簡潔漆黑,利用投影營造出都巿的深夜浪漫。舞台建成反光平台,那正是都巿中被突出的獵奇事件,觀眾正是把詛咒轉嫁於他人的人們,事件背後的因由或匙羹為何都不重要,重要是看到那拼命掙扎與失敗後,人們如何疲役地找到下一場荒謬劇。 (閱讀更多)
忘川嬉水,記得自己的本來面目 ——評《給美狄亞的男孩們》
近日西九文化區與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聯合製作的《給美狄亞的男孩們》,以古希臘經典悲劇《美狄亞》結局為起點,以美狄亞的兒子為主角,由兒童與成年演員同台參演,結合了扮演、編作、即興、遊戲及多媒體影像等元素。詩人廖偉棠為了學習自身經驗以外的新生命而觀看,然後在小演員身上明白戲劇詩學的「淨化」(katharsis)有了不一樣的意義。他認為劇作有著前進進一貫以來的現代文學意識、豐富的隱喻細節、龐雜的議題野心和嚴謹俐落的結構掌控,而小演員在「忘川嬉水」,為他們這一代的命運充權,解構所謂的戲劇性之外,也提醒我們要記住自己的本來面目。 (閱讀更多)
《月明星稀》與漢娜鄂蘭
劇評 | by 蕭雲 | 2024-07-02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近日上演了全新劇作《月明星稀》,以香港、倫敦、柏林、基朗拿和愛爾蘭莫赫懸崖多個地點的離散故事,構成多線交錯的敘事,其中一幕令蕭雲印象難忘。劇中主角之一「阿遠」(鍾益秀飾)堅持想還47本不復存在於圖書館目錄的書,被圖書館長(黃衍仁飾)勸退,當中一場「善意而溫柔」的對話,讓蕭雲想起 1933 年柏林警局的囚室裡,給了漢娜鄂蘭一條生路的警官,令世界從此不同。 (閱讀更多)
一舖清唱:《____小事化有____________》——把歌唱成舞台劇再演成電影的戲法
劇評 | by 新八 | 2024-05-30
無伴奏合唱劇「一舖清唱」最近推出原創音樂劇場《____小事化有_______》,由「一舖清唱」聯合藝術總監盧宜均包辦作曲、編曲及合唱指導,加上著名填詞人梁栢堅執筆,捕捉了城市內小人物的聲音。新八回想十二個獨立的場景,當中充滿電影感的舞台處理,是他認為近年最出色的,觀眾能在〈草書〉感到「又去草被玩一餐,再揈手遊遊閒」的放鬆,〈霞氣〉則述說了淡然哀傷的愛情故事,而導演林俊浩充分利用劇場空間,營造出多變的場景,為觀眾帶來不一樣的劇場體驗,在疲倦的生活中打開了一個休憩的空間。 (閱讀更多)
還有甚麼憧憬與憂鬱:從藝君子劇團《惡之華》看波特萊爾
藝君子劇團的同名新作《惡之華》,以詩集為基礎,嘗試與觀眾探索波特萊爾的世界。創作過程中,陳臻亮與創作團隊共讀《惡之華》、《巴黎的憂鬱》、《波特萊爾書信集》、波特萊爾晚年隨筆集《我心赤裸》,以至後世對他的評價與剖析,嘗試尋找蛛絲馬跡,重塑波特萊爾的面貌。陳臻亮認為今次創作把詩集放入表演,不禁會問,身處在2024年的時空,比起十九世紀的巴黎,人們還有甚麼憧憬與憂鬱?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