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都》:不結婚的結局是尋回自己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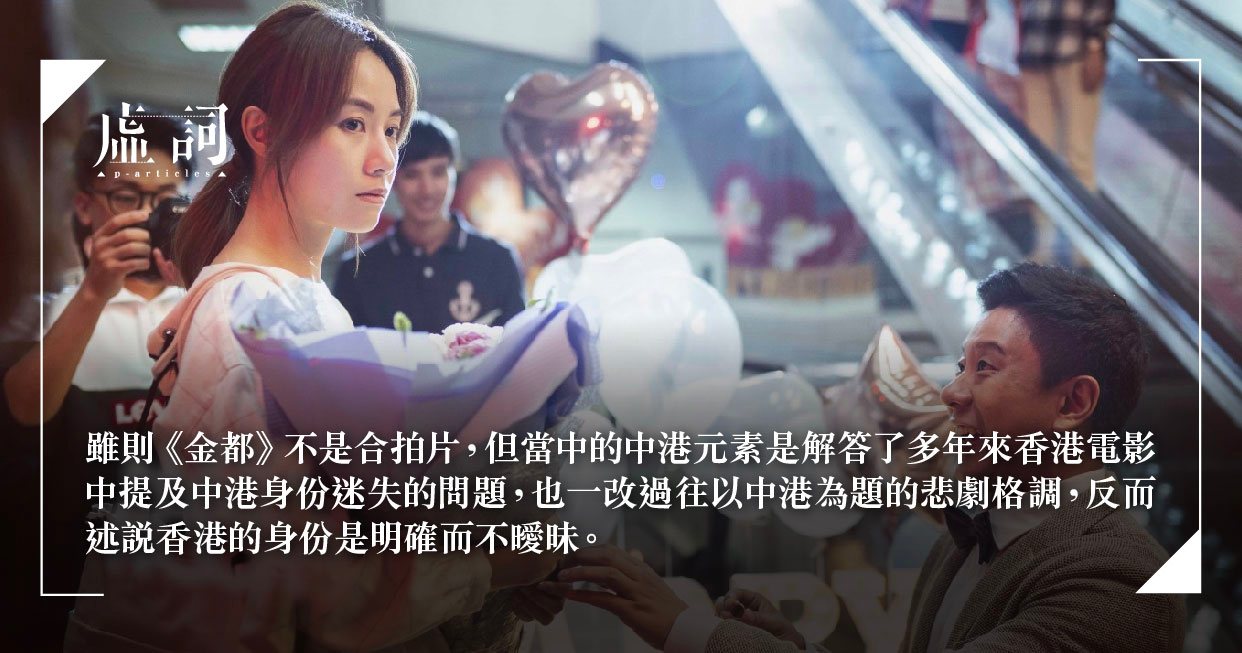
280296432_518199029856651_2259711341008508851_n.jpg
高先電影院為迎接開業一週年,重映一系列高先電影出品的電影,《金都》是其中之一。計及今次重看,我已在戲院看了三次《金都》,不是為了寫影評而看這麼多次,而是看了近年一系列以香港為題的電影,不計那些重映或上映無期的,能上映或重映的香港電影中,《金都》絕對是近年十分重要的港產片,甚至是近年香港電影中其中一大重要註腳。雖則《金都》不是合拍片,但當中的中港元素是解答了多年來香港電影中提及中港身份迷失的問題,也一改過往以中港為題的悲劇格調,反而述說香港的身份是明確而不曖昧。
《金都》第一鏡頭是洗衣店櫃台上的白色婚紗遮蔽張莉芳(鄧麗欣飾),然後張莉芳取回婚紗返回她工作的金都商場,就此展開電影的引子——處女情義結。處女這個生理特徵在《金都》內是不由自主。在電影初段,張莉芳穿着的鬆身V領上衣容易露出胸圍肩帶,男友Edward(朱栢康飾)對此甚為介意,不但為她整理衣領以遮蓋胸圍肩帶,更叫她不要再穿這衣服——日常如穿衣也受限,對如今港人而言,可謂身同感受——劇情其後講到張麗芳好友阿怡(林二汶飾)得知白色婚紗代表處女時,說白色婚紗「實滯銷」,代表處女已不普遍,這種諷刺更見社會對處女情義結的執着極為偽善。
處女與否,理應屬於女性自己身體,過往洪尙秀的《處女心經》更以「失貞」為主題,當中的一段可與《金都》對照:在《處女心經》中,女主角秀貞與男主角傑勳發展進一步關係時,傑勳知悉秀貞是處女後他露出的笑容,縱然他們同坐在床邊同一視線,但這種男性「俯視」女性身體的隱喻,令人心寒;同樣的權力關係在《金都》更具象化:張莉芳與Edward為結婚張羅時,張莉芳試穿中式裙褂,Edward卻在她手袋裡發現她與內地人楊樹偉(金楷杰飾)假結婚的結婚證書後,強行拉着正穿着裙褂的張莉芳到他的工作室,在工作室內站着的Edward質問坐着的張莉芳,更具體呈現男性俯視女性的行為。在沒有愛情只為佔有的婚姻中,現代男性要和處女結婚只是將處女情意結掃進一紙婚書底裡。
在《金都》中張莉芳每每遷就Edward,她自己的身體及身份愈見迷失。誠如導演黃綺琳在《金都》劇本集「自序」所言,「處女情義結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張莉芳怕Edward 或者Edward的母親大人介意她結過婚、Edward最關心的是張莉芳有沒有跟假老公上過床、張莉芳不想住二手樓、白色婚紗代表處女,非處女只能只能穿珍珠色」。說到底,處女情義結一直在香港以不同形式存在,不斷蠶蝕我們。在電影《金都》裡的人,不論女性如張莉芳,連男性如Edward凡事聽命於母親(鮑起靜飾),結婚也是為迎合母親的要求,Edward要與張莉芳結婚只為完成社會既定的人生方程式,甚至連Edward母親要他們「結婚擺酒」也為迎合親朋戚友。金都即香港,《金都》內的人,命運是不由自主,結婚如是,身體如是,處女更不是張莉芳身體的一部分,而是被賦予的處女情意結中的一部分。假若對照港產片如今的命運,更是寫照。
然而,《金都》劇情的推進卻未見絕望,反而表達港人/港產片是可以繼續走自己的路。《金都》像過往的港產片一樣,也有牽涉中港關係,但不像過往港產片處理同類主題般絕望。在2016年的許學文、歐文傑及黃偉傑合導的《樹大招風》甫開首,已是季正雄(林家棟飾)在播放着「九七回歸」片段的電視機前焚燒身份證,港人身份將被抹殺的意象昭然,而電影隨後三大賊王返回中國更見身份模糊及迷失;而2006年杜琪峰的《黑社會:以和為貴》中Jimmy仔(古天樂飾)在中國內地有如「龍游淺水」的遭遇更是絕望。不只返回內地後迷失,內地人來港在近年港產片也是悲劇收場,以2004年爾冬陞的《旺角黑夜》及2009年許鞍華的《天水圍的夜與霧》最是明顯,《天水圍的夜與霧》更是中港婚姻悲劇的寫照。
反之,《金都》在處理中港婚姻的議題上,以張莉芳及楊樹偉假結婚入題,雙方本無感情,各自也是為了自由才假結婚——張莉芳不想與家人同住,楊樹偉想申請單程證,然後移民美國,兩人才於十年前假結婚——但他們沒有感情的「婚姻」,沒有悲劇收場,反而悲劇出現在張莉芳與Edward的「真結婚」中,他們表面雖有愛情,但Edward處處管制張莉芳,張莉芳只能不斷忍受,直到Edward揭發張莉芳與楊樹偉假結婚後一連串矛盾白熱化到出現電影中段的一場鬧交戲,雙方矛盾也得不到解決,反之張莉芳跟楊樹偉去福州辦理離婚手續時,她關掉手機去迴避Edward連番的訊息轟炸,慢慢才找回自己的生活節奏。
在電影尾段她再次去福州探楊樹偉前,因Edward母親自作主張放生了她養的小龜,Edward與張莉芳到太子花墟明渠找小龜後再次齟齬,Edward以合約形容婚姻關係,兩者之間愛情的空洞,回應了香港這個「金融都會」如教條般刻板與冷酷。從而引伸電影結局是張莉芳穿回電影起首那件V領鬆身上衣,再去福州探楊樹偉,退回他送給她的人民幣,然後在福州一間麵店自在地食麵及買她原本想買的傢俱——這與過往非合拍片的港產片處理中港關係的不同是,雖然這段「中港婚姻」是假結婚,但卻令張莉芳找回自己的身份,去重拾本屬於自己的自由(之所以「重拾」是因為她假結婚本來就為了自由,為了擺脫不愛她的父母),從絕望的「真結婚」中找回可「自由拒絕絕望」的希望;《金都》更突破了過往合拍片中港人日漸迷失的困局,就是港人的身份不是無法定義或唯唯諾諾,是本來已有,只要重拾自由抉擇的勇氣,就會顯現出來,即使港人返內地也不會迷失身份,甚至在對照下更見明顯——在《金都》電影尾段的一場戲可堪玩味:楊樹偉恭喜張莉芳,張莉芳反問他恭喜她甚麼,他說「你結婚」,她說「李潔冰」(Edward在電影初段將他朋友「李潔芬」(廣東話諧音「你結婚」)及「李潔冰」合成的冷笑話),從楊樹偉的聽不明白與張莉芳的輕鬆以對作對照,中港差異不一定要以融合為出路,差異更可點石成金,這也是港產片在電影市場上發展下去的出路。更重要是,《金都》平實地述說中港關係,即使港人回內地不單沒有迷失,也沒有歌頌人民幣的偉大,而是以一個尋回自己身份的目的地,去描寫中國內地這個地方。
遺憾是《金都》在2020年票房沒有大收旺場,但《金都》肯定是近年重要的港產片。2015年《十年》(同樣是高先電影發行,但不重映,是可以理解)曾被某文化人批評過份本地化,沒有提升至國際層次,外國觀眾難以理解。即使橫掃全球影展獎項的《上流寄生族》,也一如奉俊昊以往的韓國本土關懷。正如黃綺琳接受訪問時引用《伊朗式離婚》及《伊朗式分居》為例,這兩套充滿濃厚地方色彩的電影也能在國際影展大放異彩。這正是港產片應繼續生存下去的重要註腳,這亦是近年新導演多以香港為題拍攝電影的現象,因為在這個時代,香港理應向全世界展現另一個香港電影新浪潮,向全世界繼續講香港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