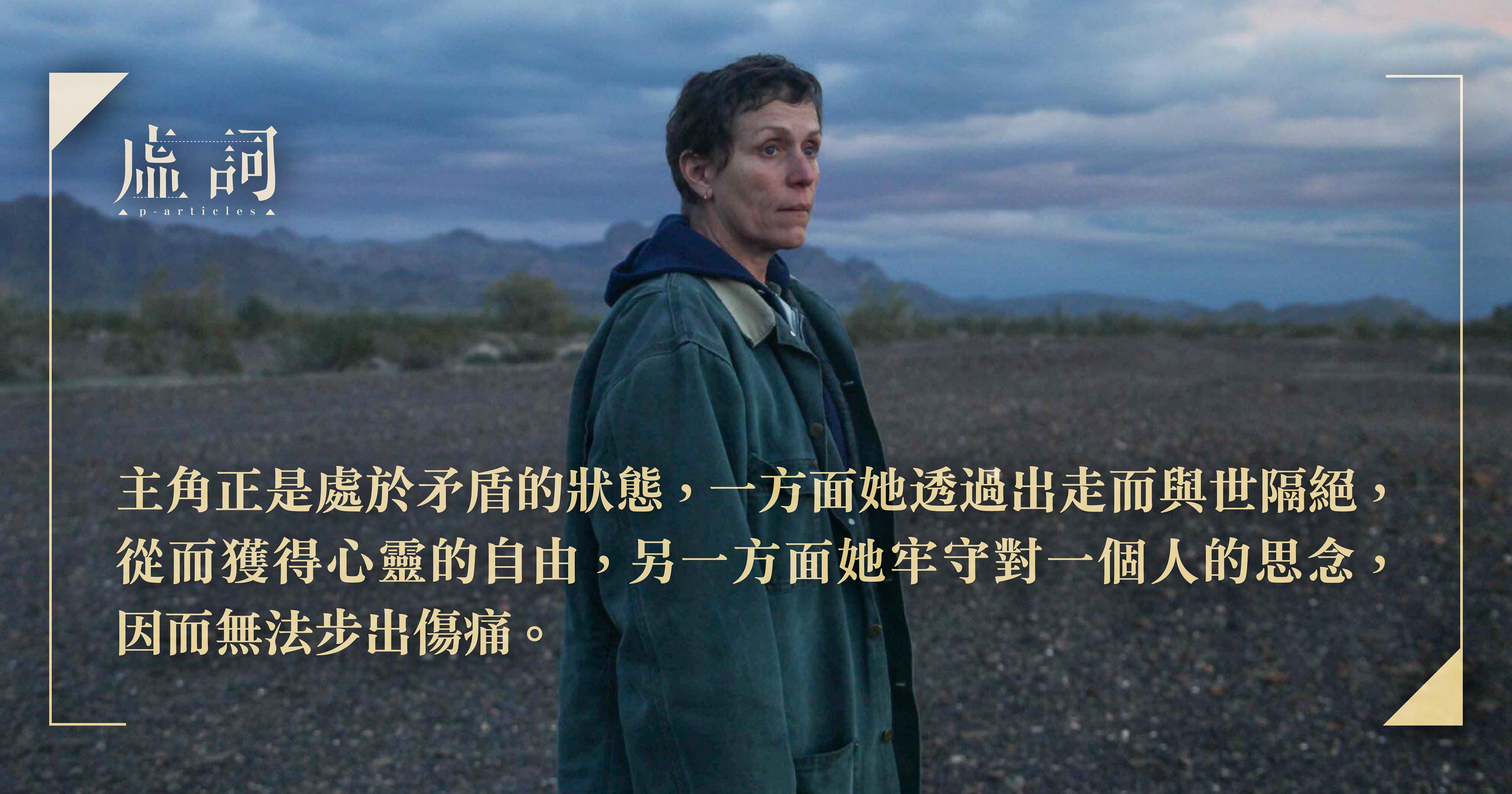《浪跡天地》:沒有夜歸人
影評 | by 失.逃 | 2021-04-22
這世界還剩下一個人沒有睡著
這個夜晚屬於他
路燈下沒有夜歸人
— 傷心欲絕 〈沒有夜歸人〉
純粹的孤獨乘風奏起荒原上的樂章,野草伴樂地輕輕搖曳,她站在荒原的開端,靜謐感受湧現的記憶和孤寂,無處是我家,落處即為家。
清晨漫步的當下,肌膚能感受空氣中晨露水珠的冷意,幾聲問候,遁入晨曦將至的地平線。《浪跡天地》(Nomadland)講述的是每天親歷初露的晨光、姣好的圓月、輕滲的草香的一個族群。他們住在自己的房車裏,花盡心思打造專屬自己的家。隨着微風飄浮的鏡頭,捕捉到那些剛打開車門,正在梳洗、煮咖啡的人。不同的原因,使他們不得不上路。所謂「無家」,不只是身體跨越地域的流動狀態,也是無法使雙腿著地,永遠靜止地待在精神困局的描述。前行不再是具有目標的進程,而是各自尋找療癒秘方的修行。
《浪》導演趙婷自言視泰倫斯馬力克(Terrence Malick)為她的精神導師,從作品而言,強調自然光源和手持鏡頭,以人物為主的敍事基底,均可證明趙婷所言非虛。若深入談討馬力克的作品,透過解構崩壞的現處結構,向外或向內尋找「新世界」的可能性,是馬力克的創作主題。《狂林戰曲》(Thin Red Line)與《新世界》(The New World)撥開重重煙火濃霧,試圖找出戰爭的本質;《天堂之日》(Days of Heaven)置於經濟衰退的時代之中,流徙中的族群獨靠虛妄的情愛關係支撐,;《生命樹》(Tree of Life)透過精心神遠征至銀河星際,穿梭過去與现在,尋求諒解父親,同時放開自己的可能。不論電影的時空設定,馬力克處理的人物總能觀察正在崩壞的文明(或是個人的精神)世界,他們透過自己的方式,奔向一個理想化的精神空間。如此一來,《浪》或許可以此作為剖析的開端,亦成為了其矛盾之處。
《浪》講述一個後半生不回家的人,逃離典型中產家庭的虛妄生活後,嘗試以現代遊牧的方式療癒過去的傷痛和早已枯竭的精神狀態。如此一來,電影同樣可理解為尋覓新世界的旅記。離開故有的家園,漫長的流徙中插入鏡頭的存在,攝影機伴隨 Fern(法蘭絲麥杜曼 飾)到處工作和歇息。混雜專業與素人演員的群體互動讓觀眾慢慢理解「游牧者」的日常和共通性。如此一來,專業演員與素人的分野便顯然易見。尤其在於如法蘭絲麥杜曼這種技法嫺熟的演員,強求她短時間內融入一個徹底真實的族群,大抵是強人所難的任務。故此,《浪》的整體表演即落入一個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演員的表現無法說服觀眾代入一個半虛半實的人物,另一方面,抽離的觀影過程不由得讓思索創作者與真實族群的關係,繼而雙重否定了導演原以為設定的親密感。
更甚者,《浪》的問題癥結不只在於演員之間無法磨滅的實感差距,而是延伸至整個敍事取向的割裂感,從而讓人意識到創作者舉旗不定的處理。從整體角度看,《浪》是一部試圖融入真實事件與虛構劇情的作品,前者指涉當代美國游牧社群的生活經驗,他們好比現代的嬉皮士,透過選擇有別於常人的生活方式,表面上他們對抗的是社會常規,但他們真正想得到的,是要實踐更為徹底的傳統價值,比如是自由與愛;後者卻是反映作為游牧者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卻因上路的原因而精神囚困。如此一來,《浪》主角正是處於矛盾的狀態,一方面她透過出走而與世隔絕,從而獲得心靈的自由,另一方面她牢守對一個人的思念,因而無法步出傷痛。關於「自由/不自由」類似的討論,不禁令人想起奇斯洛夫斯基《藍白紅三部曲之藍》(Trois couleurs : Bleu),也呼應到艾麗絲·華妲《無法無家》(Vagabond)對於「無家者/游牧者」的身分流動狀態和現實生活的窘境。《浪》前半段的主角多半成為某個真實素人或族群的介入者,從他們的互動裏,鏡頭突然插入二人的對話空間,宛如訪談式的紀錄形式呈現素人們的自身經歷。導演試圖捕捉的,顯然是彷效紀錄片下的真實感,並且透過電影語言賦予每位素人的同等發言空間,以此達到其心目中的關懷。如此一來,這樣的處理固然是雙面刃。當觀眾凝視(偽)素人直述命途多舛的人生,彷紀錄片形式的預設真實感自然使人動容;可是,平鋪直敘的呈現也省卻了以故事方式表達的可能性,雖說動容,卻不足以稱之為「深刻」或「豐富」,故此看似真繫的情感,實際上不太穩定,因而創作者必須另尋路徑,強化素人經歷本身具有震撼力。可惜,《浪》顯然在整個敍事結構中失衡,因而創作者於前後部分嘗試的效果均屬失效。《浪》後半段回歸主角的個人視點,Fern 的人際關係逐漸建立起來,也貌似有回歸常規的家(庭)模式。即使她曾嘗試回鄉或是進入別人的家,面對愛她的親人和同伴,她始終無法釋除喪夫(家)之痛和無根感,她終究是一位不能回家的人。如此看來,導演設計的整個敍事結構便顯然易見:透過電影的前半段安排不同的素人演員,讓觀眾沉浸於邊緣族群的生活經驗,從而承托後半部虛構的個人傷痛與其意圖作出的和解,亦是延伸「流徙」的其他形式,像是趙婷少年時期離開家鄉,遠赴美國研讀電影的移民身分;或是中產階級虛妄的存在價值。可是,如此刻劃特定虛構人物的後半部,正是與以徬紀錄形式捕捉真實群像的前半部,形成了宛如鴻溝的割裂感,因而使後半部讓觀眾徹底投入的企圖完全失效。
回看過來,馬力克的成功之處,在於他透過某種迂迴的路徑描寫他的人物,像是本來生活無憂的美國中產階級(《生命樹》),或是側重於個人心理狀態和哲思(《狂林戰曲》),甚至大時代下的例外狀態(《天堂之日》、《隱秘的生活》(A Hidden Life)),從而側寫人物的不同掙扎。雖然這些的敍事設定使故事不具備強而有力的寫實感,可是塗抹上一層虛幻色彩的處理反為更為連貫,或是像導演以全素人演出(主角甚至是真實事件的當事人)拱托的「重演」前作《重生騎士》(The Rider)也同樣適用於建兼具劇情與情感的張力。當然,《浪》作為一部以邊緣族群為題的電影,側重於感性表達的取向並非必然成為它的「缺失」。所謂的選擇,這不過是創作者的選取而已。只是,當整體的情感表達崩壞之際,所謂「以真實人物提煉戲劇」的方式便會變得更不可信,因此本來誠懇的關懷,則會讓人覺得虛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