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跡天地》小輯
專題小輯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1-06-17
雖然《浪跡天地》和導演趙婷已經橫掃多個國際電影獎項,不過,坊間對《浪跡天地》評價不一,有人認同電影中借遊牧生活打破城市迷思,追尋真正人生意義,但同時亦有人認為電影過度美化美國的houseless現況,迴避了真正的社會議題。
《浪跡天地》:各種悖論導致形式成雙面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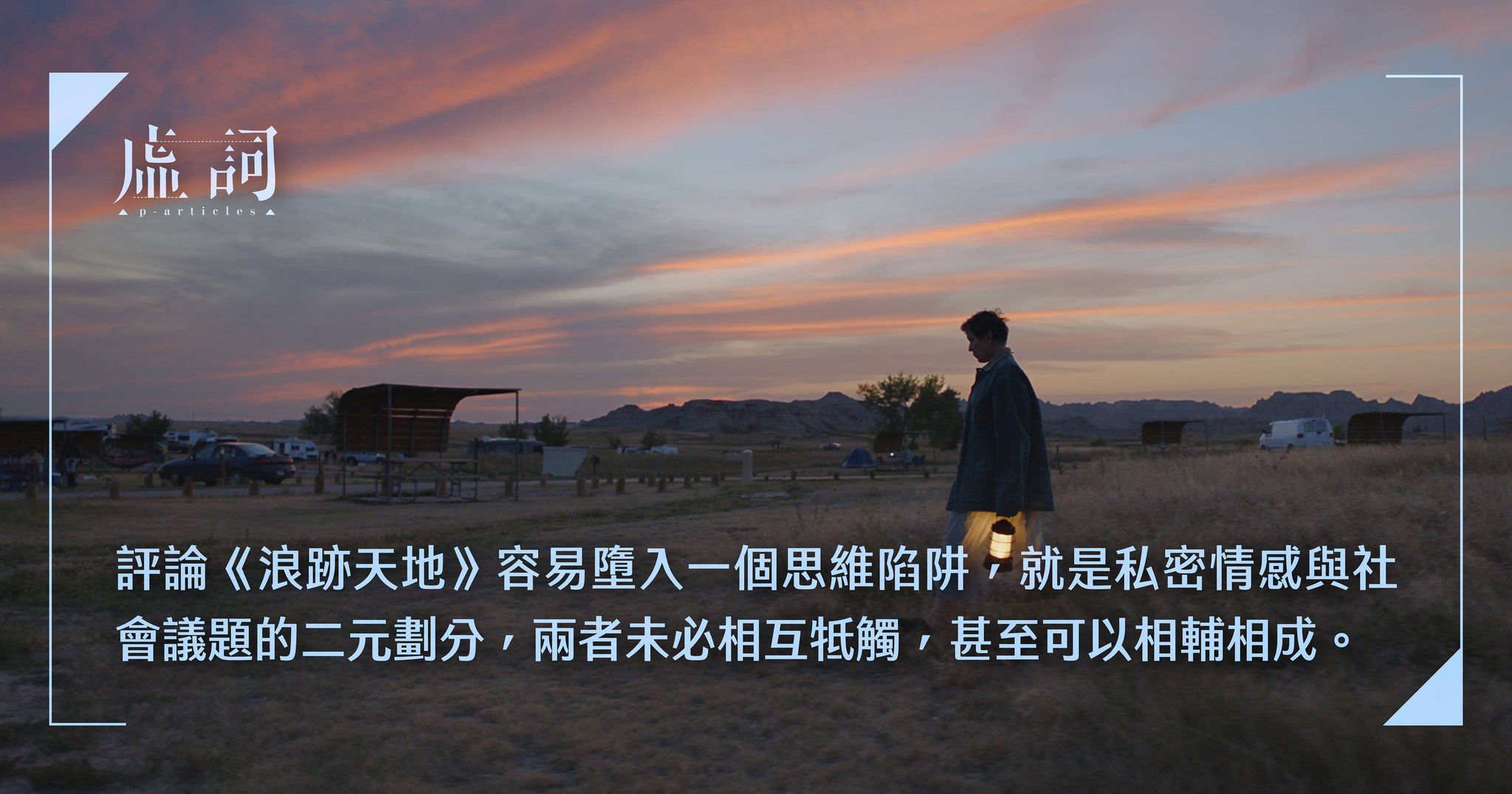
評論《浪跡天地》容易墮入一個思維陷阱,就是私密情感與社會議題的二元劃分,兩者未必相互牴觸,甚至可以相輔相成。《深夜裏的美味祕方》(‘First Cow’,Kelly Reichardt導演,2019)是一個極佳的例子,影片極細膩地刻畫兩個男人間的友誼、他們跟母牛的互動,可是敘事焦點無礙觀眾看見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雛形(文明與野蠻的碰撞)、俄勒岡在1820年代的處境(族群間的暗流湧動),題外話是故事以骸骨開場跟《無法無家》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浪跡天地》:佛學味道的美國電影

電影把一個旅者的心情捕捉得細緻——震懾的景色有時候,的確讓人不枉此生。然而一個人在路上久了,也會渴望與人同行。在另一部流浪的經典《Into the Wild》,主角最後顫顫寫下「Happiness is real only when shared」。《Nomadland》裏到過無數地方的阿伯,希望臨老有伴,也肯回家好好去當爺爺,是平常不過。快樂許多時是建基於與人分享經歷,多於那個經歷本身。況且,人總是在漂泊中求安穩,安穩中求刺激,刺激過後羨慕淡泊。一路的浪蕩,或是了無生氣的穩定,都不是人的終極嚮往。
《浪跡天地》:沒有夜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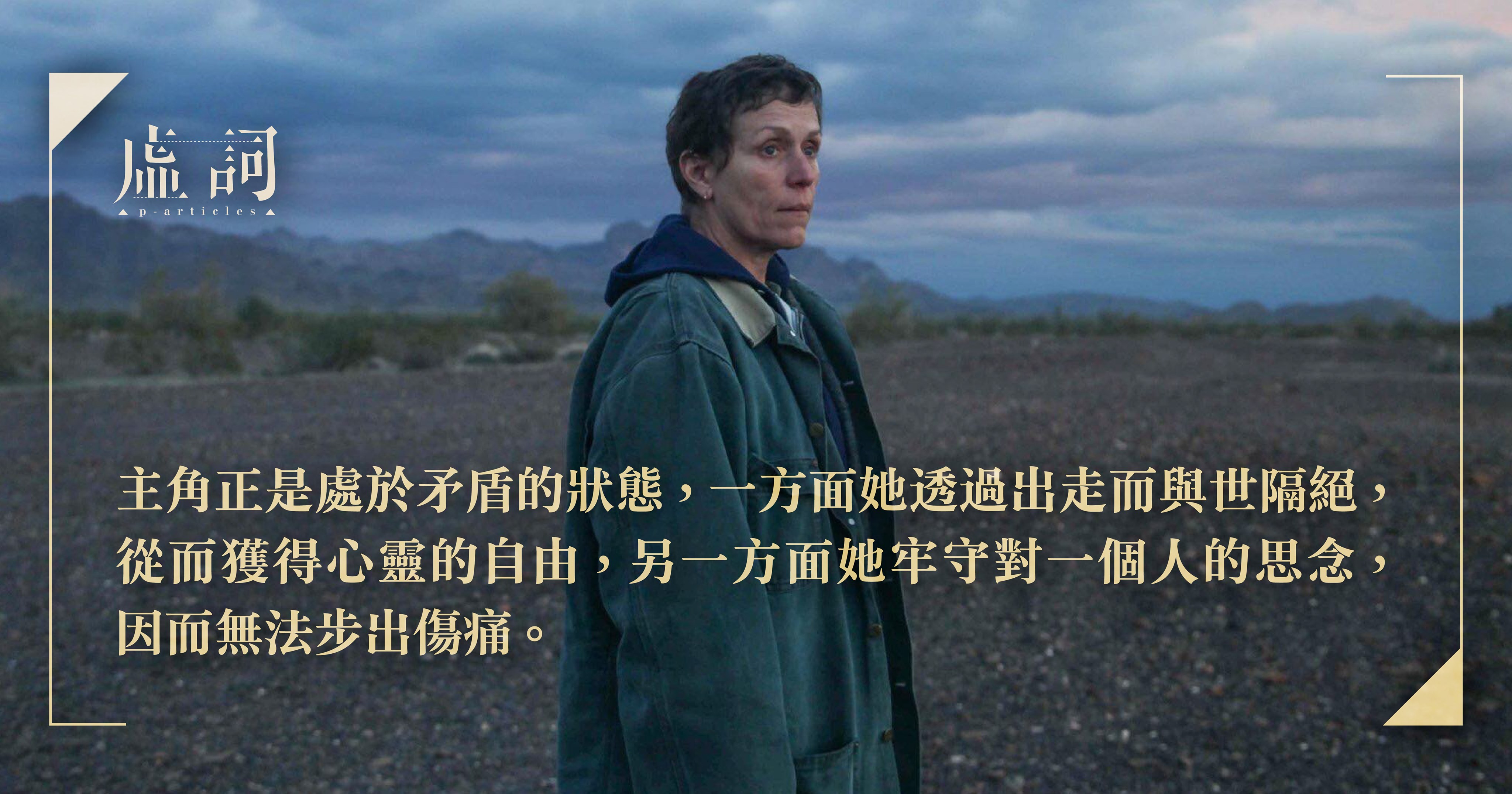
《浪》導演趙婷自言視泰倫斯馬力克(Terrence Malick)為她的精神導師,從作品而言,強調自然光源和手持鏡頭,以人物為主的敍事基底,均可證明趙婷所言非虛。若深入談討馬力克的作品,透過解構崩壞的現處結構,向外或向內尋找「新世界」的可能性,是馬力克的創作主題。《狂林戰曲》(Thin Red Line)與《新世界》(The New World)撥開重重煙火濃霧,試圖找出戰爭的本質;《天堂之日》(Days of Heaven)置於經濟衰退的時代之中,流徙中的族群獨靠虛妄的情愛關係支撐,;《生命樹》(Tree of Life)透過精心神遠征至銀河星際,穿梭過去與现在,尋求諒解父親,同時放開自己的可能。不論電影的時空設定,馬力克處理的人物總能觀察正在崩壞的文明(或是個人的精神)世界,他們透過自己的方式,奔向一個理想化的精神空間。如此一來,《浪》或許可以此作為剖析的開端,亦成為了其矛盾之處。
死不是生的對立,而是它的一部分:並觀《明明無盡》與《浪跡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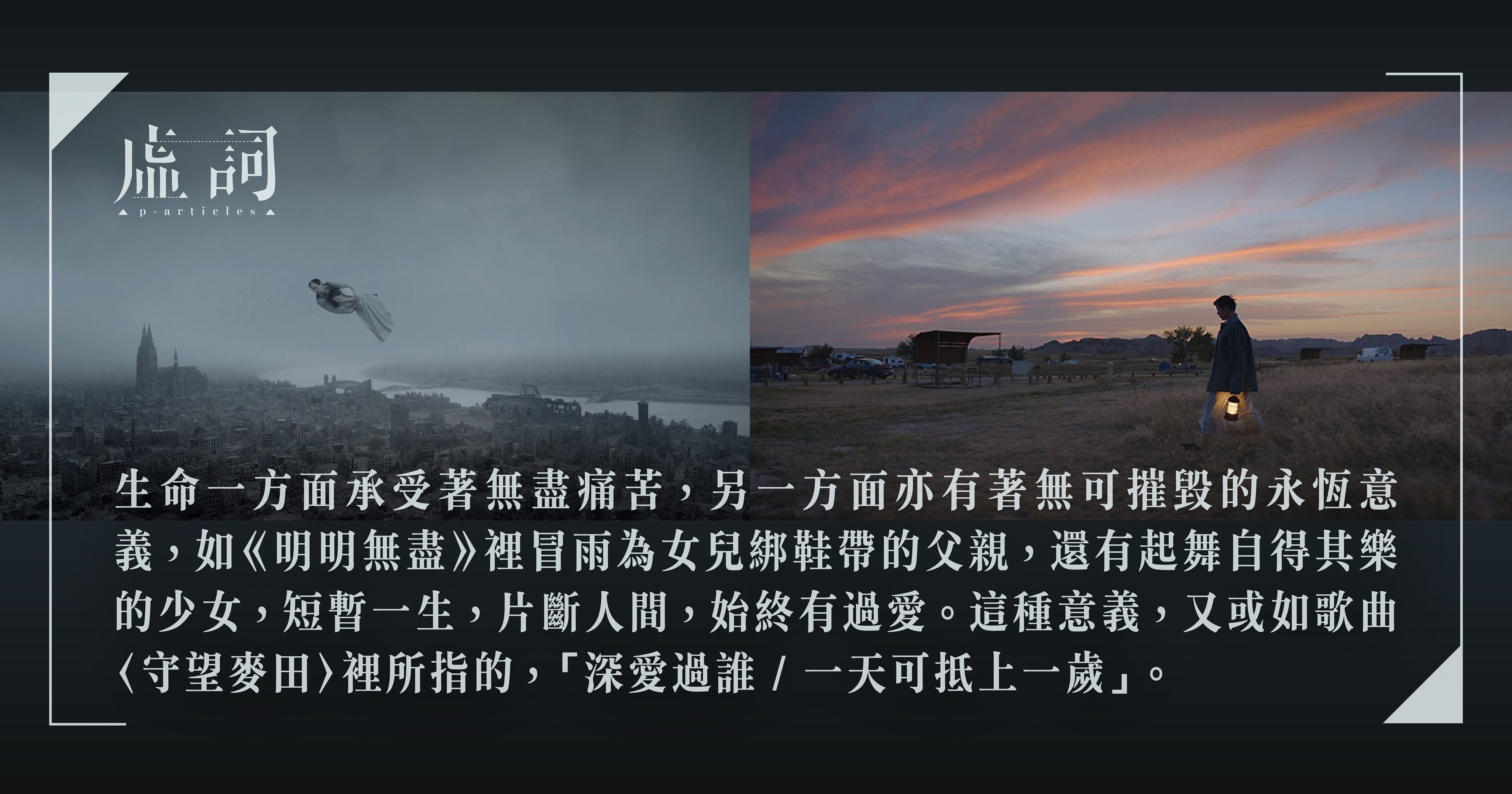
沉默是《浪跡天地》的基調。Fern大部分時間不是在路上,就是在工作中。在路上時,時光緩慢,她踏在歷經千萬年風化而成的奇山怪石之中,她遙望夜空那遠在光年以外的星光,在古老的宇宙裡,她沉默。在工作中,時光飛逝,她在亞馬遜公司處理包裹,她在快餐店製作速食,在重複瑣碎的流水式工業中,她沉默。導演故意安排Fern在兩種沉默中遊走,無須硬生生的說教,自然呈現出兩種生活的強烈對比,前者充實飽滿,讓人連結萬物,肯定生命,後者虛無空洞,記憶無法成形,教人否定生命。
《浪跡天地》:談評論者的「思維陷阱」,對劉建均影評的幾點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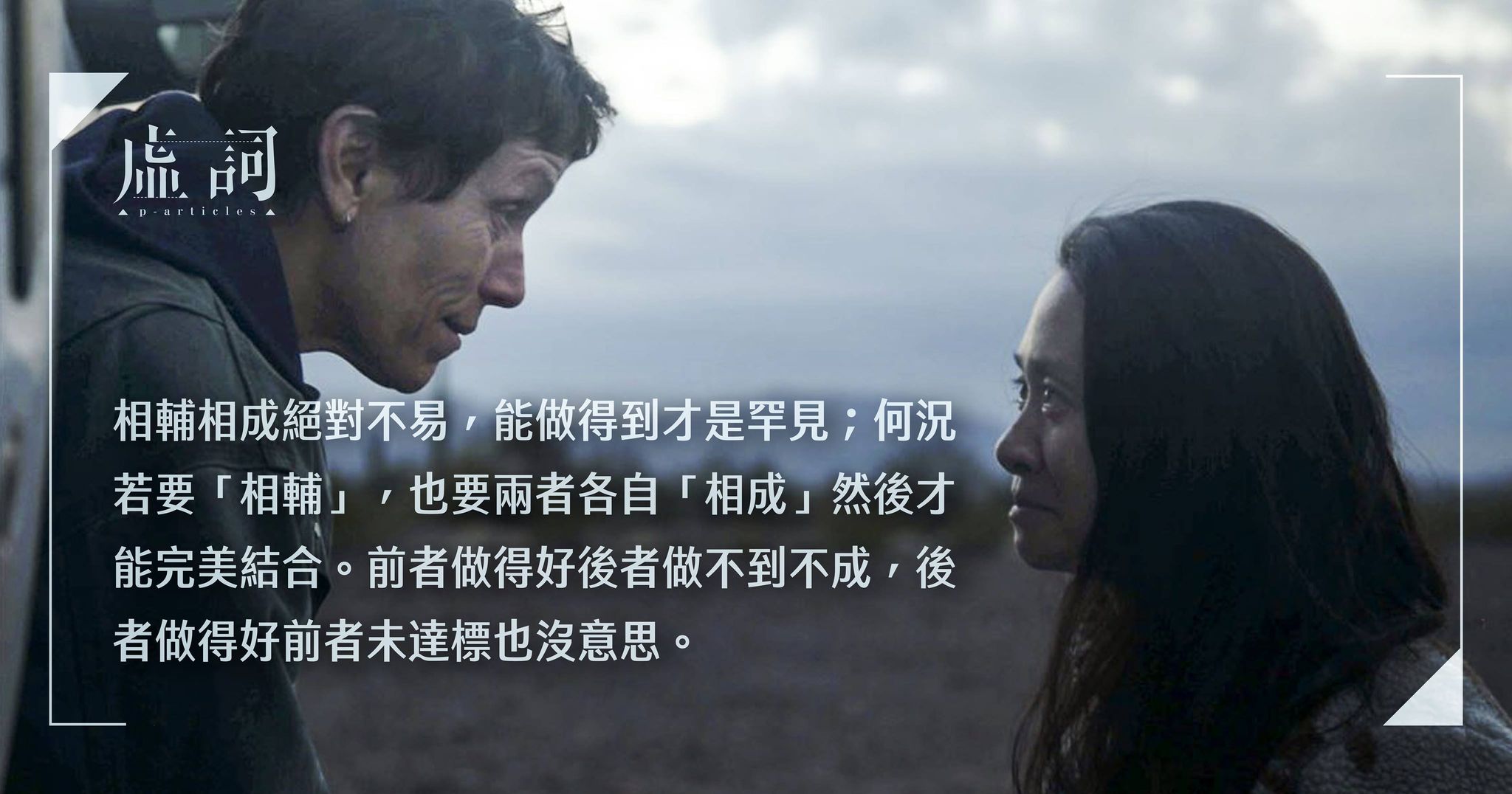
近讀劉建均早前的《浪跡天地》影評,陳廣隆認為它是相關影評中,寫得甚為出色的一篇,有些論點更值得仔細討論,並對此作出幾點回應。當我們回憶觀影歷程時,如何明確分辨自己到底在甚麼時候生出怎樣的情感並得出怎樣的結論,陳廣隆借這篇文章嘗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