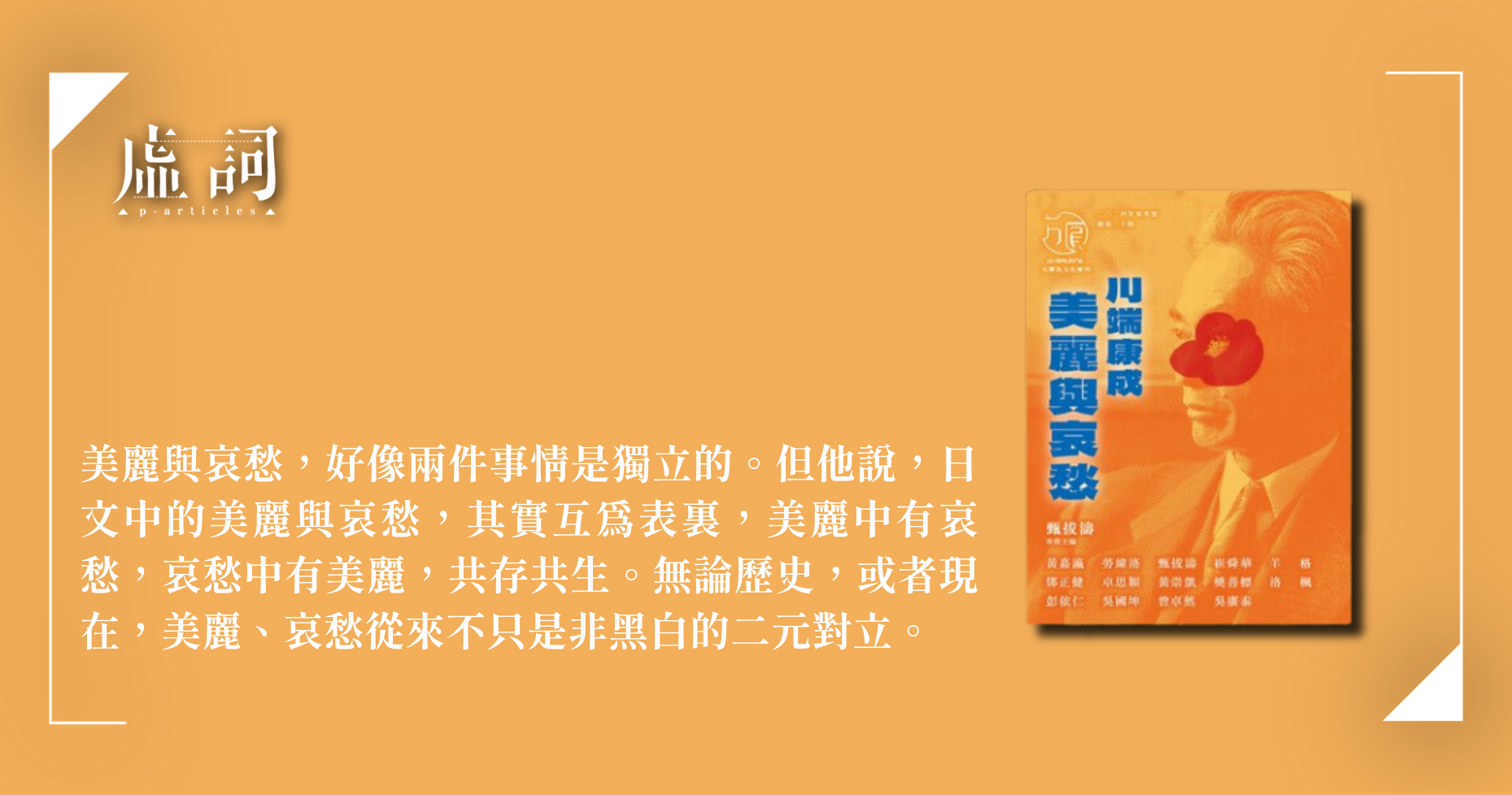《方圓》「川端康成・美麗與哀愁」——編者話〈哀愁中的美麗中的哀愁……〉
其他 | by 方圓編輯部 | 2024-08-26
今期《方圓》延續回應經典,迎來川端康成的《美麗與哀愁》。對談嘉賓之一的緯洛提到,中文的翻譯名字叫作美麗與哀愁,好像兩件事情是獨立的。但他說,日文中的美麗與哀愁,其實互為表裏,美麗中有哀愁,哀愁中有美麗,共存共生。
川端康成筆下的男女,多涉忘年、不倫之戀。刻板印象之下他的作品是情色文學,論者亦多以性別角度切入、研究他的作品。我覺得他反而老是在寫壓抑,就像李安。另一位對談嘉賓嘉瀛,同樣認為以性別理論閱讀川端作品,並非唯一條路。她在對談中仔細分析人物的心理狀態,常常深有啟發。正健同樣認為性別角度並非重點,所以他的分析也別出機杼。
小說中,作品好像都有魔力,會反噬作者、或他身邊的人及現實生活。不論是大木年雄的《十六七歲的少女》,或音子念茲在茲完成的畫作,都一樣。崔舜華小說中的女畫家,好像被美男肖像畫給吞噬,想像和現實的界線頓然崩塌。羊格小說中的男女主角,甚至已經不能還原一幅完整的情史圖像。
我們的現實世界,同樣美麗、哀愁兼備。「散策」中的作品,不謀而合地呼應刻下的生存狀態。黃崇凱直面一個活生生的人、隨時消失的恐懼。誰曰這只是歷史?身為作家,坦白說,也曾泛起過一絲半絲、人工智能取代人類寫作的恐懼。曾卓然、吳廣泰仔細檢驗這種恐懼是否成立。洛楓回到班雅明,述說後2019的說故事之困難。讀著讀著,好像聽一個很懂你的朋友在說話。彭依仁評析黃燦然詩作,連繫到自然、靈魂、以致深刻的痛苦,都是我們時代的命題。
歷史並不一定是來回往復的圓圈,更像滑不溜手地隨意變形,因而藝術史也有其有趣的面向。吳國坤將視角拉到1934年,重尋這個大時代下製作的電影《神女》之視覺力量。樊善標從盜印的《歐陽天隨筆》,補回香港文學史上的重要一筆——早期書業的發展。
無論歷史,或者現在,美麗、哀愁從來不只是非黑白的二元對立。
甄拔濤
2024年3月21日
葵芳新都會人造小草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