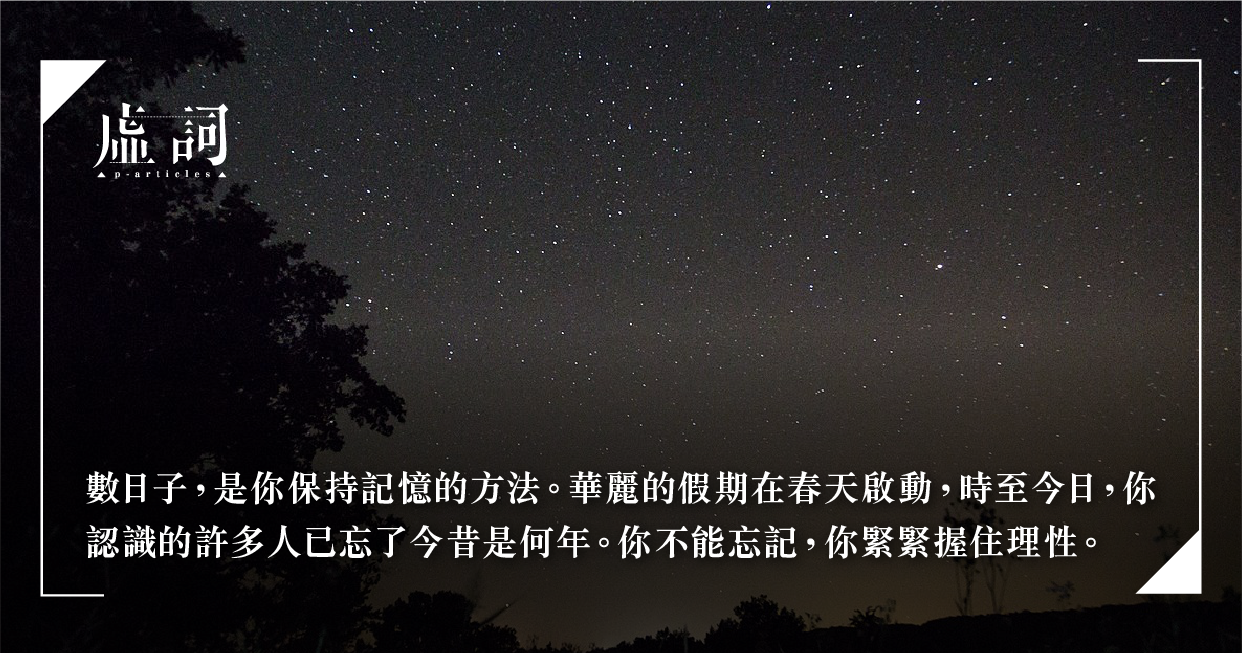回家
散文 | by 郝偉凡 | 2023-01-30
(一)
「今天是你到這裡的多少天了?」每當有人這麼問你的的時候,你總能給出一個精確的數字,第28天,第36天,第52天。數日子,是你保持記憶的方法。華麗的假期在春天啟動,時至今日,你認識的許多人已忘了今昔是何年。你不能忘記,你緊緊握住理性。
一推開門,樹葉沙沙地響,鳥囀囀地叫,菜粉蝶在草坪上飛,風吹過你的皮膚,陽光將其曬成黑色。眼見之處,都是綠色。你從你租來的小閣樓的天窗望出去,能看到什麼?一半屋頂,一扇天空,一隻鴿子。你從你老家的那扇窗戶望出去,能看到什麼?村落,莊稼,遠山。綠色不總是在家門口的。你現在在這裡,看這暮春初夏的田園風光,多麼美。這裡有一匹馬,兩隻火雞,兩隻鵝,三隻羊,一群鴨子,十幾條狗。蠶豆、豌豆、洋蔥已經成熟,油麥菜、土豆、黃瓜、玉米、番茄正在生長。你不必擔心你會挨餓。自然教育學校的老師教孩子們認識昆蟲和植物。你也跟著他們一起學做蝴蝶標本,做扎染蠟染。你何其幸運。但是,你知道,這裡沒有什麼是屬於你的,你也並不屬於這裡。回到這間借住的小木屋。你不能隨便移動家具的擺放,它們有自己主人的喜好。你最好不要使用屋內的任何東西,以免損壞。你要接受自己與另一人合用這個小木屋,以及接受小木屋的缺陷。
你扎起褲腳,一手拿掃把,一手拿簸箕,將積水掃起,倒進馬桶,沖走。洗完澡後,你重複以上步驟,日復一日。一個積水的衛生間,如同你的生活,將你圍困。什麼時候能疏通,未知。未知感,使你焦慮。你在夢裏尖叫到聲音嘶啞。你墊起腳尖,將破布掛起,你隔出一塊自己身體的疆域。
「你對空間有很高的要求,如果有其他人的物品在你的空間,你會感覺自己被侵佔。」占星師看著你的星盤說道,並且問你是不是與你母親關係疏遠。
你母親站在你眼前,側身背著個包。「你去哪裡」,你問她。她不說話,只是對你笑了一下。她的笑刺痛了你。她走了。你追了出去。你跟在她後面跑,想要抓住她。你跑丟了一隻拖鞋,站在那裡哭。一個小時後,她回來了。「因為你」,她站在你的房間說。她進你的房間,從不敲門。她和你父親吵架的時候,就會跟你一起睡。他們不離婚,說是為了給你一個完整的家。你想跟你母親離婚,跟你父親離婚,你要獨自生活。於是,你離開了家。可每年過年,你還是會回到你的老家。三十年來,從未間斷過。現在,你想回家。在外求學工作多年,你歸家的心情從未像現在這麼迫切。你知道,你想要回到的並不是有你母親在的老家,更不是你租來的那個小閣樓。「一個人要如何才能建造一個新的家?」你自問,還是你只能永遠在自己的家園流浪?
(二)
你和同伴一起出門。街上的人和你們一樣,脖子上掛著通行證,背上掛著帆布袋,手腕上掛著網兜包,步行。超市外面早已排起了長隊,至少有兩百米長。有人的耐心已耗盡,試圖加快排隊的步伐。看門人出來制止,然後,出現了推搡,排隊的人紛紛掏出手機拍攝。你們聽見那個崩潰的人罵娘罵老天。你們的時間不夠你們圍觀,你跟同伴指了指馬路對面的那家小超市,排隊的人沒有那麼多。
「禁止通行」。當你把臉對準機器人的時候,機器人發出警報聲。「禁止通行」——機器人重複著這句話。你有點慌。因為昨天你沒有準時上交你的唾液。你僥倖的以為不會有什麼後果。現在,你知道你要付出什麼代價了。你深吸一口氣,鎮定了下來,你和看門人說好話,希望他能睜隻眼閉隻眼,放你進去。「像你這樣的人我見得多了!」看門人不為所動。你立即調整策略,擠出了幾滴眼淚,你就差在地上撒潑打滾了。這時,排在你後面的人騷動不安,「讓我們先進去吧。」他們祈求道。看門人舉起鞭子,「排好隊,保持距離!」人群噤若寒蟬。同伴早已趁亂擠進超市搶購。你站在隊伍外等待。等待同伴出來。等待她能買到你需要的咖啡和香菸,還有貓糧。
(三)
你彎著腰,拔除地裏的雜草。你喜歡雜草叢生的自信,但也想看看冬日不那麼荒的花園長什麼樣。你在地裏勞作一整日。播種,搭架,綁藤,澆水,施肥,剪枝,移植。薔薇的花苞長了出來,紫花地丁和月見草,開得正好。蔦蘿的芽發出來慢了一步,它們還小小的。一日勞作之後,人不勝疲憊倒頭就睡,而第二日清晨起來又有更多的杂草待要拔除,更多發芽的秧苗需要照料。如此日復一日,人便貼近土地而生活。
泥土滲進指縫,你想起了「四月」——那是四月一號你在農場門口撿到的一隻小猫。它全身黑色,但爪子和尾巴尖是白色的。它那麼小,發出的叫聲卻能傳到很遠的地方,至少讓你聽到了。它黑色的眼睛望著你,像是一個等待被認養的孩子。你於心不忍,把它帶回了家。你翻箱倒櫃,找到一根火腿腸,你切成小塊,放在盤子裏,它一隻前爪抓住盤子,吃得狼吞虎嚥。於是,你走到哪,它就跟到哪。你把它放在口袋裏,抱在懷裏。它喜歡睡在你的腿上、你的枕頭邊,或是有陽光的地方。有一天,它蔫蔫的,接著,它不吃不喝,後來,你就找不著它了。你知道它一定躲在什麼地方,等待死亡的降臨。這是動物的本性。幾天後,你找到了它。在月桂樹下的雜草叢裏,它躺在那裏,像是睡着了一样。只是它再也不會站起來,豎起尾巴、打著呼嚕在你腳邊來回打轉,再也不會四腳朝天地躺在地上、向你袒露最柔弱的腹部,等待你的撫摸。
你回到小木屋,取了一件磚紅色的T恤,蓋在它身上。你拿起花鏟,就著月光挖了起來。挖掘並不順利,因為石塊太多了。彷彿這棵月桂樹是種在石頭裏而不是泥土裏。你出汗了,挖坑的右手又酸又累。當你把它放進去的時候,才發現它的後腿放不下去。你抱起它,忍不住哭了。這僵硬冷卻的身體已失去了往日的柔軟和溫暖。你知道,你需要它多過它需要你。你脱了外套,扔了花鏟,用雙手刨土,你要給它挖一個尺寸合適的墳。
你把它埋了,將你的羈絆也一併埋了進去。你曾經想像,它茁壯成長為一隻成年大貓的樣子。你想是名字沒取好,它終究沒有活到六月。許多人也一樣,等不到這一年的盛夏。東亞豆粉蝶停在紅車軸草上,滿院的一年蓬在謝去。你直起腰來,滿手是泥,你看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
(四)
「我走了。」你接到了她的電話。你有點意外,但也在意料之中。你認識的許多朋友,不是已經離開,便是在準備離開。現在的你,比任何時候都擅長告別。當你想到從今往後,你要獨自面對一切時,你反而很平靜。
她說離開的路上並未遇到障礙。只是在過交界的大橋時,被看守的人詢問了幾句。「回家」,她說。看守的人放了行。
「我害怕被遣返。」
「不要怕,你現在安全了。」你安慰她。
「只是暫時的......飛機場擠滿了人」,她擔心那位抱著妻子骨灰的七十歲老人,仍滯留在機場,「你也離開吧。」
「不,我要留下來。」你說。
「為什麼......」她在電話裏哭泣。
你沈默。你們都知道原因。在她離開的前一夜,你們為此爭吵過。
「我覺得......」信號突然變弱,你聽不清她說了什麼,只聽見四個字,「起死回生」。你從她的聲音裏聽到了一種希望,只是這希望是她的,不是你的。你為她高興,同時你也感到不快。你沒想到她這麼快就忘記了那些不堪,好似倒掉了一盤隔夜菜一樣,餿味也一併沖洗乾淨了。
「你要勇敢一點。」你們異口同聲。
(五)
外面的割草機響了。 你感到煩躁。你從床上坐起,拉起窗簾,烏雲壓了過來。天氣預報說,暴風雨將在零點到達。那個身穿黑色皮衣,戴著護目鏡的男人,又出現在院子裏。野草、雜草倒下了,野薔薇也倒下了。他手持武器,一往無前。他渴求泥土的芬芳,如同渴求鮮血的味道。
在颱風來臨之前,你煮起一鍋水,餃子在一旁等候。新年在倒計時,豐收的慶典正在緊急籌備。割草機又響了,太響了!鼓掌的聲音,太響了!鞠躬的聲音,太響了!你不想捂住耳朵,你想發出巨響。這巨響來自你的喉嚨,這巨響來自你的呼喊。此刻,外面的雨下大了,風也很大。你的小木屋搖搖欲墜。你用力地,大口地,呼——,你血脈僨張,你咽喉腫脹。呼吸本身堵住了呼吸。
水開了。你被淹沒了,海草纏住了你的喉嚨。如果你想發出的巨響不是夢話,那麼你就要將暴風雨吸進肺部,而暴風雨的闖入將撕裂你。為了發出這聲巨響,你將自己排盡。為了發出這聲巨響,你必須倒下。
你倒下。你倒下,但你不害怕。你吐出你的害怕,在連續的痛叫、間歇的呻吟中。你在瘋狂的冰凌聲中撞向柱子。他的聖殿,會倒嗎?你不仰望,你不瞻仰。把詩人關進精神病院,將異教徒從城市驅逐,把你流放在你的故鄉。你不祈求。你倒下。你倒在土裏,和野薔薇在一起。你不出來,你不再出來。你聆聽,來自你傷口的回響,「噓——,聽,種子在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