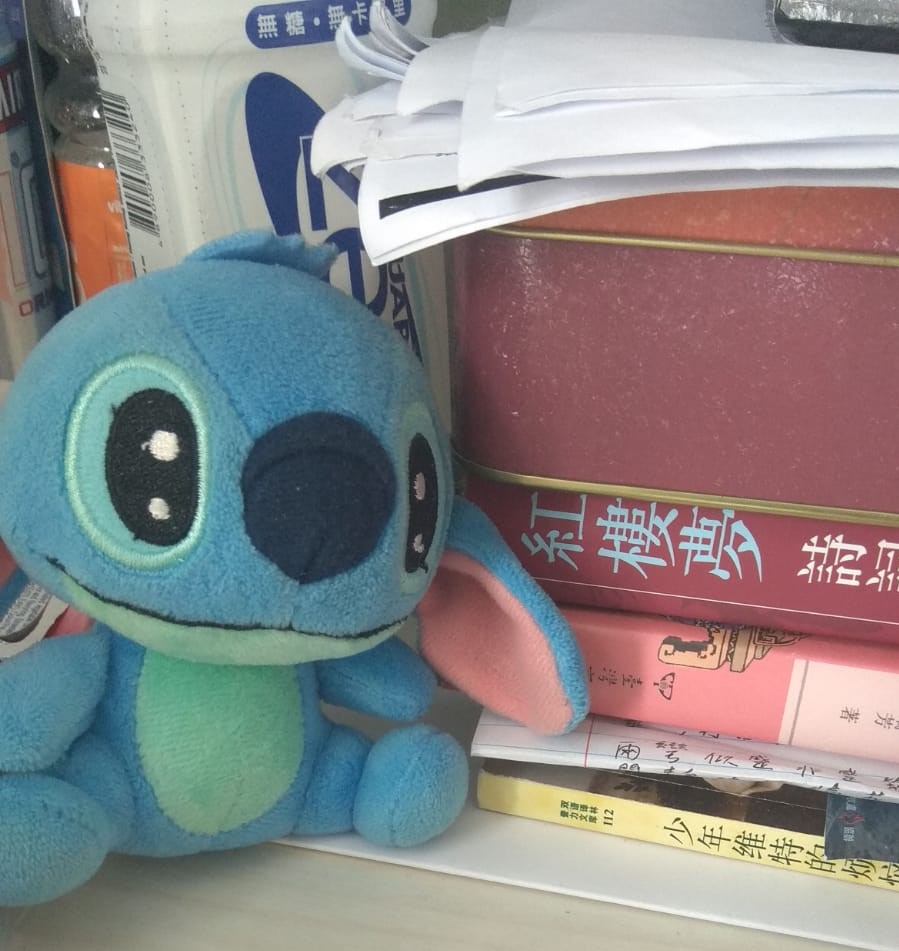【虛詞.癢】恆.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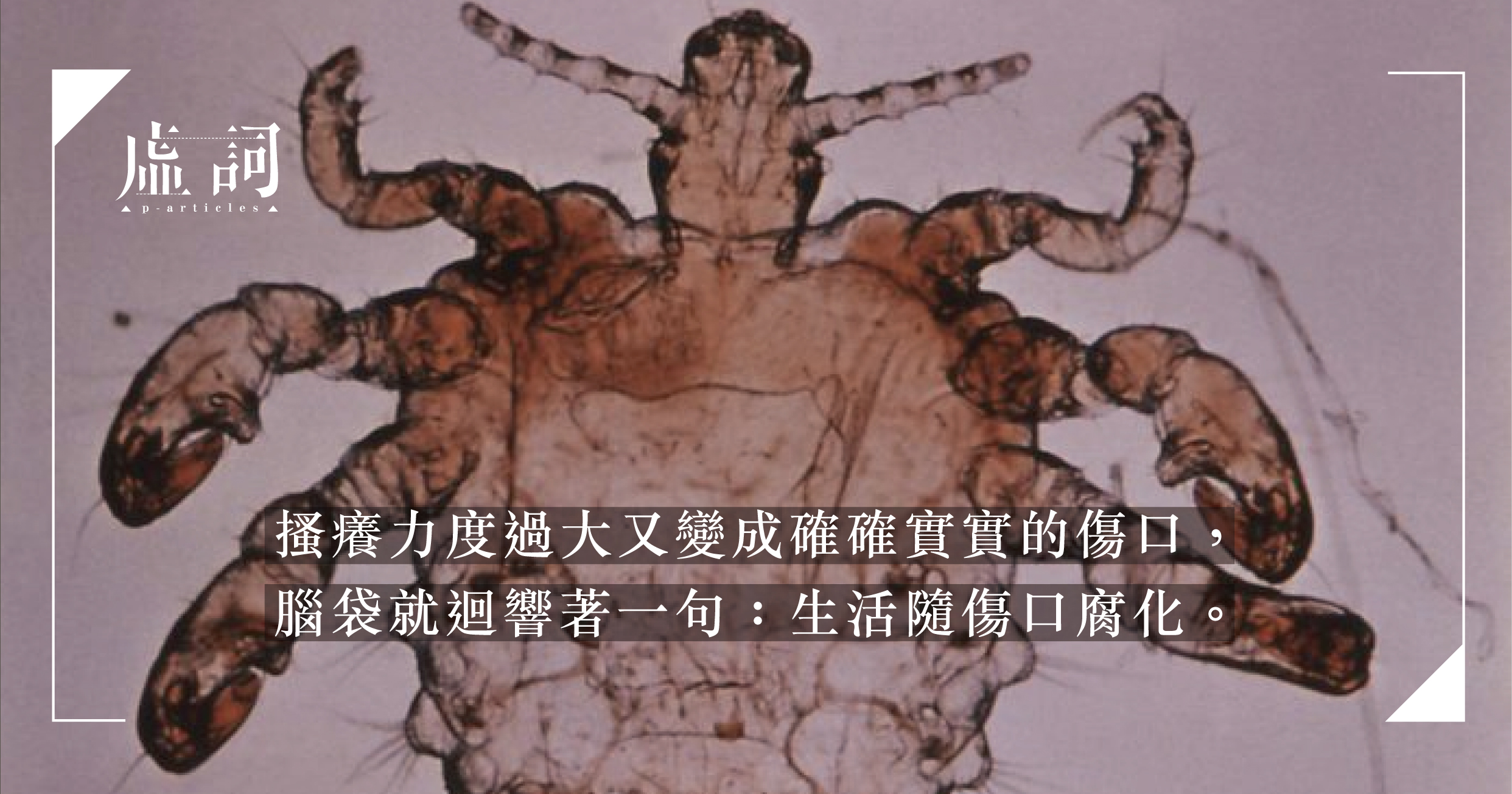
OG09-09.jpg
張愛玲十九歲時,寫出散文〈天才夢〉,不知贏得了多少讀者的喜愛。人們最為津津樂道的是結尾一句:「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她貼切地對自己的天賦與困境作出比喻。出身於沒落的書香世代,先天擁有出色的背誦能力,孕育出繁盛的文字、過人的洞察力,但多年來自理和社交能力幾乎毫無長進……這些雖不至將她咬到半死,但她也因此受過不少苦。
八娣讀到此書時,慶幸自己沒有這樣的煩惱,她社交能力算起上來,得過且過的還未算太差;至於背誦能力,自小就只有她母親還讚譽她幾句。八娣成績未如理想時,當母親的就能輕鬆結案陳詞,將之歸咎於八娣的懶惰。八娣大了才開始極力否認,像古裝劇中的罪人,跪下求饒般真誠地想母親收回這想法。寫作呢?最引以自豪的,就只有一兩位老師寫過評語予她,覺得她是有兩分頭腦,乃至於畢業那年的考試中,考獲全級最高分。八娣有點疑心,是因為她以抱恙的狀態去考試,寧靜的考場中,嘔得人人皆知,傳到老師耳裡。這樣的高分是種施捨,但多年後她也不想去弄清這猜度是否屬實。
她不想弄清的事太多,單單是記得一件可有可無事,那還好,就怕弄清過後又要決心忘記,則是件費神而不划算的事。
有人說風癩一生只會生一次,八娣回想起她的風癩經驗,雖是狀態可怖,但因為不用上學,又有點有趣而愉快。那天早上,朦朧醒來,父親少見的一面惶恐,有點緊張,小學生那知風癩是甚麼,一看便是驚訝,第二個動作就是去搔它,一粒一粒,質感甚佳,像看到泡泡紙時,情不自禁地去逐個按,換來莫名的滿足感一樣。小朋友,連自己身體也是玩具,每一部份也是,無聊但賺取了簡單的滿足感。如此病患,當然不用上學,直接就被母親帶去看醫生。路上,包得密密實實,密不透風,母親道是有了風癩不能吹風,八娣覺得自己是患了古時致命的麻風病,死了還好,那時的她,太怕一個人,受不了被歧視的目光。
這樣的風癩後來因為食物敏感,又再來訪多一次,但是同樣的不消兩天就完全康復。這是八娣頭一道清楚地記得,問道為什麼是自己,為什麼她要有要此病患。
她六歲時,一位天王巨星受不了抑鬱症的折磨,從高處跳下,在遺書中也曾如此相似地問道。
八娣沒有那麼嚴重,也未曾懂事,沒有砰然一聲殞落,只有似有幻無的患處。往後,類似的問題漸漸問得多了,而大多都沒有答案。
踏上青春期,八娣有了最任性的時刻。午休、放學便去球場,落得大汗淋漓,長久積累下來,便發覺某些皮膚都給搔傷,脫皮,變色,因為長久的汗液積累,真菌入侵,她又一癢便搔,結果八娣也有了自己的長期戰爭,和真菌長期撕殺;八娣的青春期也比一般人遲,可能如此,她的發育也比一般人強悍,似是一種償還:長高的速度令人咋舌,而縱慾也誇張得很——她過後才知。
那是場不堪入目的敗仗。
在任性過度後,她走上自修的路,這是她確確實實的一種償還!在美好的自修計劃裡,雖沒有早睡早起,但每天中午要到圖書館自習,無時無刻都警剔自己,從前是懶惰夠了,長高了,看遠了,再經不起那樣風光明媚的奢侈。
想像總是美好,但後來回想,現實也未免過於不堪。
自修就似是在一望無際的海洋浮浮沉沉,望不見盡頭,而單單是一窗秋月,等著月落日出就夠數到手指累透,但腦不肯入睡,容許著寄居在內的慾望,一點一點把它吞噬。依稀可見銀色的窗花被塗上一點點月光的粉末,就這樣等,原先覺得腦袋會先睡去,但不知何時風吹微光滅,是重重覆覆的黑暗,重重覆覆的酥癢,一種慣性,還有忍耐之後,擺脫不了的結局。八娣那時開始熟知每季的日出時分,而大多都是抱住對自己無限的失望去看,月芽會變,紅日依舊,像她掙脫不了的慾望枷鎖,避了一時,則如月有盈虧,終會來臨而不能自控。
空白的腦袋在最滿足的一刻過後,說過一句,它會使八娣的所有都毀於一旦,而僅僅是因為一個慾望,那是如同黎明前的昏暗,任何光芒都倍加耀眼,預示、倒數著不能正視,恐怖得刺眼的段落將終結,然而,只有一天是新的,其他依舊。
八娣偶爾會夢見小時那次風癩,不能自已的去搔癢,但她覺得自己畢竟是要長大了,小朋友的快樂是短視,但因為合理,所以可以接受,中學生為了一時享樂而殺掉自己的責任仍可以青春為由作盾,再設法挽救,但到了一定年紀,身邊的人都通通扶搖起飛,就只剩她原地踏步,她又會想起那個問題,為甚麼是我?
長夜漫漫,八娣可以想的事很多,記得她小時很多事也很好奇,周圍去發問,現在的她,有時盡量都想去懶理,那些經常問自己的問題都沒有答案,何苦又去追尋題目。八娣也漸漸明白好奇為何會害死貓,但貓尚有九條命,八娣的命只有一條,她倒想自己是部手機,一按就是睡眠模式。這樣的等待無差於消耗生命,誠然,如同張愛玲的孤僻,或是如白先勇一樣隔離人群,沉到昏黑的汪洋深處獨想,也並非全是壞,未知的地方令人恐懼,亦埋著最鮮為人知而迷人的寶藏。
她感覺心中天秤有點分崩離析。
八娣的腦筋還未長進,最多的時候都是在想念曾經最愛、最重要的人,一回想都不禁幾番竊笑。曾經有這樣的一晚,大家都在仰望同一樣的桂月,年月流轉,幾回寒暑,桃花依舊,煙花卻早已冷,他身邊是有了人和他成雙成對。說來可笑,慾望沒有來的時候,正是痛哭流涕得天昏地暗之時,大抵眼淚漲潮得淹沒那慾望的居所,也淹沒極顆腦袋,整個感覺就似個人就斷了氣,窒息中,但又死不成。思念就似是塵埃,看不見,而八娣總感到它是無處不在,如影隨影,但這次是如何搔都是如隔靴搔癢一樣,是好過沒有,但依然的痛苦難忍。有時覺得隨影的塵埃都只是身外物,只有一個人蜷縮於被窩時,覺得是深入骨髓,搔不得,最怕一世都會是這樣,一樣是無盡頭,沒有終站,最為驚心動魄。想到此,試過枕頭上的淚痕,一大灘,有不甘,有絕望;也有麻木過,眼水滑不出眼眶,於是甚麼也清楚得很。
凡浮腫起來的,果真是要到搔穿了,吃痛,才肯忍手。
好了,搔癢力度過大又變成確確實實的傷口,腦袋就迴響著一句:生活隨傷口腐化。
這是八娣讀副學士時想起,八娣房間也換上了更不透光的窗簾,沒有月色,甚麼也沒有,只得幽暗、幽靜,困在一間房,統統走在一條直線上,無盡延長、伸展。傷口腐化至少有一個好處——不敢去搔,擺在這裡,沒人知曉,嚇不了人,也足夠提醒自己,別亂碰,也別去招惹新的患處。那當然還會癢,世界本是五光十色,外面的世界多精采,但在八娣眼中,一概都是如同看到金陵十二釵般無奈,因為總凝著是早已塵埃落定,至少自己的那一冊是。八娣也想跨過去,但總怕傷口會撕裂,就躺著,在等。
從前的夢中,總有父親那一面驚恐的輪廓,也有母親一面擔心的剪影,都在面前,走在身前,影影綽綽的晃動著。但醒來,發覺上學的路程都已是遙遙的九龍,都是一個人在走,也要一個人走。
小孩的病痛,哭啼幾聲,也總有人發現。人不得不大了時,愈來愈多事要獨個往肩上揹。對八娣而言,與真菌的戰爭依然打得如火如荼,還是靠當初父親的方法,以皮膚水去消毒,但由於痛入心扉,所以堅持不了下去,但又屢敗屢戰,因為太癢,癢得有點過份,總在迷糊的時候,難以不犯禁。患處不易見,這仗八娣只能獨戰下去,因為只有自己知。每次痛入心扉,痛得很,但都是快樂的痛,因為作對,如同那種走在正途上,踏實的快感與成功感。
小孩的正途都是有所規劃,送著監管。八娣可以想到母親如何怕她在人海茫茫中掉失,八娣也不能沒有母親,一出街,與母親緊握的手就不易放開。到發現自己的手比母親大,手指比母親長,八娣只有拿著自己手上不似樣的地圖,慌慌張張獨自去探索,去犯錯,去負責。我們有林林種種的目的地,也有無人過問,也非旁人能想像之痛與癢。「遊戲就算愉快,不會幸福」,八娣很愛哼著。短暫的快樂總是簡單,但精砌玉砌的,都是慢工雕成的,八娣這樣對自己說著,每晚也是。累了,呆望枱面一瓶安眠藥,有時就一整晚對望著,數著數之不盡的酥癢,全都是遙遠若近的戰爭,有些是沒有盡頭;一盡頭,八姊的靈魂也就是結束,看得見只有行屍走肉在等,等著斷氣,然而,八娣相信這世上,只有這種等是毫無意義。
所有的殞落都煞是可惜,但就算紅樓中,都有過一夢。發棄去放亮,放任靈魂放涼,沒有意義,沒有。
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上面爬滿了虱子,張愛玲用一句概括了自身背負的世界,有璀璨的才華,也有鮮為人知的缺陷,但她寫下那句子時,也不曉得自己晚年會與蟲抗爭,幾度搬家,她身邊的虱子孰真孰假,幻影還是現實,大概無從稽考,但現實是,人生中少不免有蚊叮蚤咬的酥癢過程,對抗下去,走下去的才是人。
八娣發的夢依然是五花八門,但總有熟悉的場面,熟稔的人物角色,有時醒過來會怕,會有淚痕在臉。八娣依然在走,走得時慢時快,因為未看見斷崖。
無盡的等待中,回過頭來,總算有點甚麼可寫寫了。
那是一兩天的酥癢過程,八娣對這點是滿意,心裡笑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