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詞.癢】心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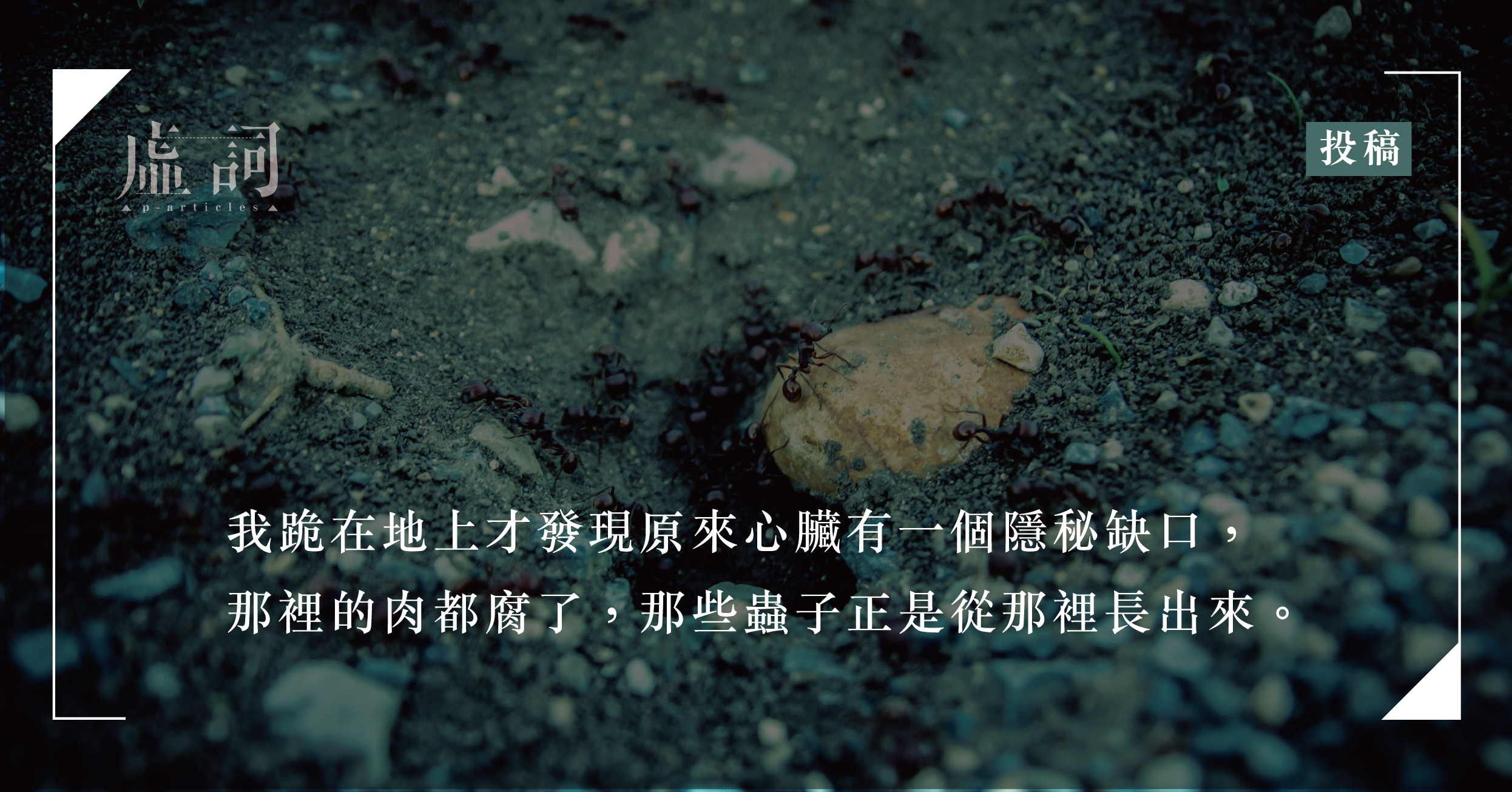
心蛆圖-01.jpg
癢是從心底顫抖著爬到耳窩的。像蟲子。咔咔聲,緩緩的。
我不自動地抖了抖身子,尾指便自動反應過來,手指探進耳道。末了,把手指擺在眼前細看,耳屎碎掛在指縫裡。鏡子中的那個人向著指甲一吹,左右環視,把手指湊到鼻孔前,輕輕地索了口氣,又放鬆地嘆息。
自己的味道,止住了心癢。
第一次心癢是因為一個夢。我夢見自己又到了湖邊,在我還有雙腿的時候。我曾在這片湖泊中紮根過,然而在夢裡,我的位置消失了。
湖說:「對不起,這裡已經被易手了。」
我是被癢醒的。我看著成群的飛蟲跑到耳朵中,眼珠裡,喉嚨處,無法制止。我急得淚水都冒了出來,也無法好好說話。我從鏡中看到她,樣子像嚴重過敏,趴在床上狼狽地翻找著,卻再也無法找到她的解藥。
她嗚咽地抱著頭:「停下來。」於是癢變成一種火燒心的胃疼,蟲子沉甸甸地在腹部竊竊私語,等待伺機再次發動攻擊。
蟲子從來沒有死在腹中,於是我也就學著與之共處。一開始稍有動搖,蟲就會群起攻擊,慢慢就發現自己的氣味能安撫躁動的蟲子。所以我學會了獨行,利用純正、不加雜質的個人味道,養育著蠱蟲。
「這種癢是因為你牽掛甚麼了吧,」朋友A瞭然地道:「像是我不喝咖啡總會心掛掛一樣,都成習慣了。」朋友A的手指上了發條一樣攪拌著咖啡,勺子跟杯有節奏地哼著單音。
我有天告訴朋友A我的秘密。只是我沒有告訴她,我已經很久沒有對一件事習慣,因為害怕著習慣變成依賴,蟲子會全部醒過來,猛烈地撕扯噬咬。現在,我覺得我失去了腿,但我很安慰,我好像活成了一根無根草,隨處漂,也很是安全。
「不是這樣的。」那個湖低語。確實不是這樣。我的確曾經習慣一個人,但現在,我也已經習慣了一個人。
我有天偷偷跑到湖那裡去,那裡豎了個新牌子,湖的確有了主人,因為那個人的笑臉,湖邊都種滿一簇簇的花,陽光灑在湖面,是我不曾見過的波光粼粼,此景是我從未有過的風光明媚。
忽聞身邊冒起「窸窣」的異聲,我低下頭一看,只見蟲子啪答啪答地從我指尖跌下來,它們在掙扎蠕動,一寸寸地蠶食這片草地,蟲子尖銳的牙在咬斷草根,恨恨地。
那湖的主人聞聲而至,看了眼蟲子,又悲憫地看著我,宛如在看著其中的一條蟲子。我只來得及偷瞥一眼,便匆匆離去,我確信我不是蟲,也再不是人,我只成了裝滿蟲子的容器。比蟲更不堪。
就似是定格了數年的心臟忽然再次跳動,我終於反應過來這些蟲子、這些癢,是多麼的讓人厭惡。牠們扭動白胖的身軀,毫不在意地疊在一起是多嘔心。雞皮疙瘩掉了一地,我終於吐了。
我跪在地上才發現原來心臟有一個隱秘缺口,那裡的肉都腐了,那些蟲子正是從那裡長出來,牠們吃著腐肉,長大了就從大動脈順勢游走,佔進我的五臟六腑。我忍著痛,把壞死組織慢慢除去,那原本近乎壞死的心,像被剝的洋蔥,我鮮血淋漓地感受椎心之痛。
我做了無數的夢,繃帶也用完好幾箱,反反覆覆的檢查,再也沒有蟲子,也不再出現癢。我終於能平靜地走到那裡,再一次偷看那面湖。
那個主人依然把湖打理得井井有條,湖邊多了一排果樹,果香怡人。那曾經被蟲子玷污的那小片草地上,生出了一叢叢金黃的向日葵。然而明明應該已經杜絕的蟲,我仍然感覺到牠們在往我心尖上攢動,在眼眶裡蜂擁而至。我跪在地上,忽然明白過來,醫治太慢了,腦子的神經都被嚼光。
那熬人的癢,依然在幻想中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