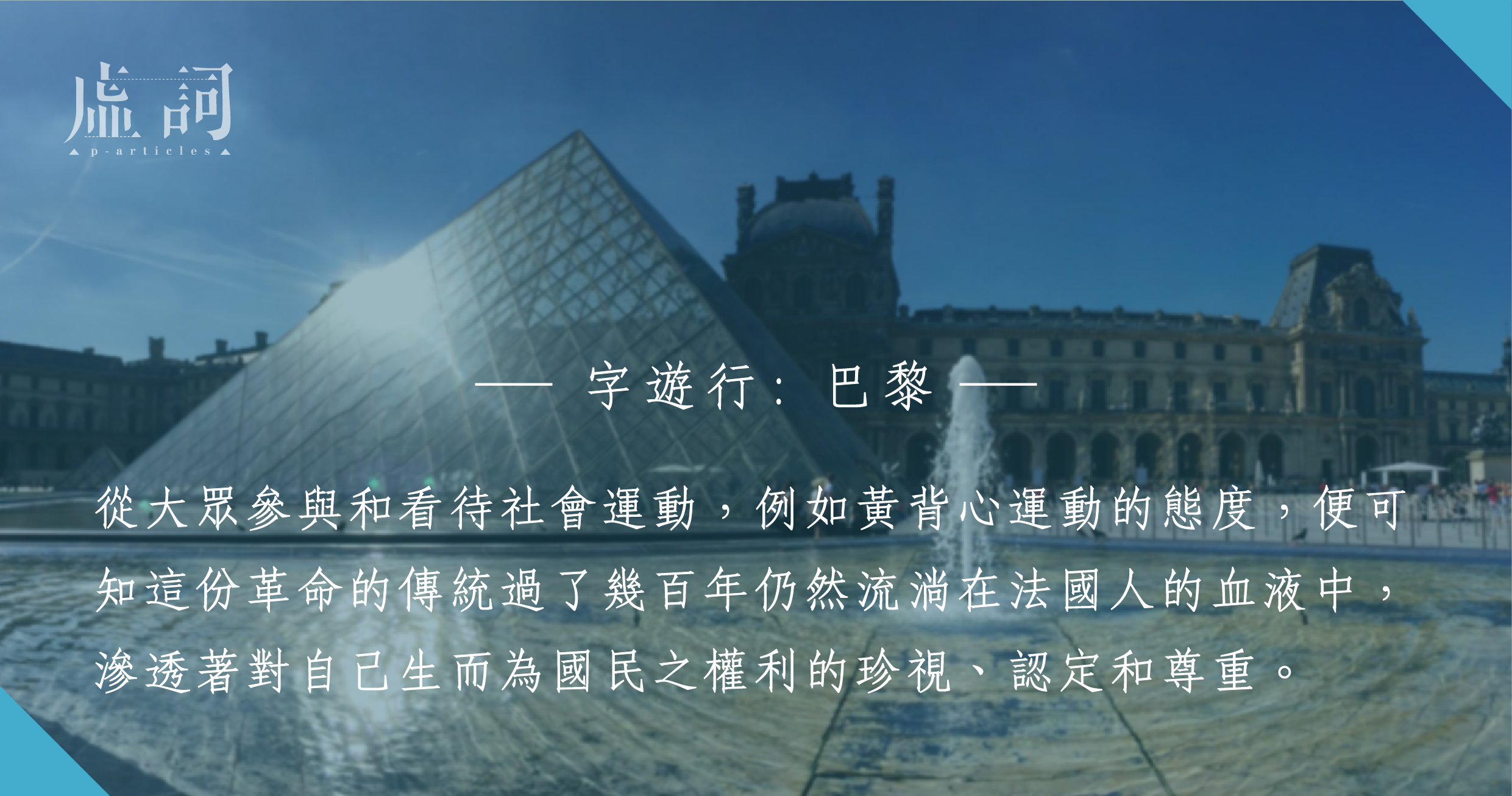【無形.金牛座】沒有金的金牛
我是連十二星座的次序都數不出來的那種人,但出生必有時辰,那麼就十二個之一總會中一個,而我抽中的是金牛一隻。自己沒有甚麼研究,卻常會和朋友談及我到底哪裡金牛了,而被說中了的部份老是令我很驚奇。 (閱讀更多)
【無形.金牛座】金牛化的虛幻紀錄片
散文 | by 張鐵樑 | 2019-11-07
對真實定義得愈實在,這種東西就愈是虛浮和不存在。反過來,真實不是要去定義,而是要去「接近」,這也是我現在辦「香港真實影像協會」的初衷。 (閱讀更多)
【字遊行︰緬甸】以守塔者之名
第二天清晨,天未光我嘗試抵著冷風騎機車去爬佛塔。因為2016年大地震後佛塔群嚴重受損,政府勒令把通往塔頂梯子前的塔門鎖上,現在可以爬的塔便愈來愈少,進出的門前都有鏽跡斑駁的鐵閘。那個清晨找到的,是一些遊人已經爬上卻無名的塔,他們大多都有嚮導伴著前來爬塔。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