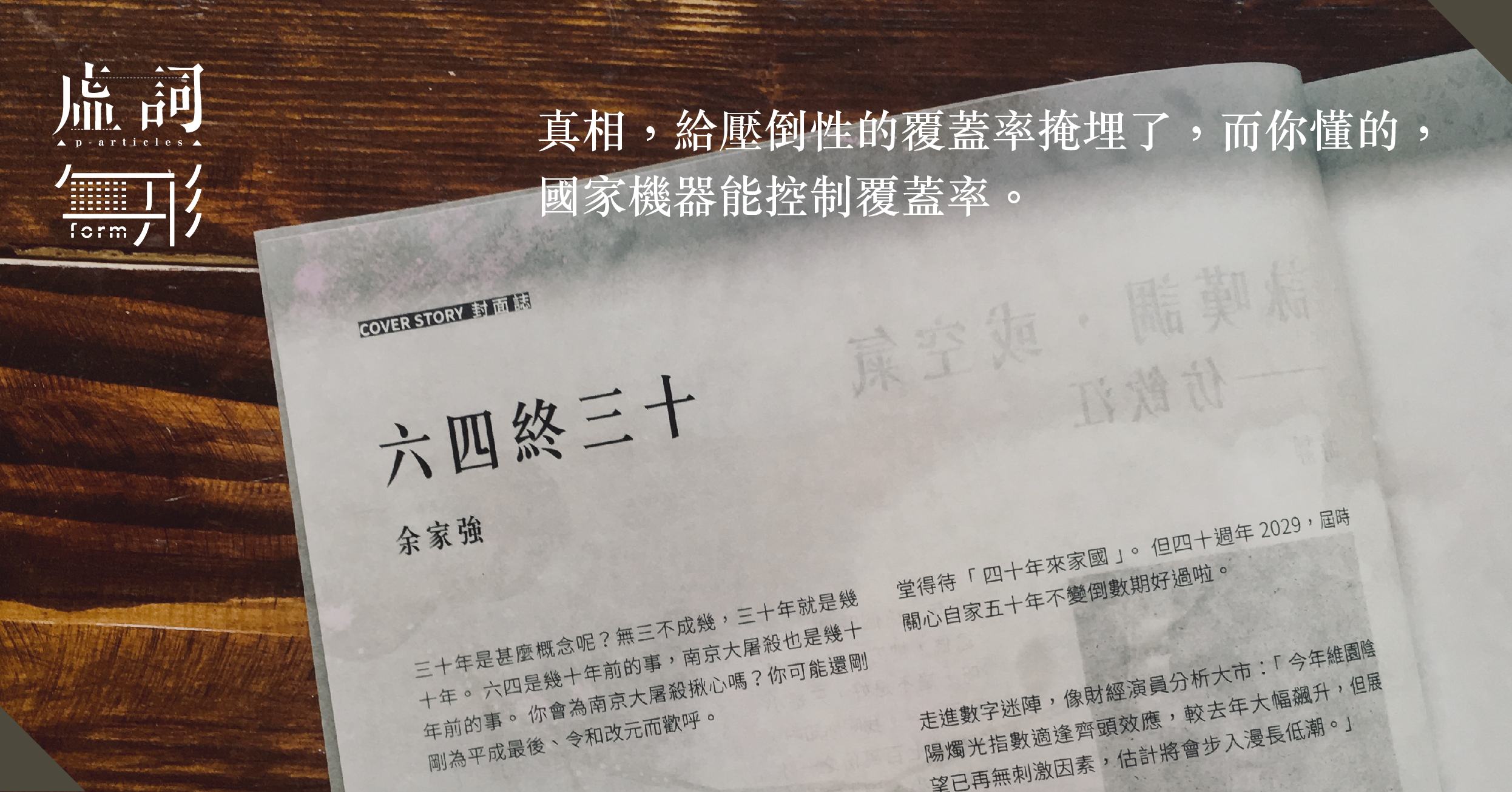【五月三十五】詩輯:白魚蠟燭倒下燃燒了一卷雅歌
詩歌 | by 淮遠、廖偉棠、李顥謙 | 2021-09-23
為六四事件撰詩,不僅是紀念,更是藉以觀之今日香港,提出反思:「晚安,香港!/飛站的列車,我們都是乘客/不再抓穩扶手,因為雙手都拎滿炸藥。/昨天沒有骨灰,留給明天的飢餓。」 (閱讀更多)
【五月三十五】茶座旁邊的戰爭與和平
我這一代香港人,沒經歷過真正的戰爭;我最感受到武力張狂的時候,應是二零一四年雨傘期間。當時我每星期有一門夜課,課室窗外是尖沙嘴警署附近的大馬路,授課中途,常有警車出動,「嗚嗚」笛鳴與刺眼紅光闖進課堂中,我和同學都沉默下來,望出窗,想像警車要往何處去,將要發生甚麼。那些日子的課堂,與現實生活是平行時空。 (閱讀更多)
【字遊行.古巴】夏灣拿日常
字遊行 | by 柴子文 | 2019-05-31
我們從墨西哥坎昆做落地簽再飛往夏灣拿,但託運的行李箱卻不幸被滯留在了出發的三藩市,需要等待數日才能運到夏灣拿。心中忐忑,必須做好最壞打算,找不回一整箱的行李,要做減法,從零開始「生活」。 (閱讀更多)
大陸網絡小說新禁令!寫及性相關是高風險!網民:中國特色柏拉圖網絡小說更誘惑
其他 | by 李元巢 | 2019-05-29
柏拉圖式網絡小說,說的不僅是不能有性愛場面,是連「嘴唇」兩字都成為敏感詞,那還讀甚麼、寫甚麼?還有網友一針見血充滿內涵地回覆道:「在BL同志漫畫小說都被命令禁止的中國,你跟我談柏拉圖?」哦對,最近連諾貝爾獎得主、中國共產黨員莫言最近都遭習近平點名批評,紅高粱影視基地遭到強拆,這樣看來網絡小說可真如螻蟻,一捏就爆。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