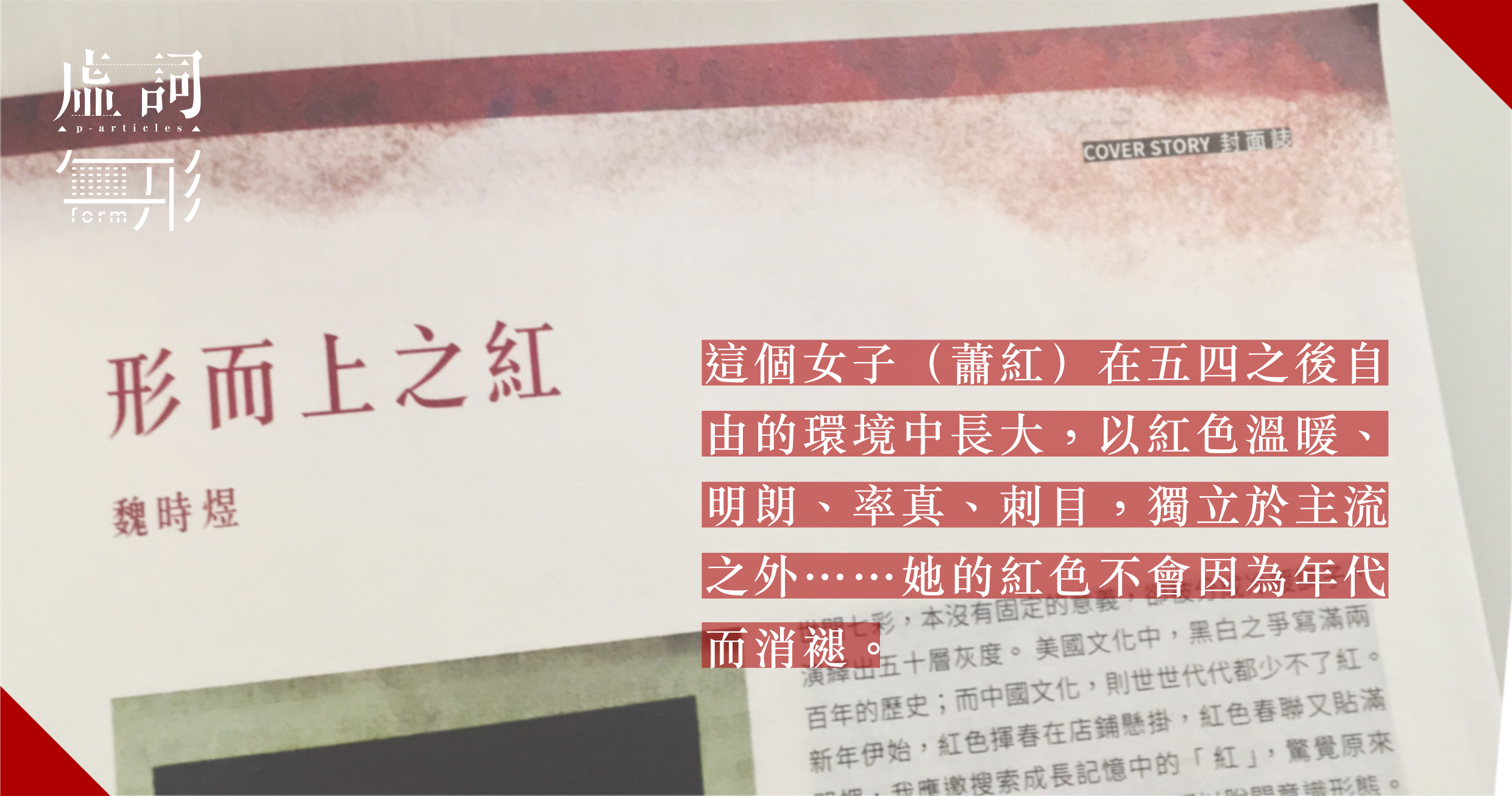【無形・紅】形而上之紅
散文 | by 魏時煜 | 2019-02-22
世間七彩,本沒有固定的意義,卻被分成冷暖調子、 演繹出五十層灰度。美國文化中,黑白之爭寫滿兩百年的歷史;而中國文化,則世世代代都少不了紅。新年伊始,紅色揮春在店鋪懸掛,紅色春聯又貼滿 門楣,我應邀搜索成長記憶中的「紅 」,驚覺原來我所有關乎紅色的記憶,竟無一可以脫開意識形態。
二尺紅頭繩
小時候爸爸經常出差,家裡還沒有電視,大床是用兩條長凳支起來的床板,可能還都是公家財產。媽媽最甜蜜的記憶中,有我把大床當成舞台,晚上睡覺前給她表演《白毛女》,把一床棉被當成楊白勞(看看這個名字起得多麽犀利,簡直說盡了貧農的人生)。據説我最喜歡唱的一曲是《哭爹爹》:「刹時間天昏地又暗,爹爹、爹爹你死得慘。鄉親們呀鄉親們,黃家迫債打死我爹爹。」我朦朧記得至少在劇場看過五次芭蕾舞劇《白毛女》,至於為甚麽愛唱這一首,卻不得而知。小學的時候和鄰居小朋友一起學唱越劇《紅樓夢》,我最喜歡唱的也是《哭靈》:「林妹妹啊林妹妹,如今是千呼萬喚喚不歸,上天入地難尋見。」媽媽對我這兩段並無忌諱,十分欣賞我的表演,而我隱約記得唱高腔時候的爽快。
八個樣板戲中六個是現代京劇,只有《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是芭蕾。「白毛女」的名字叫喜兒,她剛出場的時候,紅衣綠褲,十分歡樂。爹爹為了過年還給她買了兩尺紅頭繩,我覺得穿紅色的她真美。可惜「舊社會人變成鬼」了,喜兒後來從地主家逃回到深山中,頭髮全白了,衣褲都成白色的了。我最喜歡的舞蹈,就是喜兒開場時跳的《北風吹》。據説幼稚園時期,我有一年時間都是自己坐在一個角落和自己玩。但是大班時,有個挺喜歡我的年輕女老師,在畢業前的一次演出中,還特意讓我獨舞了一次《北風吹》。不過在買布要票的年代,沒有人可以為了這個小小的演出做一身演出服,而我整個童年、青少年時期也沒有一件大紅色的衣服。
記得我有兩件燈芯絨的外衣,一件棗紅,一件湖藍,都是表姐的。有一天,老師和同學們都站在幼稚園的小電視前,跟著電視裡面的人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我覺得很好笑,笑出了聲。喜歡我的女老師打了我一巴掌,我抬頭看到她臉上滿是淚水。第二天,我穿著湖藍色的衣服準備上學,鄰居有位很愛我的任阿姨給我戴了一朵小白花。她表揚我說,「周總理去世了,小煜真懂事,穿的是藍色衣服。」那一年,朱德、毛澤東也跟著去世了,可能後來一直都在穿藍衣服。
紅衣少女
幾乎一踏進中學,我就被收編進入學校的「紅領巾合唱團」。我們班六個女生,很受音樂老師重視,常常除了大合唱,女生小合唱是我們六個人,四重唱就是我們中間四個,我和周繼寧還有個二重唱。我們合唱團曾經在市級比賽中三連冠,可見我們的音樂老師是很有水平的。我是最近才聽説,她和丈夫都是福建人,和我父親竟然是同鄉,不知道為甚麼到西安工作了一輩子,退休才回老家。那時我們仍舊沒有演出服,是穿白襯衣、藍色背帶裙演出的,每個人都是戴一條紅領巾。我模仿老師指揮,居然就成了我們班的指揮,於是歌詠比賽可以穿一條和大家都不一樣的粉紅裙子,甚為得意。
那時候經常一個電影出來,裡面陳沖和男主角接吻了,張瑜剪了個短頭髮,都有很多議論和模仿。人們的思想還在80年代的解凍之中,我的同桌還想著長大了要解放台灣呢。有部印象很深的電影叫《紅衣少女》,裡面有一對姐妹,妹妹安然是個學生,姐姐已經成人。安然因爲穿了一件「沒有鈕扣的紅襯衫」(也是鐵凝小説的原題),在學校引起了很多議論。電影是陸小雅導演的,我一直記著這個名字。2014年我到深圳的導演協會去放映《金門銀光夢》,那個房間的投影機因為老舊,每半小時就會自動關機。在90分鐘的放映過程中,關機兩次。但是席間有幾位老導演,抑制不住激動,也確實很少有紀錄片是講早期女導演的故事。放映結束時,有位女士從第一排走到後面誇讚我的電影,原來她就是陸小雅導演!是陸小雅導演!
高中的化學老師是我們班主任。他說一口陝西興平話,我們用了幾個星期才能聽懂他的話,但是有些詞,仍舊是聽不清,比如他說的到底是「純鹼」還是「沉澱」?我們經常模仿他說「氣體的體積」,因為聽上去就是「七七七七七」。劉老師是當年的高考狀元,分配到我們這所重點學校,就被委任負責我們這個重點班,最後要全班考上大學。他有很多説法,我們現在還記得。比如,「酸是革命的,鹼是反革命的」。因爲酸讓pH試紙變紅,而鹼則讓pH試紙變藍。我們會笑這種説法,但是老師確實讓我們記住了這件事。最後我們全班以化學平均分86.5分的成績,全部考上大學。那時候同齡人中,一萬個人,只有十三個可以上大學。
一塊紅布
上大學不久,有個封面紅色的卡帶出來了,上面青年崔健的半側形象,設計成類似報紙照片的那種質感。專輯名稱叫《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很多同學都買了。我們英文系的同學平時都是聽英文歌的,但是不知誰送了我這個卡帶。當時我比較喜歡其中慢一些的歌曲,但是也沒有到癡迷的程度,可能主要是沒有聽出歌詞裡面的第二、第三層面的含義。接著就要開亞運會了,崔健樂隊開始巡演。到了西安,我那些熱情的同學們買不起也買不到票,居然在音樂會中間,擠壞了門,進去了。後來聽説,場上不管男女老幼,都是站著看的,都在跳舞。
其實早在1988年,崔健已經寫了〈一塊紅布〉,沒有收入在第一張專輯裡面。在香港,很多朋友都是通過〈一塊紅布〉認識、記住崔健的。他1990年3月,被媒體稱為「萬人空巷」的那次演出中,用紅布蒙上眼睛,彈著吉他,唱出:「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蒙住我雙眼也蒙住了天,你問我看見了甚麼,我說我看見了幸福。」這可能是中國流行文化中,最有趣的對紅色的解釋。美國詩人、教授江可平說,這個「你」當然是毛,聽這首歌,他腦海中的畫面是手舉紅寶書的年輕人,在天安門廣場上歡呼雀躍。這個情景在我看來,的確和Woodstock聽搖滾樂的年輕人十分相似。後來訪問到八零後朋友,覺得正因為「愛」字從沒有出口,這首歌才是真正的情歌,他完全沒有政治的想像。
我出國留學比較早,聽崔健後來的專輯,都是2005年之後的事情了。崔健有很多演繹「紅色」的歌,除了〈一塊紅布〉,〈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紅旗下的蛋〉、〈紅先生〉裡面都有很多紅色的意象,令人有無窮臆想的空間。他對世界的認知,如他多次解説的,卻還有黃色和藍色兩種顔色,再加上黑和白。拍紀錄片之後才知道,因爲華語歌曲裡面一直不能討論身體和情慾,所以聽他的歌長大的人,尤其男性,對他很多歌詞的感受是很貼身的。他說紅色是激情、革命、搖滾,黃色是身體、愛情、家庭,藍色是理性、電子,他在紅色的海洋中長大,青少年時期開始認識黃色,經過不斷的思考到達藍色,但是每一個顔色都仍舊在他的世界裡。這個世界觀第一次比較完整的呈現,就是和香港現代舞團合作的演出《給你一點顔色》。
大紅燈籠
九十年代我在加拿大開始讀博士的時候,選擇了當時已經紅遍全世界的中國第五代導演作為研究對象。當時這代導演中在西方最受矚目的,當屬張藝謀和陳凱歌。張藝謀是陝西人,對於陝西民俗、民間藝術中的大紅色,情有獨鍾。在電影裡面,他絕對是用紅色的高手,他可以用同一種紅演繹喜慶與危險、情慾與禁慾,有學者把他的美學稱為紅色蒙太奇,絕不為過。《紅高粱》一開場,就是身穿紅色衣服的鞏俐準備上轎。《菊豆》裡面,染布坊裡面紅色的水池,是殺人的地方。所殺的這位,是個為了要兒子折磨、捆綁,用馬鞍子騎在鞏俐身上的老丈夫。但人死後,菊豆和老丈夫的侄子要面對的肅殺的白色,比那紅色更加可怖。
台灣年代出品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就更有趣了,有一套完整的紅色規矩。片中的老爺有四房太太,哪房太太被老爺選中,那晚她的院落裡面就會點上紅燈籠,她則可以享受捶腳的禮遇。久而久之,哪一房要是老點不上燈、捶不上腳,連房内此後的丫頭都會覺得沒臉面。片子裡面受寵的太太才會穿紅色,而鞏俐演的四太太為了能夠多得寵幸,假裝懷孕,一時院子裡點上了長明燈,可惜最後被白褲子上的一滴經血出賣。這部電影當年獲得過金像獎提名,外國人以為現代中國仍是如片中那樣。張藝謀為他的「偽民俗」背上罵名,說他專門揭短,把老祖宗那些齷齪給人看。看戲的人和拍戲的人永遠不是一個思路,這一點任何一個做過電影的人都清楚。張藝謀解釋說,很多東西不能拍啊,性不能拍,他只好用視聽元素彌補禁忌,盡到電影人的本份而已。
這部電影改編自蘇童的小説《妻妾成群》,紅色的視覺卻是張藝謀的發明。企鵝叢書出版小説英文版時,書名乾脆改成《大紅燈籠高高掛》,和莫言的《紅高粱》、余華的《活著》一樣,這些中國的先鋒作家出英文版的書,都是靠女神鞏俐做封面。我覺得諷刺的是,這幾位先鋒作家寫女性的時候,多少都有點厭女情節;我很期待有費穆這樣愛女人的導演再世!後來在《秋菊打官司》裡面,村姑鞏俐仍舊是紅色的棉襖和頭巾。然後小村姑章子怡也是穿紅色,在《我的父親母親》中首次登場。到了張藝謀和香港人合作,《英雄》裡面章子怡和張曼玉都穿紅色,與《東方不敗》中的林青霞一樣,成為武俠片中最炫目的身影。
穿大紅衣服的蕭紅
我已經不記得甚麽時候,第一次讀到女作家蕭紅寫的《回憶魯迅先生》,一開頭,就和別的回憶文字不同:「魯迅先生生的病,剛好了一點,他坐在躺椅上,抽著煙,那天我穿著新奇的大紅的上衣,很寬的袖子。」因為沒人注意到她的衣裳,她問先生,「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魯迅竟回答:「你這裙子是咖啡色的,還帶格子,顏色渾濁得很,所以把紅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訪問了鄧小樺和洛楓,才知道魯迅先生關於怎樣穿衣服的高論,原來早已是幾代文學青年的寶典。
最近一年拍紀錄片《跋涉者蕭紅》的時候,我翻了很多書、問了很多人,努力想找到蕭紅所有的照片。因為她所有的照片都是黑白的,甚至連一張手工上色的照片都沒有過(當然這個上色也經常是不準確的,我小時候就有一張淡紫色的襯衫上色成淺綠色的)。我沒有看到一張照片上有這件袖子很寬大的紅衣裳,沒有看到過梅志提到的配金色扣子的黑色絲絨長旗袍,更沒有看到過史模特萊(Agnes Smedley)在香港送給她的紫紅色的大衣,甚至不能辨認照片上她束頭髮的綢條是不是許廣平幫她選的米色的那條。事實上,除了一張模糊的報紙照片,我根本沒有找到她在香港的哪怕是一張清晰的照片。這些問題,到了拍電影的時候,就成了服裝師要具體面對的問題。好在她的照片都是黑白的,誰也不能過度苛求。
然而我心裡卻以為,這位學名張廼瑩、以悄吟的筆名登上文壇,以蕭紅的名字流傳於世的女作家,本色就是大紅色的。這個大紅,是視像學色譜中最「正」,也即最純淨的八個顔色之一。雖然「蕭紅」這個名字來源於和蕭軍並立的「小紅軍」的諧音,但是這個女子在五四之後自由的環境中長大,以紅色溫暖、明朗、率真、刺目,獨立於主流之外,不受意識形態的影響,始終以自己生命的感受為出發點,在身體可以承受的情況下不停地寫作。正因如此,她的紅色不會因為年代而消褪。直到今天,當面對生活中總會遇到的悲苦與孤寂時,翻開她的一篇文字,我們還是能夠在她的文字散發出的紅光中取暖,並且獲得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