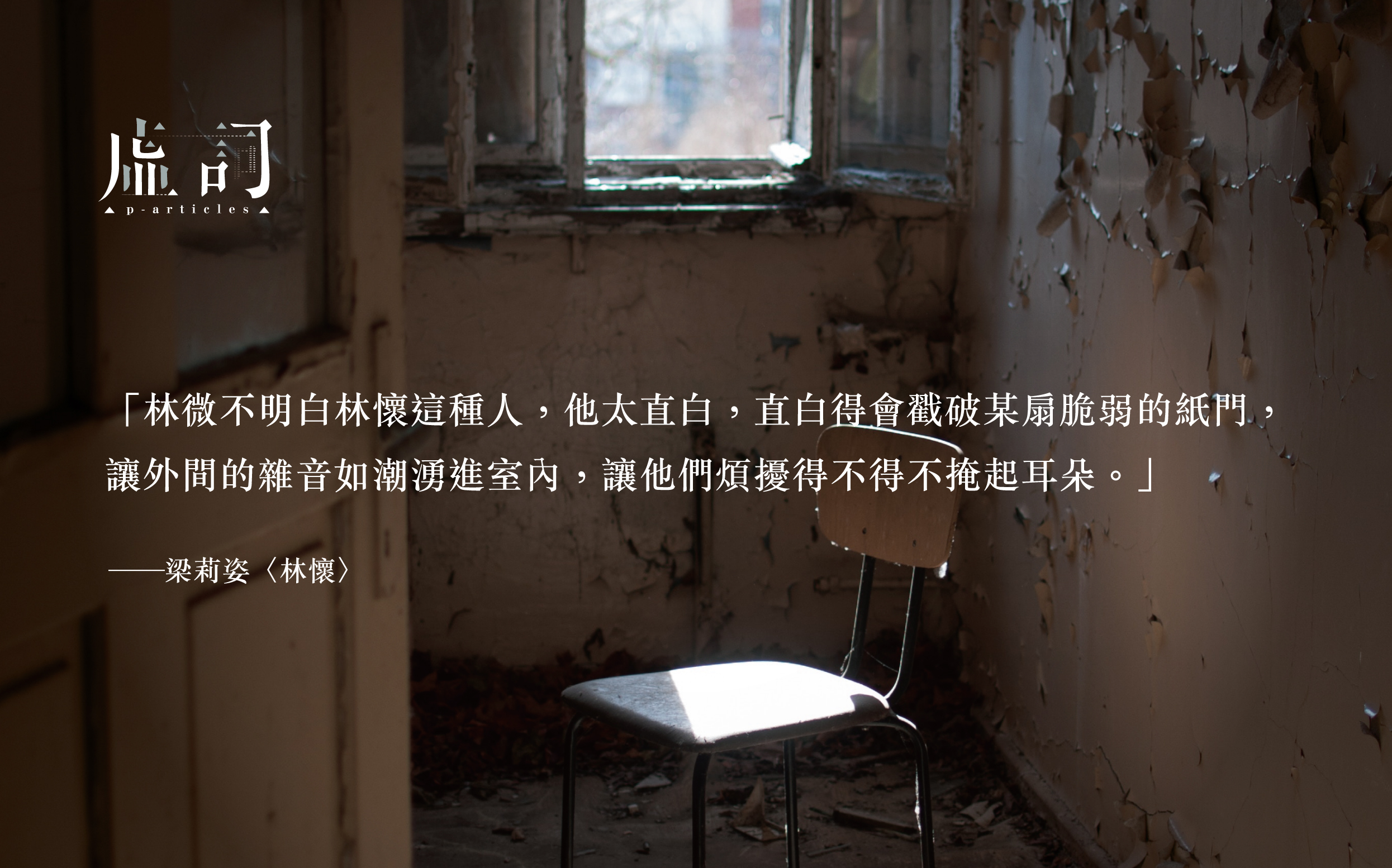林懷
林懷說,不要打開那衣櫥。他們進了那家渡假式民宿,剛拿了房匙,幾個人正歡天喜地左看右看,有一兩個人已一把跳上那軟彈的床褥以某種不太好看的姿勢搖晃,猛說在這床上做愛一定棒呆了,另一個人開了電視,看看泰國有何節目。直到林微剛把手伸向衣櫥,想看看內裡有否即棄拖鞋,林懷忽然冒出一句,不要打開那衣櫥。林微手一下子縮了回去,怔怔聽著他這麼很輕的一句,卻不知應否開聲問「吓,點解」,大概因爲不想聽到不中聽的答案。
林微聽別人說大學幾年可能是人一生中能最頻密而最自由地去旅行的時期,當然不算日後進了甚麼跨國企業得常出國的公幹,或發達後能周遊列國那種。而是以年輕為本錢,可容許自己忍讓或被糟蹋多一點,所以會買廉航,住民宿,太空倉,青年旅舍,旅遊地點大多為東南亞或中國內地。在香港磨人,便到物價更低的地方消費,剝削他人。玩樂渡假一回,又回來上課,生活,被他人剝削。有種微妙的說法是,你被邀請過與多少個團體一同去旅行,便意味你在大學幾年的人緣如何,像一張成績單。林微頗為幸運,努力都有回報,共有四個畢業旅行,其中一個,便是與林懷和幾個師兄,同屆同學去的泰國——林懷會來,也是個意外。
他們是同學系的同學,曾一起籌辦過迎新營,有個WhatsApp group,常聊些有的沒的,都是沒甚麼營養的事,從「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中的大小姐和送水輝戀情,到宿舍裡誰昨晚是否帶了女生回房間之類。群組裡有十多人,只有七到八人活躍,有時有些一直「潛水」的人會退出群組,可能耐不住他們這麼吵鬧。他們沒所謂,也不想開個新群組小圈子,有些沒那麼活躍的間中也會搭搭嘴,林懷屬於這種。直至他們說起組個泰國豪華畢業團,問誰有興趣,好預算人數搶便宜機票時,林懷忽然說,預上他的份兒。大家立馬怔住,林微也愣了一下,程美私訊她問怎麼辦,沒人想跟林懷去旅行啊。
林懷這人沒甚麼,就是太坦白,又剛好能看到「那個」。
他們籌辦迎新營那年,籌委們在長洲訂了家渡假屋,兩層高。地下是客廳,一樓有四個房間,某兩個房間隔著的牆壁掛了幅畫,是個笑得耐人尋味的中年女子,披了條印度紗裙。大家覺得有點不對勁,但沒人吭聲,誰也不願戳破那些可能必須觸及不愉快或尷尬的瞬間。但當林懷走上來後,卻忽然來了句:我們這樣住在這裡,真的沒問題嗎?彼時大家早在宿舍知道林懷能看到那個的「本事」,也對此確信不疑。
一開始是林懷跟幾個同學在凌晨還在寫導修報告,有一兩個組員沒宿舍,只得留在通宵開放的大學電腦室工作。他們五個人分佔兩排電腦,背對彼此埋頭工作。到了凌晨三時多,林懷忽然拍拍旁邊的組員說,你把椅子往前移一點,有人要過。那男生已有點迷糊,依言一移,打著呵欠說好,便聽到有人背後傳來一句輕渺的謝謝,遠得他幾乎以為自己聽錯。他轉過頭,驀然發現,他們坐在靠窗位置,距離窗口只相隔一個座位,而那位子,早被他們的書包背囊佔滿了,如何有人?林懷看到他快要崩潰的模樣,大概想安慰他:那女孩不會做甚麼的,她幾年前趕回大學時交通意外,一直以為自己還未寫完學期報告,才會常常在這裡出現。我也在其他圖書館見過她。
除此以外,還有好幾次類近情況。林懷不是嘩眾取寵的人。他十分踏實,不多言,認真可靠,但在大學,人們會把這種人歸類為真心膠,粗俗一點叫「認真撚」。有些同學把他視作麻煩,主要由於他常會說出一些大家不願考慮或討論的事。看見「那個」是其中一面,又例如他在迎新營籌委的會議上問,會否讓大學學生會來宣傳。他們有點為難,好幾個籌委贊成,但大多數人都認為大學迎新營應是開開心心的,不應牽涉太多沉重話題,也不希望太政治,營主利索拒絕:「我們學系向來是政治中立的,新生們入學後有興趣可自行探索更多,但我們不建議在迎新營中帶入太多政治色彩。」又有一次,節目部在場地安排上跟其他團體協調不了,本應安排新生入宿的時段變成得趕到大學體育中心玩破冰遊戲,於是節目部建議由讓新生先在集合處放下行李,再前往體育中心,而行李則由約十名籌委搬送到小貨車,送往山上宿舍,再由籌委移送到各個房間。
一百多人的行李,大概只有十個人。林懷並不是搬行李的一員,但對這方案極力反對,每次開會都跟節目部部主爭執得幾近面紅耳赤,他執著於這是個不人道而勞役籌委的方案,何以新生有手有腳,就不能自行入宿,場地安排的問題實在不應由勞役籌委作解決,何況此例一開,往後的籌委必定會依樣而行。他們是籌辦迎新營的學生,不是苦力。
拜此所賜,他又在同學間獲得了「原則撚」的新標籤。林微便是此時起對他印象深刻,她是搬行李的一員,卻沒太多怨言,覺得人家讓她做,她便應當做。就像中學唸女校時,老師叫她們逐一跪下,用尺子量裙擺與大腿的距離,她便跪下,在黑板上的十字架前。相信命令比相信這世上有鬼要輕鬆多了,起碼不用與人爭論,解釋。她不明白林懷為何要為這些與自身無關的事,這麼動氣,堅持,為這個原本一天內便能表決通過的方案,爭辯了兩星期,拖延大會進度,甚至更讓大家對他敬而遠之。
林微不明白林懷這種人,他太直白,直白得會戳破某扇脆弱的紙門,讓外間的雜音如潮湧進室內,讓他們煩擾得不得不掩起耳朵。
那次在長洲,大伙兒打圓場說沒事兒沒事兒,幾個女孩隨後放下行李,四處視察。卻不知是否受林懷那句話影響,有種走到哪裡,都會被畫中女子盯著的毛骨悚然之感,便喚來男生們,問能否找甚麼蓋住那畫或把畫拆下來。林懷卻說不好,說那樣會激怒畫中人。幾個女孩一聽,當場尖叫起來,猛說別再說了好嗎?有個男生馬上拉了林懷到樓下。林微剛好得接父母的來電,也到了樓下,聽到那男生(其實就是營主)拉他到屋外,跟他說,他理解林懷能看到甚麼,也理解他那樣說只是在說事實。但有時候,一些事情不要被說穿,可能才是他們需要的。你有否想過,我們不提起,不討論,就是因為不想理會?有些東西,說出後只會讓人不好過,為何你就不能多諒解大家的心情,而只顧逞英雄?
林微躲在窗後,不知道營主有多顧慮別人的感受,但她知道,林懷必然極不好過。因為往後幾天他都非常沉默,而後來幾次籌委會議,他都缺席了。
到了正營時,林懷並沒有被編為搬行李小隊,卻自告奮勇來了幫忙,一人提起了好幾件行李。林微跟他一同跟車,她卻因不知所措而沒有說話,只敢斜眼偷瞄他,他一直看著車窗外,不知在想甚麼。車子到了宿舍,他幫忙把行李分送各房間後,又趕回自己負責的崗位,沒有多說一句話。
到了晚上的夜行,林微又跟林懷編成同組帶隊。他們帶的那組新生玩遊戲毫不起勁,自然也走得慢。走到環迴路,林懷突然拉了她靠右偏一下,又馬上鬆手,低頭往前走。林微在後問他是不是她本來會撞上甚麼,他沒有回答。那是個炎熱的晚上,林微熱得把上臂兩袖都捋到肩上,露出兩個赤條條的肘膊。儘管不知兩者有何關係,但她忽然覺得自己變得勇敢,走上去問林懷,為甚麼他總要做或說這些對自己沒有好處的事。
林懷想了一會,問她,你相信這世上有鬼嗎?她說她是教徒,所以……他打斷她:與你的信仰或教義無關,而是你如何選擇你要相信甚麼,以及你會為了捍衛你相信的東西,做到甚麼地步。
他相信而關心的是,人怎麼活的問題。
林微在那個晚上後,沒再跟林懷說過甚麼話,也沒變成一個執著公理而突出的人。她仍像所有人一樣,穩妥過完這尋常而精彩的大學生活,並於畢業前已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只是在這幾年來某些需要下抉擇的時刻,她仍會驀然想起林懷那晚說過的話,也許這閃電般的回想,也或多或少影響著她成為一個怎樣的人。直至她畢業前三個月,就在大伙兒私下討論該如何禮貌地拒絕林懷時,某天下午,傳來了林懷在大學站跳軌的消息。
一個月後,林微跟朋友聚會後,乘了最後一班車回大學,下車時,看見月台的等候椅上,坐著一個年輕的男子。她定睛一看,正是林懷。
林懷說,不要打開那衣櫥。林微回望他一會,想了想,進了廁所一會,出來跟眾人說,不好意思,我們換房間好不好,這裡的馬桶不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