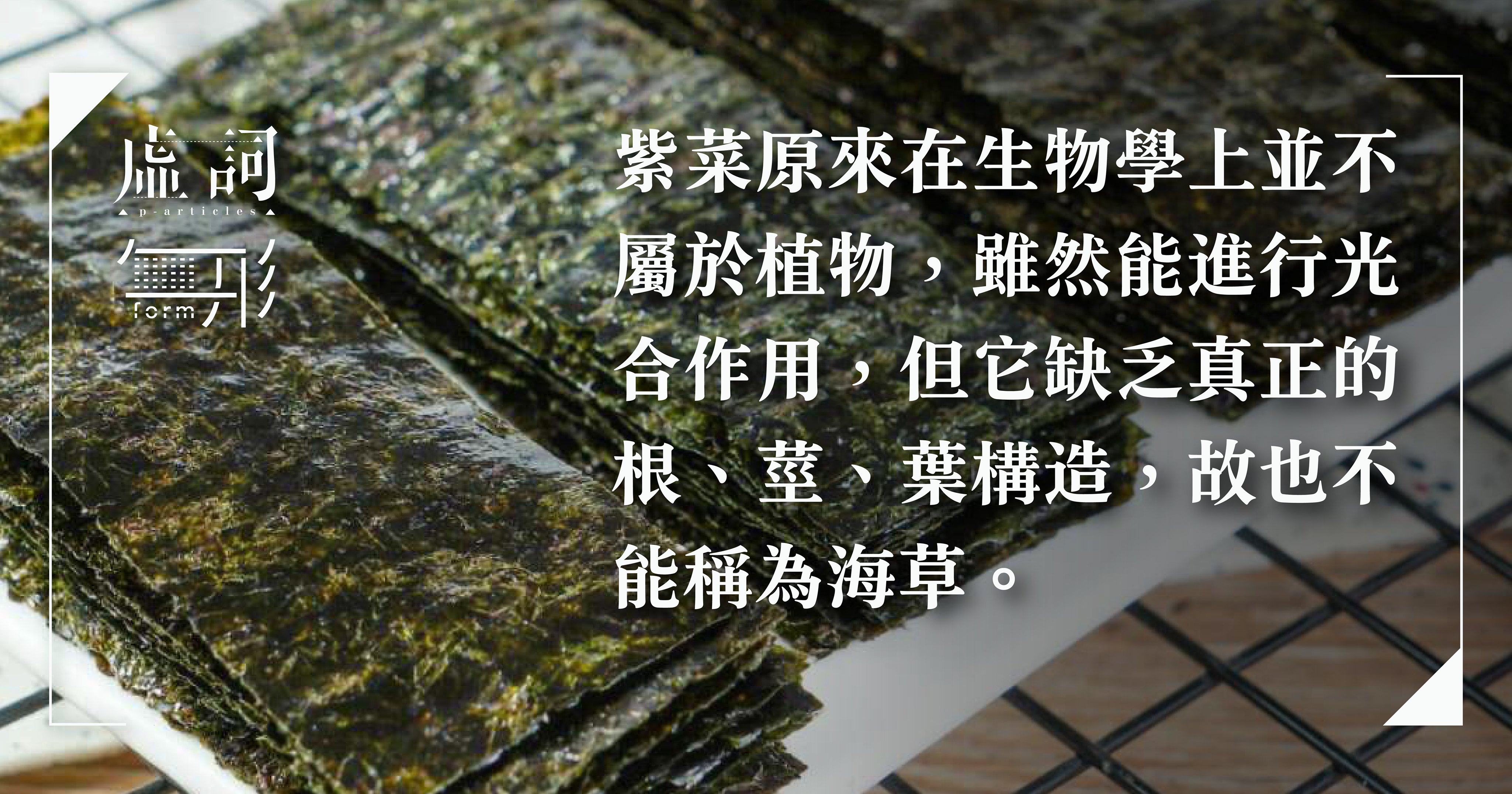【無形.Comfort Food】 紫菜
「如果有一天,紫菜突然從地球上消失了,你會怎樣?」那天你突然這樣問。我以為是某種謎之心理測驗或是甚麼環保議題新聞,未有認真:「會生物鏈斷掉之類,像蜜蜂消失,人類滅亡?」你說:「好簡單,就是你再冇紫菜食了,只是這樣。」
在那幾小時前,我們談到Comfort Food,相互提了些例子,總覺不怎麼對味。原以為是海膽,再貴也願意花費,喜歡那濃甜;又以為是布丁,不好過時會衝進超市或便利店買冷冷滑滑的布丁,焦糖、牛奶、草莓……任其融化口腔,便覺有甚麼消減了一般舒懷——但總覺得,不對味。真是麻煩,生活中太多選擇,到必須抉擇時,便覺論斷艱難。
然後你說啊不就是紫菜。
不就是你平穩相信著不會變改,會一直如此的東西,某天眨個眼的瞬間,灰飛煙滅,在那呆滯怔忡的時刻,才理解那原是一直穩住自身,如呼吸所理所當然的存在麼。
我想起自己是那樣無所節制的人,一旦習慣便不懂規律和約束,做事如是,飲食如是,生活如是。小時候讀到喜歡的小說,便日夜不能停止要讀完,上課藏在抽屜偷讀、晚上躲在被窩打著電筒讀——被老師或老爸沒收了,到另一家圖書館再借,就是卯起勁來就誓要如此。
上了中學後,開始借住外婆家。外婆是刀子口豆腐心,嘴裡總沒一句好話,但整天四處奔波,不是見她待在廚房削蘿蔔包餃子,就是到老人院替友人看望已中風的丈夫,當然也包括餵養我。忘了哪次跟她逛超級市場,挑過紫菜、益力多、魷魚絲之類。(大概那時只是嘴癢想吃些零嘴。)然而此後每次到外婆處,總會見她沒好氣說:「自然不會餓壞你這化骨龍啦,早買好你喜歡的東西了。唉,全都不健康,食到你大頸泡。」幾句話間全無邏輯關係,甚至相互矛盾,是她的講話特色。還需相當久後,我才把這些含混的話理解出來。
然後成為一種模式:她買來三三兩兩的零嘴,我沒兩下吃光;購來更多,我吃得更兇——一種無意識的進食,呼吸一樣,並未理解節制之必要,甚至越快消耗越好,才能得到更多,譬如一排五枝的益力多,我可以塑料包裝也不拆,只以短硬的小飲管逐瓶戳出小洞喝光,下一枝,再下一枝。最後整排連包裝丟掉,不過數分鐘的事。
或譬如紫菜,那時尚未興起韓國鹽烤紫菜或小老闆之類,尚是四洲紫菜的天下,外婆從小包買到大包裝,即從廿四小包至五十小包,皆被我一下掃光。連底片般連起的片裝都不用撕,逐包剪開,一把整撮塞進嘴裡,我也以經驗與舌頭見證著四洲從一包五片減料至三片。
外婆說我從不知節制,一個下午就吃光一大包紫菜和兩排益力多,包裝漲滿垃圾袋,像紫菜混著益力多在肚內發泡,擠堵了整個胃,幾近嘔吐。
上了高中後我開始不怎麼愛吃這些零嘴了——或該說是,那種無法抑止,沉溺似的不可抽離的狂熱,不再體現於進食中,更多是談亂七八糟的戀愛、寫迴迴繞繞的字。情感的磨人實在比肉體上帶有極限的運動性更為消耗。
但外婆仍然買來零嘴,規律而秩序的儲量一樣,我的處理速度卻大不如前,食物遂越積越多。
多年後至今,直到整天上班當老人院看護而無暇在家做飯的母親,總像購物狂般買來大量凍肉如肥牛青口漢堡扒雞翼急凍雜錦海鮮麵包蟹豬腩肉,囤滿冰箱塞至偶爾打開時會被某塊無法平衡安放的硬重冷肉墜落砸中腳背痛得紮紮跳,而被母親怒目抱怨全都怪我,怪我未有消耗、吃或煮掉她買來的種種食材,才會致使冰箱過滿,教她再難添置新貨。我才明白,這是她們表達愛的方式。購買,囤積,不由分說地,把愛塞至懷中,殷切期盼你能迅速消化,好使她們舒氣並安心去張羅更多的愛。我想起那些在腹中泡爛發漲的紫菜,像藻類於海底蔓生擴佈。那是它們原初的模樣。
***
後來還是一直吃紫菜。外婆走後,在她的床頭櫃內,還有兩大包韓國烤紫菜,許是等著我來而買。
大學最難熬時,整天就躲在宿舍裡暴飲暴吃,吃好多紫菜,阿信屋的九包裝韓國紫菜,從從前十多元加價至如今二十元,一直是忠實支持者,大量入貨。無法控制一樣流著淚吃,拆拆拆,粗暴焦急。一盒包裝近十塊紫菜,餓鬼般一手抓起放進嘴裡嚼食,脆裂可口,彷如救贖。(後來看《地厚天高》,看到梁天琦說自己憂鬱至臨界點那時,會到快餐店吃薯條,不停吃不停吃,尋找某種憑依一樣,就知道,噢出事了。我便想起,啊,紫菜真的好好吃。)
有次在做個類似「You are what you eat」的計劃,好奇下查了部分食物資料,發現紫菜原來在生物學上並不屬於植物,雖然能進行光合作用,但它缺乏真正的根、莖、葉構造,故也不能稱為海草。
所以真正的問題應該是:「如果有一天,再冇紫菜食了,你會怎樣?」(你會跑到另一個有紫菜食的世界嗎?但這是不存在的。那些以為可行的人,不過把海草誤為紫菜)那些我們曾習以為常,視之為定律常理的種種,在城市崩壞之時,彈指間消燃殆盡。
我說,無如果的。只能趁還能吃時,餓鬼般含含聲倒入口。不過是,無根之人亟欲抓緊甚麼,救命草一樣,我的剛巧是,這皺皺飄飄,無根無莖無葉的海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