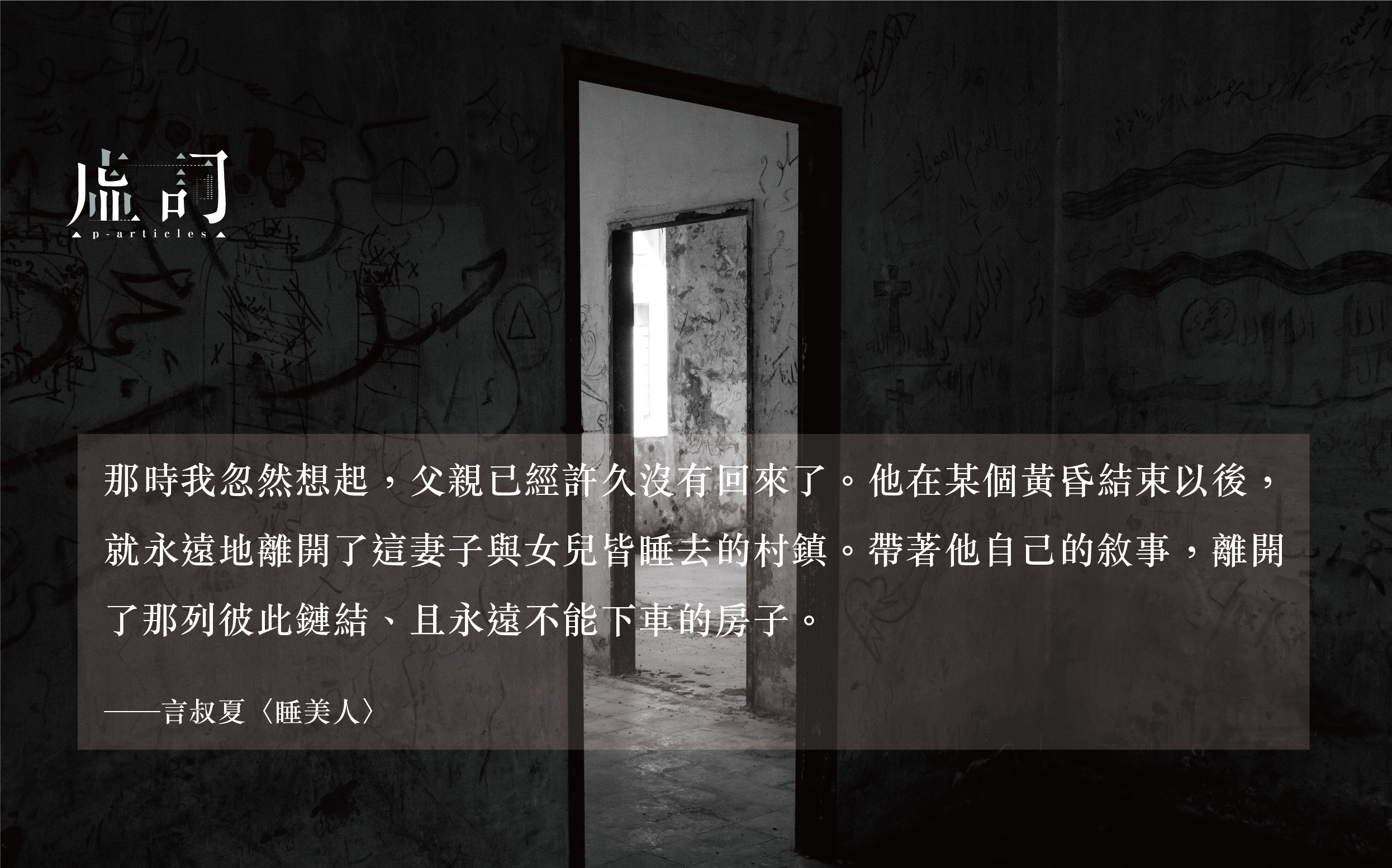【無形.無形】睡美人
越過了三十歲,老家的屋子在夢境裡逐軌道般地遠去了。像一列淡出的火車。我不知道那車廂上屬於我的房間是否亦被搖搖晃晃地一路晃進無邊的黑裡。三十歲以前,我一直以為自己會在這列車上,一起被駛進無有重力的黑洞中,和另一個車廂的母親與妹妹一起。她們都戴上了狐狸般的面具。即使母親不說,我也知道她的害怕。母親常很可憐地看著我說,婚姻是歧路,總有一天你會落車,和我們行不同的路。說著這話的母親,將她遮蔽了半邊臉孔的狐狸面具輕輕地挪移開來,露出了艷淌的唇色。我害怕了起來,有點生氣地對母親說,現在可是二十一世紀。
但是,母親的話語像是海邊岩石的皺褶。有些裂縫,是女性主義者怎樣也抵達不了的罅隙,遠在世紀的向度之外,停棲著小丑魚。那像是童話故事開始時的一種預言,決定了敘事的命運。奇怪的是婚後我真的極少再夢見那幢屋子。母親與妹妹的狐狸臉孔,變得很淡很淡,敷上人皮般地現出了人形。在光天的白日之下,她們的輪廓浮水印般地浮了上來,拓印出現實的側臉。母親與妹妹好像分裂成兩個,一個在白日裡顯現,另一個就在光影裡被漸次地擦拭,黯淡了下去。我擦了擦眼睛。也許變得現實的人其實是我?是我離開了二十世代結滿蛛網的巢穴,走進了前中年的白晝。
惟有一個房間,是至今仍不時出現在我午睡的夢中,幽幽魅魅地,干擾著午寐的漩渦。醒來的時候,沼澤般的午睡爪一樣地攀抓住了我,使我分不清究竟是黃昏還是天亮。那是老家頂樓幽黯的鴿樓。我出生的時候,樓裡的鴿早已不知去向。那廢棄的鴿樓像是一顆屋子生長出的瘤,懸掛在頭頂,燈籠魚一樣地讓這屋子在夜裡懸游。有個記憶不知是否準確。母親告訴我,捕魚的叔公夜晚就睡在那鴿樓上,打著赤膊。那是因為南方的夏日屋裡,實在太過燠熱的緣故。
叔公已死去多年了。是我離家唸大學時的事。印象中是一種和水有關的疾病。我沒有回鄉參加過葬禮的記憶,因此總覺得叔公的死像是一個波長十分微弱的回聲,嗡嗡嗡地從海底探測儀裡傳來。我已經死了噢。告訴你們一聲。開玩笑般地。好像他只是住在一口海底的石油井裡,好像那井底住著的是一隻很老的動物。那使得死亡這件事也變得讓人摸不著頭緒了起來。其實我並不記得叔公的長相,卻很記得他家裡有位姑姑十分瘦弱,手腕跟雞爪一樣細。有些暴牙。永遠剪著一式女學生般的短髮。靜默地坐在家門口。
「別接近契子姑姑。」 黃昏露出一條牙齒般的縫隙時,母親的話就像烏雲那樣飄過來,鴿樓一樣地遮住了傍晚的天空。鴿樓裡空盪盪的,傳來嗚咽的回聲。跟著母親的聲音方向看去,我看到契子姑姑絲質黃色襯衫的側影。西曬的黃昏來臨時,她的側臉就長出了金黃色的毛邊,像一朵安靜發狂的菊花。很多年以後,我在田村隆一的詩裡讀到:「這個男的/是年輕時殺死了父親/那年秋天/母親便很美麗地發瘋了。」
很直覺地想起了那樣的姑姑。不知怎地竟有點美麗。
那樣有著尖尖鴿樓的村鎮,多年以後回想起來,竟像是沙漠中的一個小城,發散著西部片般的色彩。北緯二十三度以南的地方,底片的膠捲翳上了昏黃的顏色,一格一格拉得又遠又長。不知怎地,腦海裡浮現的,竟是睡美人的故事。也許是因為那閣樓上的女人日夜踩踏著一架老舊的紡織機,最終被紡錘的尖端給刺出血來,就此昏睡了一百年,像極了這個昏昧小鎮的午後燠熱。它離海很遠,離山也並不靠近。低矮的丘陵起伏像是海港昏沉的午寐。午睡醒來的時候,是下午三點鐘那種安靜的時間。白日的男人理所當然地外出工作了,消失也似地。只有那些圓規般的女人們,在這貓一樣孵著的小鎮裡,立定單腳,緩慢地用另一隻腳畫圈跳舞。不知道為什麼,童年時的我總有這樣的錯覺,好像睡了一覺醒來時,整個村子都被海吞進了肚子裡似的。是海做了一個夢,吹泡泡一樣地將它孵進了透明的泡沫裡。於是母親,姑母,妹妹,還有我,在這泡泡裡走來走去,無論走到哪裡,都觸摸到那看不見的隱形牆壁了。
只有一次,在黃昏的頂樓,積雨雲紡錘一樣地剛好來到我們的屋頂,插在屋頂的天線上,變成了一張巨大的蕈傘。我在那直角三角形狀的灰暗鴿樓裡,看到了蹲踞著的姑姑。
我沒有與姑姑說話的記憶,因為姑姑牙齒排列組合的方式,使得她所能發出的每個音節,都像是一把壞掉的提琴,是用琴弦鋸出來的。
「你在這裡做甚麼?」
她抬起頭,用微微暴齜的牙口,詰屈聱牙地說:「等船來把我接走。」
我抬頭看到那頭頂上積雨的雲朵,倏忽靠近,忽然掉下了斗大的雨滴。發出很沉重的「咚」一聲。因而知道雷很快就要落下來了。在雷之前,是大片掉落的閃電,將天空蘋果一樣地劈成兩半。還有傍晚從城那邊回來的男人們,像鳥一樣地,濕漉漉地上了岸。我忽然明白,姑姑在等的是她的父親,從海上把船開到這屋頂來。
母親與妹妹,好像都不知道這樣的事。不知道夜晚的屋頂,會在黃昏過去以後,變成港口。很多年以後,我在一個清晨穿上了白紗,跟著某一男人離開這魘一樣的村子時,母親還在床上深沉地睡著。我把扇子從車窗丟出去的時候,鴿樓裡傳來嗚咽的哭聲。那會是契子姑姑嗎?
那時我忽然想起,父親已經許久沒有回來了。他在某個黃昏結束以後,就永遠地離開了這妻子與女兒皆睡去的村鎮。帶著他自己的敘事,離開了那列彼此鏈結、且永遠不能下車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