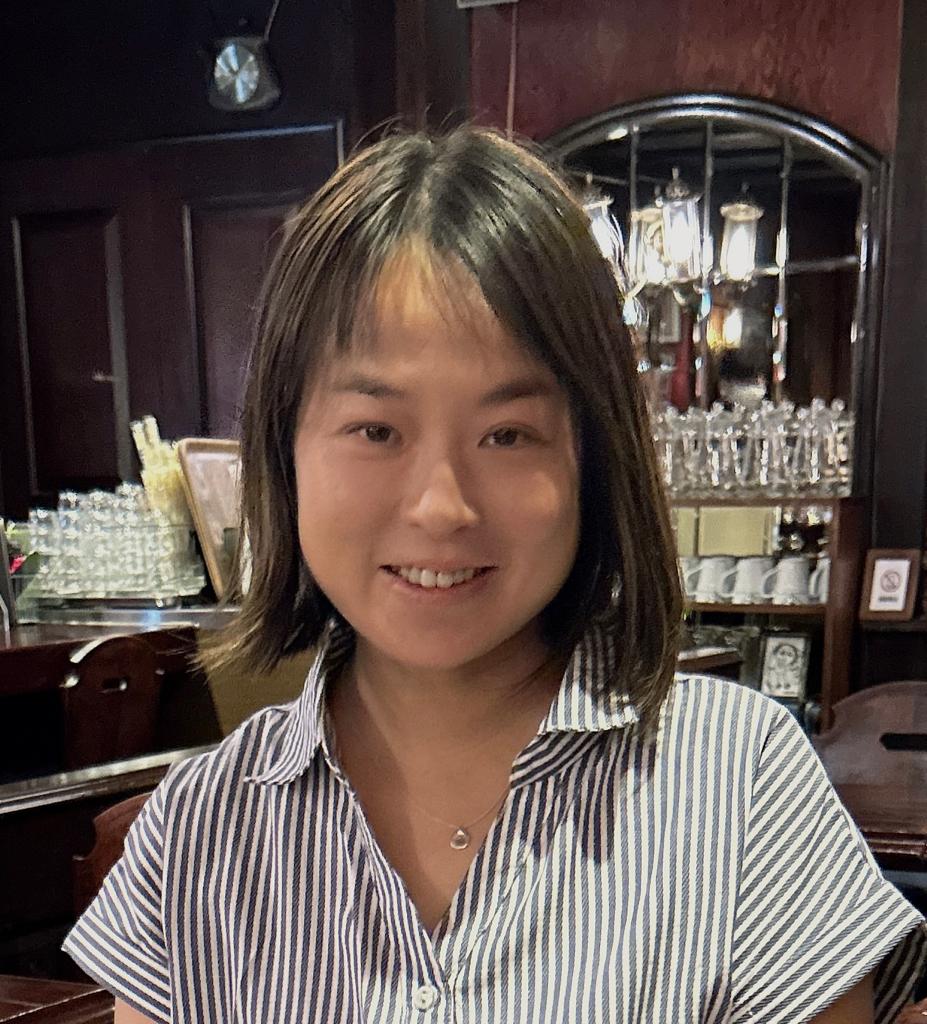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為師之道】既不多言也不妄語
那時已經在讀中大的教育學院了,去問中學時非常尊敬的老先生,「老師,以後我也打算做教師呢,請問您有什麼忠告給我呢?」老先生頂著地中海髮型,托一托唐君毅式的茶色眼鏡,對我說︰「做老師的話,緊記不多言。」當老師的話,最緊要「不多言」—此話果然睿智!
這確是非常有難度,很多教師都是一上台就能滔滔不絕,能夠把每一節課都講成TED talk那樣精彩,都可說是絕活一種。現在已經很少依書直說的老師了(除非剛巧預到),更多的是上課時孜孜不倦在講自己的私事,禁不住興奮莫名的。這樣有時候真是一種自以為是。老先生︰「不多言」這三個字除了是防範「言多必失」,還有著孔夫子「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的目標。以後當我又在課堂上興奮莫名的時候,或者囉囉嗦嗦誨人不倦之時,我會突然想起這句說話︰「不多言」然後就好好勒住嘴巴。時裝界名言less is more 亦能放諸教育目標 ︰「言必有中」、「言簡意賅」名言至理,除了要寫給教育局看的文件之外。
「沒有了?就是不多言嗎?」老先生想了想︰「不說謊。不說謊欺騙孩子,孩子呀,是會長大的。」為了面子硬著頭皮教錯知識,為了避免說不知道而胡亂吹噓,能夠在課室的一時一刻頂得過去。可惜孩子是會長大的,你總不能欺騙他一世,當他長大回過頭來用成熟的腦袋回看小時候,你就會變成一個無恥之徒。這句說話也是佛制五戒之一的「不妄語」,我也深深記著了。就好像寓言故事中那勇敢的小猴子,當全村的老猴子都告誡他不能過河的時候,他就是偷偷過了河喝了更甘美的泉水,還拿來了好吃的水蜜桃。青年人懂得的,往往比我們想像的多。
有一些學術知識,所謂未知者不罪,倒是沒有什麼大礙。隨著科技發達出土的文物越來越多,很多舊觀念只是曾經存在成為集體回憶罷了。例如有孩子的人總發現現在中文老師所教的讀音或者筆順與所學的記憶相比來說真可以是南轅北轍。這點點不偏離正道也就算了。
所謂欺騙,很多時候是帶著無知的善意。這樣的結果卻是非常恐怖的,例如通過恐嚇告誡女孩子性接觸的恐怖和放浪的定義;例如只要有住屋需要就可以填海;例如南亞裔香港市民一定在從事非法勾當;例如一男一女結合的婚姻才是神聖的…這些與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放任自己的偏見和私心。我們常常說教師的職責是「傳道授業解惑」可是傳播所謂「道理」的時候,不禁常常懷疑那是事實的真相嗎?這說得上是普世價值嗎?說不定是一個時代的妄斷?那麼,如何才能通過知識更靠近真理呢?
某些主流教育模式中的課室,恰是一架在過去與未來之間擺盪的鞦韆。他從來不是一個當下的此在,有關傳承,他是過去的知識或者經典,有一些早已經被時代遺棄;有關未來,就是成年人家長或者社會對小孩子的期望,設想將來的所有告誡。當教師理直氣壯地告誡青年必須的生活方式,可能只是在舔舐自身生活的滋味。這些經驗隨著我們變得固步自封,或者步步為營,有時候是固執而過時的。
教師不是應該「先進」嗎?現在卻不知不覺成為了社會最保守的力量。教師的工作幾時變成了「管住班細路唔好畀佢哋作反,確保他們明天成為社會的螺絲繼續高速運轉」?於是學校變成一座監獄,這已經不是新鮮的比喻了。「甚麼都反對才像學生哩!」*高錕校長固然見識超卓,胸懷濟闊,可是現在要找到認真反叛的孩子也不容易呢。
妄想要「教」屬於永恆的東西,不如給大家一個更好的當下體驗,就在此時此刻,呼吸著秋天的塵埃,我們一起溫故知新,我們交換想像,我們思考我們沉默,於是我們記得。就好像大江健三郎必須記認森林裏屬於自己的樹,又要提防將來的自己*。有一天或者我已經忘了你的名字,但我仍會記得你的笑容,我記得你青春年少時的面貌,如同我們彼此都記得一段美好時光。
*
周保松︰〈真正的教者 ──側記高錕校長〉香港獨立媒體網,2018-09-24
*
大江健三郎︰《為什麼孩子要上學》第二章「人為什麼要活著」,時報出版,2002。